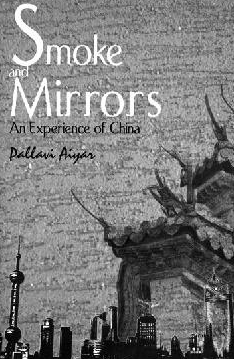
經(jīng)濟(jì)觀察報(bào) 伊武藤/文 你會(huì)唱歌跳舞嗎?是印度好還是中國(guó)好?這是PallaviAiyar在中國(guó)被人最常問(wèn)到的兩個(gè)問(wèn)題。
當(dāng)她在2002年乘坐東航航班從新德里來(lái)到北京廣播學(xué)院教書(shū)之前不久,這兩個(gè)世界上最古老的國(guó)家(而且是鄰居)之間才剛開(kāi)通第一條直達(dá)航班。Ai-yar說(shuō)她去中國(guó)大使館辦簽證的時(shí)候,發(fā)現(xiàn)門(mén)口竟然冷冷清清,而其他國(guó)家駐印度的大使館門(mén)前往往擠滿(mǎn)了印度人。
在北京呆了幾年后,她才意識(shí)到出租車(chē)司機(jī)總對(duì)著她唱的那首歌來(lái)自一部名叫《大篷車(chē)》的電影。那位印度演員在許多社會(huì)主義國(guó)家都非常紅,她說(shuō)自己的一個(gè)親戚曾經(jīng)在智利的某個(gè)小城聽(tīng)到那位演員的歌聲。
至于究竟是印度好還是中國(guó)好,PallaviAiyar試圖在《鏡中花——我在中國(guó)的日子》(SmokeandMirrors:AnExperienceofChina)這本書(shū)中通過(guò)事實(shí)展現(xiàn)出某種可以視作答案的選項(xiàng)。
中國(guó)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無(wú)疑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dāng)她在寧夏某個(gè)貧困的鄉(xiāng)下采訪,碰到一位老漢抱怨村子里15年沒(méi)有女人嫁過(guò)來(lái),因?yàn)樘F;結(jié)果她發(fā)現(xiàn)這位老漢家里既有電視還有DVD機(jī),她說(shuō)在印度這已經(jīng)可以算作中產(chǎn)階級(jí)了。在印度,只要會(huì)寫(xiě)自己的名字,就不能算作文盲,而中國(guó)的標(biāo)準(zhǔn)是得認(rèn)識(shí)1500個(gè)漢字。
在這本書(shū)的前三分之一,Aiyar就像是所有初次來(lái)到中國(guó)的外國(guó)人,筆下的所見(jiàn)所聞在大多數(shù)外國(guó)人寫(xiě)的關(guān)于中國(guó)的書(shū)中都能看到。這本書(shū)的有意思之處來(lái)自后面的三分之二。
在印度,她最常被問(wèn)到的一個(gè)問(wèn)題是:印度能從中國(guó)學(xué)到什么?這個(gè)問(wèn)題就跟“是印度好還是中國(guó)好”一樣,是一個(gè)很難回答的問(wèn)題。中國(guó)經(jīng)濟(jì)的高速發(fā)展,有相當(dāng)部分是政府強(qiáng)勢(shì)的結(jié)果。比如Aiyar在德里的家附近,有一個(gè)過(guò)街隧道修了三年還沒(méi)有修好,但中國(guó)只要在圍墻上寫(xiě)一個(gè)“拆”字,一兩年后這里就變成了一棟高級(jí)寫(xiě)字樓或者一座高架橋。但這并不表明作者認(rèn)同這種行事方式,或者不珍惜一些普世的價(jià)值觀。在中國(guó)的五年時(shí)間里,她發(fā)現(xiàn)印度雖然是一個(gè)仍然存在諸多社會(huì)不公的國(guó)家,但社會(huì)壓力通過(guò)正常的宣泄渠道得到了相當(dāng)?shù)尼尫拧?
不過(guò),中國(guó)的諸多做法在印度的中產(chǎn)階級(jí)中似乎得到了普遍的認(rèn)同。這讓我想起一些中國(guó)人在比較中印的時(shí)候,最?lèi)?ài)引用的一個(gè)觀點(diǎn)是兩國(guó)的經(jīng)濟(jì)現(xiàn)狀證明自己所處社會(huì)制度的優(yōu)越性,而忽略了(或者刻意忽略)更多的東西,比如文化差異或者人生態(tài)度的不同。簡(jiǎn)單的結(jié)論,要不就是出于粗暴,要不就是出于刻意隱瞞。對(duì)于究竟是印度好還是中國(guó)好,PallaviAiyar到最后也沒(méi)有給出確切的答案。我相信,許多人看完這本書(shū),也難 以 得 出 答案,因?yàn)槲覀儫o(wú)法通過(guò)假設(shè)去推導(dǎo)出必然的結(jié)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