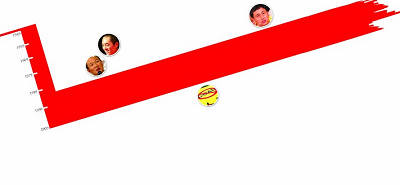
經(jīng)濟(jì)觀察報(bào) 施健子/文 國(guó)慶前的文化娛樂(lè)市場(chǎng)幾乎是一場(chǎng)競(jìng)賽,50部獻(xiàn)禮片中,除了《建國(guó)大業(yè)》,其余的49部都在爭(zhēng)當(dāng)票房亞軍;而經(jīng)常光顧報(bào)刊亭的人應(yīng)該可以發(fā)現(xiàn),在最近的兩個(gè)月里,所有的媒體都在用他們慣用或生疏的聲調(diào)來(lái)宣傳新中國(guó)的60年。而且無(wú)論是財(cái)經(jīng)、政治或是我所熟知的生活方式,關(guān)鍵詞都是“變化”和“成就”。
“五十年代手電筒,六十年代收音機(jī),七十年代電視機(jī),八十年代電冰箱,九十年代洗衣機(jī),2000年是Web2.0……”這是媒體喜聞樂(lè)見的形式,在精減掉引述的隔壁老王所說(shuō)的大量煽情詞句之后,可以簡(jiǎn)稱為一部中國(guó)家用電器編年體。不難猜到作者的意圖,物質(zhì)生活的進(jìn)步是觀察整個(gè)60年生活方式最直觀的坐標(biāo)。只是,生活并不是簡(jiǎn)單地從布拉吉連衣裙到名牌手袋的過(guò)渡,掩藏在物態(tài)和數(shù)據(jù)下細(xì)膩的情感在這種粗糙的總結(jié)中消失殆盡。作為上層建筑的衍生物,生活方式理應(yīng)帶有強(qiáng)烈的國(guó)別屬性、年代特色和體制痕跡,如果抹去紀(jì)年不看,收音機(jī)到電視機(jī)的進(jìn)化亦可以代表第二次工業(yè)革命之后的美國(guó),只是時(shí)間上比我們提前了大約50年。
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是必然的,我們想要探究的,是在物質(zhì)豐富的過(guò)程中,我們又有著如何的心態(tài)區(qū)分?它決定了我們?cè)谀硞€(gè)年代里有著怎么樣的流行和生活方式。它的變化,不難得出各個(gè)時(shí)期不同文化力量的博弈、塑造乃至回歸的形態(tài),以及一系列歷煉之后鮮活的中國(guó)生命力。它的復(fù)雜,又豈是可以用一條線概括的?
每天早上,我都會(huì)穿過(guò)和平西橋來(lái)到位于和平里的報(bào)社上班。這片1952年為紀(jì)念在北京召開的 “亞太和平會(huì)議”而命名的社區(qū),是當(dāng)時(shí)的蘇聯(lián)專家樓,中蘇關(guān)系破裂之后,它們被分給了各個(gè)單位的職工居住,完整保留下來(lái)的諸如總政社區(qū)、冶金社區(qū)等名稱,是計(jì)劃經(jīng)濟(jì)時(shí)代遺留下的最好的注腳。
如今居住在這里的大多數(shù)人依然堅(jiān)守著原來(lái)的生活方式,到早市買菜、騎車上班、像以前那樣參加社區(qū)組織的乒乓球賽——雖然從這里只要向北走十分鐘,就可以到達(dá)北三環(huán),一路之隔的生存法則換成了寫字樓、股票交易所、大型商場(chǎng),還有穿著時(shí)髦的男女。
北三環(huán)附近有一條沿護(hù)城河而建的元大都酒吧街,經(jīng)營(yíng)狀況與河水清淤進(jìn)展成正比,雖然如此,光顧此地的年輕人還算多。入夜,當(dāng)DJ開始播放萊納德·斯凱納德(LynyrdSkynyrd)樂(lè)隊(duì)的歌時(shí),吧臺(tái)附近的中國(guó)女孩和著節(jié)拍一邊唱一邊扭動(dòng)起來(lái)。
他們與父輩有著不一樣的生活,三年一代溝的俗語(yǔ)在中國(guó)不僅指的是年齡產(chǎn)生的心理距離,還有短時(shí)間內(nèi)生成的生活背景差異。當(dāng)你漫步于北京這座幾乎永遠(yuǎn)都在變化的城市,大部分地方塞滿了混凝土住宅樓,它們以一排排模糊的窗戶和裸露室外的空調(diào)部件為標(biāo)志,聳立于陰沉的天空,高檔百貨的櫥窗里展示著來(lái)自世界各地的品牌,巴黎的女裝和意大利的男裝最為盛行,一如當(dāng)年流行的蘇聯(lián)裝。“生活無(wú)極限”,門口高懸的廣告牌上的醒目字體教育著人們的生活。
“這個(gè)國(guó)家的年輕人拼命想抓住未來(lái),但未來(lái)是什么,他們不知道。”1949年2月的《時(shí)代》周刊上,美國(guó)人如此描述中國(guó),他們并沒(méi)有想到同一個(gè)政權(quán)下的60年后,中國(guó)會(huì)擁有如此生機(jī)。不過(guò),對(duì)于生活于此的大多數(shù)人來(lái)說(shuō),未來(lái)仍然存在另一種的不可控。
事實(shí)上,我們很難用眼睛所能觸及的片斷來(lái)囊括現(xiàn)在的中國(guó)以及她的飛速變化,但還是不斷有人嘗試著深入到古老文明的肌理,在政治、經(jīng)濟(jì)之外的領(lǐng)域用他們的語(yǔ)言來(lái)影響中國(guó)。設(shè)計(jì)師們翻出已經(jīng)消失幾百年的紡織技術(shù),展示復(fù)活的中國(guó)宮廷服飾;大型的團(tuán)體表演在中國(guó)條件允許的各個(gè)地方里極為盛行,延續(xù)張藝謀和譚盾所開創(chuàng)的感官中國(guó);中國(guó)暫時(shí)沒(méi)有領(lǐng)先的創(chuàng)意能力,卻有著全世界最頂尖的當(dāng)代藝術(shù),那些被我們熟知的,也讓我們被人所熟知的丑陋在畫家的手指中得到無(wú)限放大。他們渴望在行進(jìn)的途中用意識(shí)滲入的方式建立新的生活秩序,排除其他文化的強(qiáng)勢(shì)介入,讓中國(guó)特色的懷舊和樂(lè)觀得以并存,并在未來(lái)生成一種叫文化自信的東西。
這不是我們習(xí)慣的中國(guó),卻是朝著被期待方向正在被建立的中國(guó)。這是外國(guó)人很難理解的一件事,在短短60年之間,中國(guó)人的心理和價(jià)值觀可以包容如此之大的顛覆和重塑。物質(zhì)刺激下焦躁的社會(huì)心態(tài)在近20年來(lái)愈演愈烈,這種心態(tài)下的某些瓦解和突破相對(duì)而言卻是積極進(jìn)步,我們的生活才得以如此多樣地存在,無(wú)論是模仿、彷徨還是失落,過(guò)去的和我們正在參與的,組成了前所未有的尋找自己的年代。
現(xiàn)在僅僅是開始。在我們對(duì)話的人物和群體中,知名度并未作為甄選指標(biāo)過(guò)多考慮,我們更關(guān)注他們?cè)谵D(zhuǎn)型社會(huì)中所扮演的思想和力量以及在這其中存在著的重復(fù)和相似。張藝謀和張曉剛的藝術(shù)夢(mèng)靨;譚盾和吉平生的異國(guó)探索;幾乎在同一個(gè)時(shí)候,張路和薄濤帶著夢(mèng)逃離了可以預(yù)見的生活,而他們的所得與綠色和平的中國(guó)歷程又代表了多少觀念的轉(zhuǎn)身……他們的位置決定了我們的生活,我們只是談了冰山的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