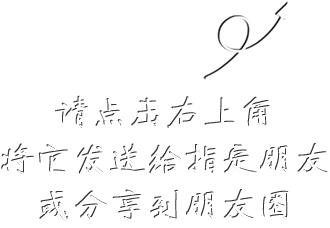陳芝/文
李劼先生的《論紅樓夢》是我在高中時期除《馬恩全集》以外讀過的最好的文學(xué)評論,大學(xué)期間也不止一次向朋友推薦過此書,七年以后借新版回顧,所生出的頭一感慨便是,文化人能寫出的最好的書與最差的書就是這種類型,愛者手不釋卷,恨者棄之糞土。如果不能接受作者先在的價值立場,讀此書仿佛自尋煎熬;反之,易有醍醐灌頂,相見恨晚之感。
不過說是文學(xué)評論,如果你想在此尋求一本專業(yè)的學(xué)術(shù)著作它是不夠格的,作者對中其意的紅樓人物的溢美與對厭惡者的刻薄明顯不知節(jié)制,使得很多人物被漫畫式的夸張放大,變得像是其所評點(diǎn)的不是我們耳熟能詳?shù)哪遣啃≌f,而是一部低劣的同人作品,至于書中各種論斷比比皆是的偏頗與武斷更讓抵觸者添加了一條放棄的理由,如果之前還沒有厭惡到家的話。
然而考慮到這是一部斯賓格勒式的論述,以上一切又顯得理所當(dāng)然,不如此反倒值得稱奇了。換句話說,李劼先生是個才子式人物,寫不出那種四平八穩(wěn)讓所有人都能欣賞的文章,自古以來這樣人的共同特征便是實際上用激情而不是其他種種言語,因此真知與偏見交雜混融,不分彼此。謊言是弱者的專利,直言不諱是強(qiáng)者的特權(quán),是以他們會比大多數(shù)人更能看清事物的本質(zhì),絕大多數(shù)聰明人以其智力并非不能做到洞穿慘淡現(xiàn)實背后的陰暗,然而他們不愿承認(rèn)真相,寧可自我欺騙,久而久之便如同皇帝新裝的故事,仿佛真的有那么一件美妙絕倫的衣服擺在所有人面前。
是以李劼先生的大部分論斷并不是沒有道理的,只是他生命中洋溢的激情損害了平衡能力,使他稍欠公正的比例感,或者說不能節(jié)制自己的尺度,讓不習(xí)慣這種言語的素人覺得言語過分苛刻,缺乏理性中立客觀,與你批評的對象有神馬兩樣,進(jìn)而站到對立面。然而如果你愿意忍受這方面的缺陷,那么這本李劼先生借他人酒杯澆自己胸中塊壘的《論紅樓夢》也不可能不從中有所收獲。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以外,如果說本書還有什么遺憾的話莫過于李劼先生將紅樓夢視為與西洋存在共時性的中國文藝復(fù)興的代表作,姑且不論自清代以來這所謂的文藝復(fù)興指代的是何物,或許他說的是完成度已經(jīng)超過百分之六十的社會主義偉大復(fù)興,就他將文藝復(fù)興視為對紅樓夢的最大褒獎,也很能反映出他視野上的天花板,再怎么推崇洋大人,對洋大人的理解還是有所局限,到如今李劼先生也沒有多少改變,這只能歸結(jié)為小資產(chǎn)階級世俗知識分子的通病。
所以當(dāng)他在本書開篇推崇貴族精神,也就不難發(fā)現(xiàn)這種不計功利為其深深稱許的貴族精神固然超脫為蝸角功名,蠅頭微利爭搶地頭破血流的綿羊走狗,但這種貴族精神只是世俗知識分子/士大夫意義上的,并且審美性更重,缺乏成為社會凝結(jié)核,更談不上正直勇敢忠誠虔誠等社會性很強(qiáng)的人格特質(zhì)。他們最終的結(jié)果無非是可以潔身自好,但不可能開辟新天地,造就一個被否定的現(xiàn)世完全不同的理想社會。因為他們太出眾了,以至于根本無法與庸眾相處在一起,兩者已經(jīng)是不同物種,存在生殖隔離。
拋開這一點(diǎn),他對紅樓人物的歸納還是很有道理的,因為紅樓夢或者說東亞大陸本來就很匱乏土豪,也罕有成為或稱許社會凝結(jié)核的思想資源,對朝廷來說這本身就有不服王化叛離中央的威脅。
李劼先生的創(chuàng)見是,至少在當(dāng)時是如此,曹雪芹的寫作可以或者說理當(dāng)從人類精神面貌和命運(yùn)處境的角度去賞析,政治學(xué)或考據(jù)功夫容易走進(jìn)支離破碎的死局,紅樓夢是作者的自傳,但又不僅僅是作者的自傳,曹雪芹借紅樓夢固然有追憶兒時似水年華的沖動,同時也在人生末年反復(fù)審視人類靈魂自身,對那些美好事物,就像賈府中唯一的凈土大觀園最終也落得陪葬的結(jié)局而感到憤恨與遺憾,世界毫無疑問最后將走向毀滅,用李劼先生的話說便是由色(現(xiàn)象)到空(虛無),但不同的東西被毀滅作者的態(tài)度也明顯是不一樣的,而閱讀紅樓夢,就應(yīng)當(dāng)與作者一起思考是什么導(dǎo)致了人類精神風(fēng)貌的衰落與瓦解,人的命運(yùn)是否終究只是一場虛無,剎那的光輝轉(zhuǎn)瞬即逝,轉(zhuǎn)而被無邊的空洞長久取代。這些問題可能有答案,也可能沒有答案,但問題本身其實比答案更重要。
從這一角度切入,我們可以看到,在李劼先生眼中,紅樓夢是一個走狗與綿羊的世界,走狗的粗鄙與綿羊的平庸替代了豹的進(jìn)取與高貴,也就是奴隸道德取代了主人道德,不僅那超脫現(xiàn)實不計利害,對世界審美式的貴族精神已經(jīng)難以看到了,就連像浮士德一樣充滿生機(jī)與動力的創(chuàng)造者也被時間湮滅,從充滿進(jìn)取精神的祖先開始,一代不如一代,逐步走向寂滅的寒冬,表現(xiàn)在紅樓夢中,便是從榮寧二國公開始,經(jīng)歷賈代善、賈代化,到賈政、賈赦、賈敬,再到賈璉、賈珍、賈環(huán),再到賈薔、賈蓉等人,再以及他們的奴仆,人類在不斷地墮落,道德文章不過是科場考試的投名狀,禮義廉恥只是行走社會的門面?zhèn)窝b,僅知皮膚淫欲的紈绔子弟忘記了祖先的德性與功業(yè),并逐漸邁上自我毀滅的道路,落得白茫茫一片真干凈的下場。
在整個紅樓夢里,除了賈寶玉、柳湘蓮等寥寥游離在世俗秩序以外的幾人,其他的男人基本上都不是好東西,越是接近主流就越容易混帳,他們既無法為世界注入創(chuàng)造力,也給不了女性好的歸宿,只能被欲望操縱像死魂靈一般游走,最終渾渾噩噩的死去。而最令人絕望的莫過于,即便本質(zhì)上是好人的賈寶玉,在對待女性上也有其天花板,金釧因其而死,縱然事后獨(dú)自一人為其哀悼,但過后該調(diào)戲丫鬟繼續(xù)調(diào)戲丫鬟,再難見到想念金釧的痕跡。晴雯被趕出去時即便對襲人有所懷疑,但三言兩語以后就不再深究此事。深怕其寒了心,紅樓中最多情,最體恤女性的寶玉尚且如此,更何況其他那些色欲頑主呢?
而作為男人附庸的女性,在整體上比男人墮落速度倒是更慢,盡管也在向走狗與綿羊演變——后者用寶玉的話來形容,便是從珍珠變成死魚眼睛。整部紅樓夢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便莫過于以林黛玉為首的大觀園中的小姐丫鬟們,作者傾盡心血刻畫這群人物,不僅是因為其有對小時候一起生活的人物原型的思念與追憶,更重要的是這群鎖在深閨正當(dāng)青春年華的女子,還沒有被外界污染的年紀(jì),因此尚保留了一份周圍人都已經(jīng)失去的純真,她們沒有自由,一舉一動都要看家長與禮法的眼色,但也因此啼笑皆非地遠(yuǎn)離主流世界,省去了多少煩心事。
盡管我們只能悲觀地預(yù)料到,倘若她們在俗世上走過一遭后,二十年后也無非王夫人、趙姨娘的下場,或是市儈功利,或是缺乏生機(jī),沉沉如死木。但至少在我們永遠(yuǎn)也無法預(yù)料到具體情節(jié)的小說結(jié)局以前,也就是賈府的敗落破滅以前,這些少女還有機(jī)會享受這份奢侈。
用李劼先生的話說,曹雪芹對少女們的缺點(diǎn)多有無言的體諒與包容,反而因為這些小缺點(diǎn)她們因此更像是一群真人,遠(yuǎn)勝于被現(xiàn)實徹底奪去活力的王夫人賈雨村之輩。
倒是李劼先生自己,對寶釵苛刻地過分了,在本書論及寶釵最激烈時仿佛她就是此世之惡,公正地講,就算寶釵在少女當(dāng)中較為庸俗,但體諒一個家境已經(jīng)沒落,地位勢力在四大家族當(dāng)中最低,而不是傳統(tǒng)理解或者李劼先生誤以為最高的年輕女子,父親去世,兄長又靠不住,為自己的未來有所圖謀實在是人之常理,其手段也無非大學(xué)寢室斗爭,連辦公室政治都不到,與王夫人的手段,賈赦的淫亂不可同日而語。
如果說黛玉是曹雪芹心目中最純粹的精神寄托,因此高標(biāo)地像是遠(yuǎn)離人間煙火,那么寶釵就是為生活而一步步妥協(xié)的寫照,是站在另一端的標(biāo)尺。在寶琴她們到來以前,寶釵的地位在小姐們當(dāng)中其實最低,不像黛玉是賈母最寵愛女兒的孩子,寶釵與賈母并沒有直接血緣關(guān)系,其身份只是一個客人,因此對賈府中的人事糾葛,寶釵無不有所留意,隨便一個小丫鬟都知曉其聲音姓名,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生怕哪日過線,活的最累。即便因此顯得功利,但也不曾像大觀園之外的污穢赤裸裸地傷害他人。假設(shè)她是男兒身,肯定比她哥哥更有創(chuàng)造力,做出一番事業(yè),而今卻不得不自我壓抑。
然而兩人的結(jié)果算起來沒有什么不同,都是正當(dāng)?shù)淖非髤s被現(xiàn)實無情地粉碎,在小說中曹雪芹不住地暗示所有人無非是心死或身死的下場,而心死往往更早于身死,而好人,或者說擁有創(chuàng)造力和精神上不肯阿世者更容易走上這么一遭。對此李劼先生總結(jié)的一語中的:紅樓夢是絕望對絕望的自述,它以驚人的氣魄直面死亡,如果說人生就是畏煩悶,那么紅樓夢對死亡的畏懼不是對生命受到威脅——因為人終有一死,而是對靈魂的殘缺感到悲憤。換句話說,正是因為靈魂的闕如,使得時間變成虛無,因為一切都沒有意義,作為倫理實體的善找不到延續(xù)的可能,無法敞開顯明自身,因此只能在永劫輪回里與惡糾纏不清,同歸于盡。
于是,擁有創(chuàng)造力身為貴族的豹與不計利害審美似的豹的精神逐漸滅絕,只有作為順民的綿羊與作為幫兇的走狗活了下來,而如果有機(jī)會綿羊與走狗就會撕下偽裝,化身為豺狼。但是他們活的同樣痛苦,不僅僅是肉體上被侮辱與被損害,而且人格也被反復(fù)踐踏扭曲,畢竟他們大部分時間是沒有機(jī)會化身為豺狼的。而假如里中有曾覺醒者,也不過是對四際無人的曠野大聲呼喊卻得不到回音,大多數(shù)人依舊如蟲豸一般生存,其中苦中作樂者寧肯自我欺騙,也不愿承認(rèn)慘淡的現(xiàn)實,因為誰都希望自己的生命是有意義的,久而久之,他們成功欺騙到了自身。畢竟,將痛苦解釋成幸福,比將幸福真正追求到手,無疑簡單太多。
李劼先生的《論紅樓夢》其實有個副標(biāo)題是歷史文化的全息圖像,這個名字說來不大妥帖,我們固然可以從紅樓夢中見微知著,看到其置身社會的頹唐敗落,然而其所反映的是一個文明的末世景象,它的青春早已結(jié)束,它的現(xiàn)實只是死路一條。所謂凡鳥偏從末世來,哭向金陵事更哀。在此之后要么繼續(xù)死而不僵,要么迎接新生。所有人都希望劫灰落地以后可以開始新的輪回,可將希望想象成現(xiàn)實,也無疑比把希望演變成現(xiàn)實簡單太多。

分享到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