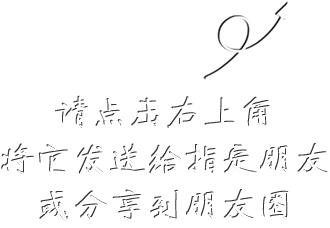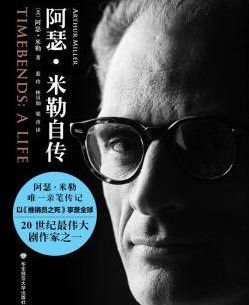

申慧輝/文
米勒(1915-2005)在1987年出版自傳時(shí)已年過七旬。他32歲時(shí)憑借《都是我的兒子》(1947)享譽(yù)美國(guó)劇壇,兩年之后又以《推銷員之死》摘得包括托尼獎(jiǎng)、普利策獎(jiǎng)、和紐約劇評(píng)界獎(jiǎng)在內(nèi)的美國(guó)數(shù)項(xiàng)重要話劇大獎(jiǎng),成為戰(zhàn)后美國(guó)劇壇著名的三杰之一。緊接著,美國(guó)在50年代麥卡錫主義橫行,大批思想左傾的作家和藝術(shù)家遭到政治迫害,這位倔強(qiáng)的猶太藝術(shù)家因拒絕向強(qiáng)權(quán)制度低頭,雖被判罪,卻贏得尊敬,成為美國(guó)“劇壇良心”的象征性人物。60年代,米勒出任國(guó)際筆會(huì)主席,為作家的思想自由和創(chuàng)作自由奔走呼吁,進(jìn)一步奠定了他在國(guó)際文壇的地位。此前,米勒和著名影星瑪麗蓮·夢(mèng)露戀愛、結(jié)婚,遂又離婚,不久后瑪麗蓮·夢(mèng)露自殺身亡。這些私人經(jīng)歷又使米勒成為社會(huì)公眾關(guān)注的對(duì)象。70年代,中國(guó)改革開放,米勒訪華并出版紀(jì)實(shí)文學(xué)《中國(guó)經(jīng)歷》,用他的文字將中美之間的大門進(jìn)一步打開。80年代初,米勒重返中國(guó),與北京人民藝術(shù)劇院合作,親自導(dǎo)演其名劇《推銷員之死》。美國(guó)數(shù)家電視臺(tái)亦同時(shí)進(jìn)入北京,專門報(bào)道首演盛況,使之成為中美文化交流甚至外交上的重大事件,再次引起國(guó)際轟動(dòng)。幾乎每一個(gè)十年里,米勒都在他的履歷中不斷增加豐富的內(nèi)容,他的自傳因此也成為一個(gè)包含了政治風(fēng)波,社會(huì)變化,文化事件,名人軼事,乃至娛樂八卦的各種故事綜合體,猶如一部二十世紀(jì)美國(guó)社會(huì)生活的小百科,而且相當(dāng)富有文藝范兒。
“自由聯(lián)想”的敘事結(jié)構(gòu)
說到文藝范兒,主要是自傳運(yùn)用了“自由聯(lián)想”的敘事結(jié)構(gòu)。這種“自由聯(lián)想”的方式不僅豐富了內(nèi)容,也打破了單一的線性敘述可能產(chǎn)生的單調(diào),在以時(shí)間為序的敘事架構(gòu)中,增強(qiáng)了自傳的藝術(shù)張力,提升了閱讀效果。從第一章開始,米勒便選擇了藝術(shù)范兒的“自由聯(lián)想”,賦予自傳一種詩意的自由. 米勒還就敘述的視角大做文章。自傳第一章中出現(xiàn)的第一個(gè)詞就是“視角”。而且這個(gè)詞在接下來的三段里,均作為第一個(gè)句子中的關(guān)鍵詞一再重復(fù)。首先,它生動(dòng)地展現(xiàn)了童年時(shí)的作者是如何趴在地板朝上仰視母親,之后又是如何在兩英尺的高度、五英尺的高度、以及最后從成人的視角來觀察世界;于此同時(shí),“視角”一詞婉轉(zhuǎn)地提示讀者:傳記的寫作角度是相當(dāng)個(gè)人化的,因此敘述的視角不僅是主觀的,也必定是有局限性的。“自由聯(lián)想”使記憶在米勒的意識(shí)中任意穿梭流淌,時(shí)而沖向兒時(shí)經(jīng)歷的沙灘,時(shí)而涌向堆滿陳年往事的彼岸;遂使這部長(zhǎng)達(dá)600多頁的自傳得以充分承載米勒豐富的一生,尤其是作者本人視作最為重要的人生經(jīng)歷,如家庭的影響,時(shí)代的痕跡,事業(yè)的追求,以及國(guó)際的視野。
影響米勒一生的猶太家庭背景
作為話劇藝術(shù)家,米勒生活在富人聚集的紐約和康州,奔波于百老匯和好萊塢等五色迷離的演藝界,卻能堅(jiān)持個(gè)人的藝術(shù)理想和追求,這本身便是相當(dāng)不尋常的。追根溯源,他在童年經(jīng)歷的美國(guó)經(jīng)濟(jì)大蕭條,家族生意的破產(chǎn),以及生活中的巨大變動(dòng),均對(duì)他影響深遠(yuǎn);甚至可以說,美國(guó)夢(mèng)的虛偽和傷痛早在他少年時(shí)代就已經(jīng)被親身體驗(yàn)和領(lǐng)悟了。
影響米勒一生的不僅是經(jīng)濟(jì)大蕭條以及當(dāng)時(shí)紛繁復(fù)雜的社會(huì)思潮,另一個(gè)重要因素就是他的猶太家庭背景。在他的記憶里,爸爸在教堂里態(tài)度嚴(yán)肅,媽媽時(shí)而會(huì)打盹,太爺爺則對(duì)所有教會(huì)活動(dòng)充滿敬意。有時(shí)候,教堂的大門會(huì)被關(guān)上,摩西五經(jīng)的經(jīng)卷被輕輕展開,然后,太爺爺和其他人一起,莊嚴(yán)肅穆地等待經(jīng)卷被拿到面前,遂上前輕輕撫摸并親吻經(jīng)卷。米勒還要和弟弟一起學(xué)希伯萊文,盡管他很少能理解文中真意,但只要背誦下課文,就會(huì)受到老師的贊賞,得到一個(gè)親吻。猶太大家庭給予他的另一個(gè)教育是關(guān)于死亡。長(zhǎng)輩們離世,孩子們都要從始至終參加葬禮全過程。有時(shí)候,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見到這位親戚。這些經(jīng)歷,正如米勒回憶的,對(duì)他后來創(chuàng)作《維希事件》和《代價(jià)》等劇本均有直接的影響。
從精神層面上講,猶太教對(duì)米勒的影響遠(yuǎn)遠(yuǎn)超過當(dāng)代讀者的想象。例如,在西方廣泛流傳的陰謀論和流行小說里,常常可以讀到關(guān)于某些秘密組織的神秘儀式,卻很難找到第一手資料來證明這些情節(jié)來源的真?zhèn)巍S腥さ氖牵桌赵谧詡髦袑?duì)類似場(chǎng)面有一段生動(dòng)的描寫。他兒時(shí)經(jīng)常和喜愛他的太爺爺一起去教堂,其中有一次不同于往常。那天,太爺爺要他靜靜地坐在長(zhǎng)椅上,閉上眼睛,然后再用手捂上,然后太爺爺自己脫下鞋子,只穿著白色的襪子,離開座位去加入一群他的同齡人。被單獨(dú)留在教堂的長(zhǎng)座椅上,米勒不免心中忐忑。他悄悄透過“指縫和眼睫毛”向外觀望,竟然看到太爺爺他們?cè)趪梢蝗Γ?ldquo;所有人都穿著白襪子”,口中吟誦著曲調(diào),手舞足蹈地“正在跳舞!”更令他驚訝的是,“他從來沒有聽到過那樣的音樂,如此奔放和瘋狂”。太爺爺他們仿佛“在對(duì)著包圍他們的外部黑暗跳舞,超越了家庭和人群,對(duì)著能夠傾聽祈禱的空間”。迷信也好,信仰也好,這些難忘的兒時(shí)經(jīng)歷必定直接或間接地建構(gòu)了米勒的精神世界,成為他日后精神力量的奠基石。
“不確定”的年輕時(shí)代
談到青年時(shí)代求學(xué)和打短工的經(jīng)歷時(shí),米勒特意借用《推銷員之死》威利的臺(tái)詞,說年輕的他“還不確定”,仍在摸索。的確,開始嘗試寫作的青年米勒,一如兒時(shí)的他,依舊關(guān)注社會(huì)與人生,而這種思想上的探索在他整個(gè)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從未停止過。例如,關(guān)于接觸左傾思想的緣由,米勒寫到,他那時(shí)參加紐約著名的記者聚會(huì),因?yàn)樗湍切﹨⒓蛹瘯?huì)的多數(shù)人一樣,為社會(huì)上“當(dāng)時(shí)的無知主義而不安”。他們?cè)诿恐艿木蹠?huì)上聆聽見多識(shí)廣的大牌記者講話,其中有為人熟知的埃德加·斯諾,約翰·赫西,以及《紐約人》,《讀者文摘》,以及《生活》等雜志的編輯。后來,參加集會(huì)的人擴(kuò)大到同樣關(guān)心社會(huì)走向的律師和商人。米勒還專門提到當(dāng)時(shí)各種思潮均十分活躍,他們甚至還收到過一位俄亥俄州作家寫來的信,同他們辯論,指責(zé)他們是在“從事共產(chǎn)主義陰謀”。另一次,也是在紐約,米勒得以和前蘇聯(lián)藝術(shù)家開會(huì),并聽到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的刻板發(fā)言。可惜這些關(guān)于意識(shí)形態(tài)的公開交流過于短暫,很快冷戰(zhàn)氣氛加劇,麥卡錫主義橫行,集會(huì)被迫中斷。不過,米勒始終認(rèn)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信仰,就如佛教或伊斯蘭教,是認(rèn)識(shí)世界的工具,而不是目的。
此外,在戲劇創(chuàng)作過程中,米勒接觸并結(jié)識(shí)了一批當(dāng)時(shí)活躍在紐約的左翼藝術(shù)家,包括著名的克里夫特·奧德茨,麗蓮·海爾曼,諾曼·梅勒。米勒說,盡管這些人當(dāng)時(shí)似乎并不把他放在眼里,甚至后來依舊不把他放在眼里(這種說法暗示他和這些左派藝術(shù)家是有思想差異的),但是與這些藝術(shù)家的交往,使他有機(jī)會(huì)親歷不同思想的交鋒,促進(jìn)了他的戲劇創(chuàng)作。例如奧德茨。這位當(dāng)時(shí)著名的左翼劇作家曾經(jīng)是米勒相當(dāng)欽佩的人。奧德茨的革命呼吁是那么地激動(dòng)人心,令人熱血沸騰。在青年米勒的心中,奧德茨的《等待老左》,就好像代表了“暴風(fēng)雨中工人階級(jí)的海燕”,是一個(gè)“全新的現(xiàn)象”,象征了“一個(gè)左派對(duì)社會(huì)制度的挑戰(zhàn)”。不過米勒的探索精神使他不滿足這樣的簡(jiǎn)單認(rèn)識(shí),因此在努力學(xué)習(xí)借鑒其他劇作家的同時(shí),他開始比較奧德茨與奧尼爾和威廉斯。
尤金·奧尼爾和田納西·威廉斯是后來和米勒一起,被稱作當(dāng)時(shí)美國(guó)話劇舞臺(tái)上的三杰。 與這兩位劇作家比較,米勒得到的領(lǐng)悟是,奧德茨筆下的人物是“無法進(jìn)入體制”的“異化的”人;而奧尼爾筆下的人物則是在“極力從體制中脫身出來”,并想“拋棄所有那些自吹自擂的自我喝彩”的人。因此,奧德茨只不過是具有“階級(jí)意識(shí)”,并企圖“用社會(huì)主義去改造資本主義”;而奧尼爾則已經(jīng)對(duì)“資本主義不抱任何希望”。因此,雖然奧尼爾從不談?wù)擇R克思主義,但他是真正反對(duì)資本主義的。對(duì)于威廉斯,劇評(píng)界一向論說紛紜。米勒在自傳中的評(píng)價(jià)則簡(jiǎn)明而中肯。他認(rèn)為威廉斯的創(chuàng)作賦予了話劇難得具有的“詩意”,而且還“有勇氣”去接觸同性戀題材,這兩點(diǎn)在當(dāng)時(shí)的美國(guó)均屬難能可貴。涉獵廣泛的米勒還在自傳中多次談及契柯夫,易卜生,莎士比亞,妥思托耶夫斯基,托爾斯泰,惠特曼,懷爾德等作家藝術(shù)家, 顯示了他的藝術(shù)視野的國(guó)際化;在精神層面上,他提及最多的是夢(mèng)露,麥卡錫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這些應(yīng)是對(duì)他影響最大的人與事。
《推銷員之死》:“亞當(dāng)”式的人類代表
至于米勒本人的創(chuàng)作,自傳中提到了所有作品,而提及最多的是《推銷員之死》。這不僅是一部被譽(yù)為二十世紀(jì)美國(guó)話劇經(jīng)典的作品,也是米勒和中國(guó)的重要紐帶,并為他帶來持續(xù)的國(guó)際聲譽(yù)的重要成就。晚年的米勒似乎依然念念不忘《推銷員之死》。在他看來,此劇的成功為他證明了一個(gè)信念:優(yōu)秀的劇作承載的是人性以及關(guān)于人性的揭示。他最初設(shè)想的威利·洛曼是一個(gè)“底層人”,他充滿疑惑和恐懼,大聲呼救卻無人回應(yīng);后來他成為一個(gè)象征:人與社會(huì)是無法分割的整體,人的命運(yùn)取決于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最后,當(dāng)威利的形象跨越國(guó)界走入不同文化并被廣泛接受時(shí),他已然成為“亞當(dāng)”式的人類代表。威利的死也同樣具有象征意義。他的妻子和兩個(gè)兒子,包括他本人,都在試圖弄明白他這個(gè)開朗善談追求成功的人為何要自殺。根據(jù)米勒的理解,威利的死因不僅是他的心理問題,更是造成這種心理的社會(huì)意識(shí)形態(tài)。的確,此劇曾被形容為一顆埋在美國(guó)資本主義大廈下的定時(shí)炸彈,的確有其道理。
在中國(guó),上演《推銷員之死》同樣具有時(shí)代意義。時(shí)為1983年,我國(guó)改革開放不久,文化還處于百廢待興的階段。米勒的導(dǎo)演為我國(guó)話劇舞臺(tái)帶來一股新鮮與活力。他從表演到舞美,事事過問。無論是布景設(shè)計(jì),燈光服裝,還是演員的化妝,他都一絲不茍。即使多年后,他的指導(dǎo)仍令人難忘。米勒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劇本的主題跨越國(guó)界和民族,因此演出時(shí)不要戴假發(fā),不要演外國(guó)人,要演你們自己。米勒對(duì)劇本主題的挖掘和獨(dú)特的導(dǎo)演風(fēng)格令人耳目一新,拓寬了演員的視野,也將《推銷員之死》的普遍意義永久地留在了中國(guó)。
對(duì)于米勒的故國(guó),又何嘗不是。年復(fù)一年,在哈佛大學(xué)等美國(guó)的高等學(xué)府里,《推銷員之死》作為文化歷史教材,被莘莘學(xué)子反復(fù)閱讀;與此同時(shí),他們也閱讀著這部自傳。和我們這些普通讀者一樣,他們會(huì)在自傳結(jié)尾處,讀到米勒的追問:“我到底是誰?”也許,讀者都會(huì)被這句追問所震撼,并因此停一下匆匆的步履,和米勒一起,去想一想人生和社會(huì),乃至和威利經(jīng)歷相似的、構(gòu)成我們自己人生的那些追求,困惑和恐懼,追問一句:我(們)到底是誰。

分享到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