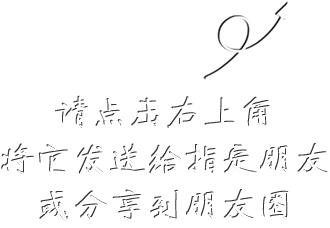那是湖上翩翩起舞的一只白天鵝,半個(gè)世紀(jì)來(lái)不常想起但也從未忘記。
一
我走出左右兩邊佇立著沉默石獅的大門(mén),中午的街道很清靜,幾個(gè)老人坐在街邊樹(shù)蔭下擺開(kāi)巨大的棋盤(pán),他們每天都在這里下象棋,成為街景的一部分。我在溫暖陽(yáng)光下漫無(wú)目的,想不出要去哪里。在記憶里,這一場(chǎng)景反復(fù)出現(xiàn),漸漸構(gòu)成了一種象征。一直輟學(xué)在家的我,從小就習(xí)慣每天起來(lái)不知道要干什么,但又在幻想里做許多事。時(shí)間和太陽(yáng)一道緩慢地移動(dòng),夜色掩蓋白晝,樓影樹(shù)影仿佛吞沒(méi)了陽(yáng)光下發(fā)生的一切。第二天,太陽(yáng)照樣升起。
由于在八十年代被認(rèn)定為國(guó)家級(jí)文物保護(hù)單位,位于張自忠路三號(hào)、原鐵獅子胡同一號(hào),被稱為“鐵一號(hào)大院”的段祺瑞執(zhí)政府得以大致保留原狀,這在近四十年天翻地覆的北京屬于異數(shù)。2016年的某一天,我曾經(jīng)回到那里,熟悉的風(fēng)景足以激活久已淡忘的記憶。
執(zhí)政府主樓是北京少見(jiàn)的而且保存完好的大型哥特式建筑,我小時(shí)候住的紅磚樓則是五十年代的宿舍樓,雖然質(zhì)地厚重,但在美學(xué)上乏善可陳。這種據(jù)說(shuō)來(lái)自前蘇聯(lián)式樣的樓房在那時(shí)隨處可見(jiàn),如今絕大多數(shù)都已經(jīng)拆除,這三棟樓卻十分幸運(yùn),沾了執(zhí)政府的光得以保存。我走上紅樓頂?shù)木薮笃脚_(tái),除了稀稀落落的幾根晾衣繩一片空曠。我忽然看見(jiàn)一個(gè)穿白襯衫和一條洗得發(fā)白的舊灰色瘦腿褲的女孩,在平臺(tái)中央隨著《天鵝湖》的音樂(lè)翩翩起舞。
在六七十年代走出執(zhí)政府大門(mén),如今寬闊的平安大道還是一條窄窄的林蔭道。馬路對(duì)面是13路公共汽車(chē)站,這里現(xiàn)在仍然是公交車(chē)站。往東不遠(yuǎn)是13路無(wú)軌電車(chē)站,然后就是與東四北大街相交的十字路口了。從北向南的六路無(wú)軌電車(chē)后來(lái)改成106路,兩站到東四,那里有兩個(gè)電影院,一個(gè)是東四電影院、一個(gè)是隆福寺劇場(chǎng)。在沒(méi)有電視的時(shí)代,電影院是孩子眼中最迷人的地方。即使我的童年沒(méi)有幾部電影可看,每次走進(jìn)電影院,當(dāng)燈光轉(zhuǎn)暗,音樂(lè)響起,我仍然會(huì)激動(dòng)不已。
“面包會(huì)有的,牛奶會(huì)有的,一切都會(huì)有的。”瓦西里的臺(tái)詞之所以膾炙人口,是因?yàn)楫?dāng)時(shí)不僅電影,面包與牛奶也近乎沒(méi)有,匱乏里的印象就格外深刻。八歲時(shí),我在東四電影院看《列寧在1918》,因?yàn)閭€(gè)子小,把哥哥和我自己的棉猴疊起來(lái)墊在座位上坐著看。有一段時(shí)間,電影院里只有《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1918》兩部外國(guó)電影,后者被普遍認(rèn)為更好看,多半是因?yàn)槔锩嬗幸恍《伟爬傥琛短禊Z湖》,在革命年代,露大腿的芭蕾舞無(wú)疑是禁忌,僅僅因?yàn)楦街谝徊扛锩娪吧喜庞锌赡懿コ觥?jù)說(shuō)有很多電影院在放映時(shí)刪去了這一段,但我看到的是未刪節(jié)本。至今記憶清晰的是看到天鵝起舞時(shí)后面有人很不以為然地說(shuō)“怎么放這個(gè)?”我大叫一聲:“看的就是這個(gè)!”一片哄笑中,輕盈的白天鵝就消失了。
二
早年的影像記憶,往往對(duì)一個(gè)人的歷史觀有著很深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很多人窮其一生也不曾認(rèn)識(shí)到,年少時(shí)不自覺(jué)接受的印象也許并不怎么真實(shí)。
整整一百年前的1918年,在歷史上十分重要,但并不是因?yàn)榱袑帯_@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國(guó)際政治版圖重組;帝國(guó)坍塌,一片廢墟,各方逐鹿,新人輩出。社會(huì)黨人、民族主義者;軍事強(qiáng)人、民粹領(lǐng)袖等等不一而足。雖然也有幾場(chǎng)革命,但大多數(shù)不成氣候,只有前一年的俄羅斯革命存活了下來(lái)。歷史上后來(lái)變得無(wú)比重要的事件,在發(fā)生當(dāng)時(shí)往往并沒(méi)有得到太多重視。而且1918年的蘇維埃共和國(guó)確實(shí)風(fēng)雨飄搖,列寧遇刺只是其中事件之一。二月革命時(shí)攜手推翻沙皇的幾個(gè)黨派很快就反目成仇,那一年俄羅斯政權(quán)脆弱,政變頻仍,都不怎么血腥,更多是一哄而起的偶發(fā)事件,最后才是居于少數(shù)的布爾什維克奪取了政權(quán)。列寧后來(lái)被尊為偉大導(dǎo)師是由來(lái)有自的:他敏銳地察覺(jué)到民心厭戰(zhàn),于是冒天下之大不韙與德國(guó)簽訂城下之盟,贏得了鞏固政權(quán)的時(shí)間;他斷然實(shí)施革命的鐵腕,外建紅軍、內(nèi)組契卡,無(wú)論是對(duì)昔日的盟友還是對(duì)沙俄殘留的軍閥都毫不留情。電影中的刺客卡普蘭和高喊“讓列寧同志先走”的諾維科夫并非十惡不赦的反革命,而是同樣激進(jìn),不久前還并肩戰(zhàn)斗的社會(huì)革命黨人。
那幾年歐洲的中心話題是凡爾賽和約、魏瑪共和國(guó)、國(guó)聯(lián)(國(guó)際聯(lián)盟)等等,俄羅斯還是一個(gè)邊遠(yuǎn)的存在。多少因?yàn)槿绱耍K維埃政府經(jīng)過(guò)三年內(nèi)戰(zhàn),把各自割據(jù)的白俄軍閥分別擊破。在這個(gè)過(guò)程里立下大功的首推托洛茨基和捷爾任斯基,然而在《列寧在1918》的電影里,當(dāng)時(shí)并不重要的格魯吉亞人占據(jù)了主要位置。
被清洗后來(lái)又被暗殺的托洛茨基電影里自然不會(huì)提,留胡子穿皮夾克看上去很酷的捷爾任斯基在1926年逝去,他一手創(chuàng)立的契卡卻繼續(xù)壯大,在前蘇聯(lián)一直是最有權(quán)勢(shì)的部門(mén)。革命的嚴(yán)酷也就一直繼續(xù),其影響遍及整個(gè)共產(chǎn)主義陣營(yíng)。中國(guó)從三十年代的肅反到文革,在一定程度上也都有前蘇聯(lián)的影子。
友人轉(zhuǎn)來(lái)一篇關(guān)于人民大學(xué)副校長(zhǎng)孫泱一家文革中遭遇的文章。孫泱是中共早期烈士、北伐時(shí)國(guó)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shū)長(zhǎng)、朱德?lián)从褜O炳文之子,著名演員、周恩來(lái)養(yǎng)女孫維世之兄,曾經(jīng)擔(dān)任朱德秘書(shū),1964年調(diào)入人民大學(xué),1967年被迫害致死。他究竟死于他殺還是自殺,至今沒(méi)有定論。雖然當(dāng)時(shí)宣布的結(jié)論是自殺,然而孫泱人高馬大,如何在很低的暖氣管上自縊,是相當(dāng)難以解釋的。孫維世第二年被捕,在獄中被活活打死。
孫泱到人大時(shí)我父親已離開(kāi)人大,所以彼此沒(méi)有交集并不熟悉。不過(guò)父親在人大多年,調(diào)離后家也沒(méi)有搬走,與舊日同事過(guò)從頗多。孫泱是文革中第一個(gè)被迫害死的人民大學(xué)負(fù)責(zé)人。
孫泱去世幾年后,遺孀石琦和女兒孫冰帶著兩個(gè)弟弟流寓在鐵獅子胡同一號(hào)大院。他們搬來(lái)的時(shí)候我已經(jīng)搬離,所以我并不認(rèn)識(shí)他們,只是聽(tīng)到有關(guān)的傳說(shuō)。我聽(tīng)說(shuō)孫冰是聞名遐邇的美女,卻不確知究竟曾否見(jiàn)過(guò)她。后來(lái)我邂逅她的一個(gè)女友,告訴我她還是個(gè)孩子頭,很有女俠氣,或許是逆境中逼出來(lái)的吧。我確知的是,在某個(gè)夜晚,當(dāng)我回故居找舊日小伙伴時(shí),遇見(jiàn)孫泱之子,文靜秀氣,坐在一個(gè)角落一言不發(fā),看上去有點(diǎn)憂郁,在一片鬧騰的氛圍里格外引人注目。幾年前友人告訴我他現(xiàn)在完全不是這個(gè)樣子,我想這也是再正常不過(guò)的,歲月在太平盛世中流逝,時(shí)代的變遷不僅僅呈現(xiàn)在每個(gè)人衣著的變化上。再說(shuō)我也并不介意是否面目全非,一個(gè)時(shí)代的嚴(yán)酷與苦難,無(wú)論愿意或不愿意,依然會(huì)深深留下痕跡,既使不再提起,也會(huì)部分流傳。這是歷史的力量,或者說(shuō)是關(guān)于歷史的一種信念。
鐵獅子胡同一號(hào)大院的發(fā)小們聚集在一起時(shí),不少人會(huì)有打撈往事的愿望。這也從側(cè)面反映出關(guān)于文革的記憶對(duì)許多人影響深遠(yuǎn)。令人惶惑的是,許多共同經(jīng)歷的記憶開(kāi)始模糊甚至互相矛盾,歷史敘述的不確定性與邊界或在于此。
三
七十年代的北京生活其實(shí)很無(wú)聊,只有八個(gè)樣板戲、十幾部電影,絕大多數(shù)書(shū)籍都成了禁忌。年少時(shí)的娛樂(lè),不過(guò)是打撲克、下棋、玩煙盒、打彈球。我很幸運(yùn),家里的書(shū)抄家時(shí)沒(méi)有被抄走,兄長(zhǎng)朋友們又經(jīng)常在地下傳閱各種書(shū),日子平淡無(wú)奇,節(jié)奏緩慢,沒(méi)有留下痕跡,只有讀過(guò)的一些書(shū)至今還沒(méi)有忘記。其中我非常喜歡的一本是海明威的《永別了,武器》,第一次讀這部小說(shuō)時(shí),我應(yīng)該還不到13歲,但已經(jīng)隱隱約約感覺(jué)到死亡的殘酷與愛(ài)情的美好,形成強(qiáng)烈的對(duì)比。后來(lái)我又讀過(guò)至少兩遍,每次讀到凱瑟琳臨死前說(shuō)的最后一句話時(shí)都會(huì)熱淚盈眶:
“別擔(dān)心,親愛(ài)的,”凱瑟琳說(shuō)。“我一點(diǎn)也不害怕。人生只是一場(chǎng)卑鄙的騙局。”
海明威就出生在芝加哥近郊的橡園鎮(zhèn)(Oak Park,音譯奧克帕克),我剛到芝加哥時(shí),去瞻仰過(guò)他的故居:一幢簡(jiǎn)單古樸的房子,舊家具、發(fā)黃的手稿和老照片有一種安詳悠遠(yuǎn)的氣息。上個(gè)世紀(jì)初,這里是一個(gè)規(guī)行矩步,蒸蒸日上的中產(chǎn)階級(jí)小鎮(zhèn)。海明威在這里成長(zhǎng),但是他并不屬于這里,出走后就再也沒(méi)有回來(lái)。海明威的一生,在作家里絕對(duì)屬于豐富多彩的:戰(zhàn)爭(zhēng)、革命、探險(xiǎn),樣樣不拉;雪茄、女人、航海,從未閑著。他一生結(jié)了四次婚,感情經(jīng)歷和話題都很豐富;他是個(gè)敏感的人,也很自我中心,行事捉摸不定。海明威研究因此一直是顯學(xué),無(wú)論嚴(yán)肅評(píng)論還是八卦緋聞。
然而一個(gè)作家的偉大終究是由于作品,其余不過(guò)浮云。《永別了,武器》是最感動(dòng)我的反戰(zhàn)小說(shuō),里面不僅僅是真實(shí)的殘酷,還有虛構(gòu)的愛(ài)情。在這一點(diǎn)上,它比《西線無(wú)戰(zhàn)事》更為動(dòng)人好看。事實(shí)上,我最喜歡的雷馬克小說(shuō)是《里斯本之夜》,同樣是戰(zhàn)爭(zhēng)中的愛(ài)與死,動(dòng)蕩里的個(gè)人命運(yùn)就如同茫茫大海上一葉扁舟,隨著波濤起伏,不管怎樣掙扎,最終無(wú)能為力。
海明威在1929年寫(xiě)的《永別了,武器》是他的成名作,和之前的《太陽(yáng)照常升起》并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迷失的一代”代表作。一戰(zhàn)與二戰(zhàn)不同,爆發(fā)于偶然而不可收拾,最終沒(méi)有贏家也沒(méi)有正義。一戰(zhàn)之前的二十世紀(jì)初,工業(yè)革命帶來(lái)生活的巨大變革,繁榮與發(fā)展似乎是一個(gè)既定方向,歐洲人對(duì)未來(lái)滿懷信心,對(duì)自己的價(jià)值觀深信不疑。“迷失的一代”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西方的第一次坍塌,在原有的政治正確廢墟上,國(guó)家主義與民粹等混成的怪胎,先是意大利的法西斯,后有德國(guó)納粹。在國(guó)際地緣本來(lái)的邊緣地帶上,興起了巨大的紅色蘇聯(lián)。
海明威、雷馬克以及我以前寫(xiě)過(guò)的茨威格等許多二十世紀(jì)上半葉作家都不是書(shū)齋中人,而是為和平、自由與進(jìn)步奔走呼喊者,然而他們那一代作家面對(duì)納粹法西斯極權(quán)主義的興起無(wú)可奈何。他們預(yù)見(jiàn)黑暗,卻只能和時(shí)間一起緩緩步入黑夜。這或許是他們當(dāng)中,不少人未能如后來(lái)的大作家那樣生活理性、壽終正寢的原因吧。雖然二戰(zhàn)以正義戰(zhàn)勝邪惡、光明戰(zhàn)勝黑暗告終,然而深淵的陰影往往伴隨人的一生。海明威在1961年用一桿雙管獵槍炸碎了自己的頭,死得很勇敢也很瘋狂。
四
十多年前我曾經(jīng)開(kāi)車(chē)去很遠(yuǎn)的地方看一場(chǎng)俄羅斯芭蕾舞團(tuán)演出的《天鵝湖》,不知是因?yàn)槠诖撸€是由于前蘇聯(lián)解體后國(guó)家芭蕾舞體制崩壞,舞團(tuán)四分五裂,普遍水準(zhǔn)下降,反正是沒(méi)有什么感覺(jué)。回家路上,我不禁開(kāi)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已經(jīng)老了,失去了對(duì)人生的敏感?
《列寧在1918》里的芭蕾舞鏡頭在我的童年里是如此印象深刻,年少時(shí),白天鵝曾常在夢(mèng)中縈繞,或許在不知不覺(jué)間影響了審美觀的成形。我已經(jīng)想不起是在哪里聽(tīng)的,但仍然能夠感受到第一次聽(tīng)《天鵝湖》黑膠時(shí)的美妙。如今我的地下室里有不下十個(gè)《天鵝湖》黑膠版本,由穆拉文斯基、安塞美這樣的大指揮家指揮的,卻沒(méi)有那時(shí)的感覺(jué)了。
發(fā)小中沒(méi)有誰(shuí)記得曾經(jīng)有一個(gè)女孩在紅樓的樓頂平臺(tái)上跳《天鵝湖》,我不知道是自己記憶有誤,還是出自童年時(shí)的一種向往、一次想象。也許我把白天鵝幻化成了一個(gè)想象中的女孩,有時(shí)人在潛意識(shí)里有一種模糊現(xiàn)實(shí)與期望的傾向,自己相信的真實(shí)可能并沒(méi)有發(fā)生過(guò)。不過(guò)我確信真實(shí)的是八十年代初的一個(gè)夜晚,第一次看《天鵝湖》全劇,散場(chǎng)后和一個(gè)女孩在北京展覽館樹(shù)叢掩映背后的回廊坐了很久。那是我曾經(jīng)認(rèn)識(shí)的跳芭蕾舞女孩,至今清晰記得她曼妙的舞姿。那時(shí)我就常唱舒伯特的《菩提樹(shù)》:“也曾在那樹(shù)干上,刻下熱情詩(shī)句,歡樂(lè)痛苦的時(shí)候,我常走近這樹(shù)”。然而青春熱情,難免無(wú)疾而終;曾以為刻骨銘心的瞬間,多半在時(shí)光里風(fēng)化。現(xiàn)在唱《菩提樹(shù)》,最后一段比從前唱得輕而自然:“如今我遠(yuǎn)離故鄉(xiāng),往事念念不忘,我分明聽(tīng)見(jiàn)它說(shuō),在這里長(zhǎng)安樂(lè)”。想象終竟是鏡花水月,大約二十年后,幻化成《美國(guó)往事》里的一段回憶;半個(gè)世紀(jì)后的今天,我坐在濱海的房間里,這是一個(gè)多云的黃昏,隱約有海浪拍岸的聲音。西望太平洋和故國(guó)的方向,但見(jiàn)海天一色,空無(wú)一人。
雖然從佛學(xué)上講,沒(méi)有分別、一片空曠更接近世界的本相,不過(guò)我素不敢以有緣法自居,更傾向于凡人的使命還是在于找尋真實(shí)。我們所經(jīng)歷的時(shí)代和我們所了解的歷史,有太多其實(shí)我們并不知道的事情,或者因?yàn)槿鄙訇P(guān)注,或者由于被湮沒(méi)與遺忘。在2018年想起《列寧在1918》,關(guān)于一個(gè)世紀(jì)之前的世界,我們究竟還知道多少?在經(jīng)濟(jì)高速成長(zhǎng)、生活快餐節(jié)奏的當(dāng)下,半個(gè)世紀(jì)前的親身經(jīng)歷,我們又還想得起多少?
二戰(zhàn)確立了新的政治正確,也開(kāi)始了冷戰(zhàn)。一邊是新興的社會(huì)主義陣營(yíng),一邊是重建的自由民主世界。狂熱獻(xiàn)身是植于人性深處的沖動(dòng),堅(jiān)信不疑是維系社會(huì)安寧的需要。敏感的文學(xué)家一生多半處于夾縫之中,他們更多感受到人性的可疑、世界的不確定性而又無(wú)能為力。《永別了,武器》和《西線無(wú)戰(zhàn)事》甫經(jīng)發(fā)表就洛陽(yáng)紙貴,早在三十年代初就翻譯成中文。前者有一個(gè)很鴛鴦蝴蝶的名字:戰(zhàn)地春夢(mèng),這個(gè)譯名大約更適合當(dāng)時(shí)大眾品味,很得流行演義小說(shuō)的神韻,也折射出譯者的理解。然而愛(ài)情在《永別了,武器》并非一種流行元素,而是與戰(zhàn)爭(zhēng)、死亡對(duì)抗的另一極。視之為“春夢(mèng)”,多少忽略了作者的寄托與小說(shuō)的力量。是的,文學(xué)與歷史是無(wú)用之學(xué),從來(lái)不足以改變現(xiàn)實(shí),在崇尚實(shí)際的商業(yè)時(shí)代人們更多離之遠(yuǎn)去。然而文學(xué)中的美感、歷史中的真實(shí),是心靈史與事件史的記錄,比物質(zhì)世界留存得更為長(zhǎng)久,構(gòu)成一個(gè)時(shí)代傳承的根本。
大多數(shù)人的歷史認(rèn)知,來(lái)自教科書(shū)、文學(xué)、電影及其他,很少來(lái)自歷史著作本身。對(duì)于我來(lái)說(shuō),文學(xué)不僅是一種歷史認(rèn)知,更是一種坐標(biāo)。日常歲月大半是平淡的,歷史真相往往是冷酷的,而文學(xué)不管怎樣寫(xiě)實(shí)或悲觀,總會(huì)是有溫度的,何況一個(gè)人完全可以心中悲哀,卻仍然滿懷希望。自然,希望很可能是虛妄的,理想主義沖動(dòng)被利用成為瘋狂在歷史上屢見(jiàn)不鮮。不過(guò)每代人都有自己無(wú)法逾越的局限性,我們自出生而逐漸形成的思維慣性,注定了必須有所寄托的命運(yùn),注定了要去尋找心中不會(huì)消逝的象征。很難說(shuō)這到底是堅(jiān)守信念還是逃避真相,有時(shí)也可能兼而有之。冷戰(zhàn)結(jié)束后的四分之一世紀(jì)里,這個(gè)世界似乎有了方向。沒(méi)有誰(shuí)意識(shí)到,二戰(zhàn)以來(lái)的政治正確其實(shí)在緩緩坍塌。在本以為會(huì)是一派祥和的2018年,人們發(fā)現(xiàn)歷史并未終結(jié),動(dòng)蕩與沖突的可能性并未減低;意識(shí)形態(tài)雖然不再分明,價(jià)值觀的混亂卻似乎與日俱增。一方面,半個(gè)多世紀(jì)的和平讓世界前所未有地富庶,大大增加了人在現(xiàn)實(shí)人生中的選擇可能性;另一方面,總有一些人感覺(jué)心靈不知所措,不得不以個(gè)人的方式構(gòu)筑自己的避風(fēng)港。在我生活中的某些時(shí)刻,那是湖上翩翩起舞的一只白天鵝,半個(gè)世紀(jì)來(lái)不常想起但也從未忘記。
(作者系作家,現(xiàn)居美國(guó)芝加哥)

分享到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