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眼中的中國 嚴翔中/文
于是世界似乎從那些書頁中流出
像黎明時在田野上消散的霧。
只有當(dāng)兩個時代,兩種形式被
連結(jié)在一起,它們的易讀性
被擾亂,你才能看到不朽
和當(dāng)下并沒有什么不同。
——米沃什《一本廢墟里的書》
總之,兩個問題:
審查和壓抑能指。
權(quán)力的存在方式、性質(zhì)和場所。
——羅蘭·巴特《中國行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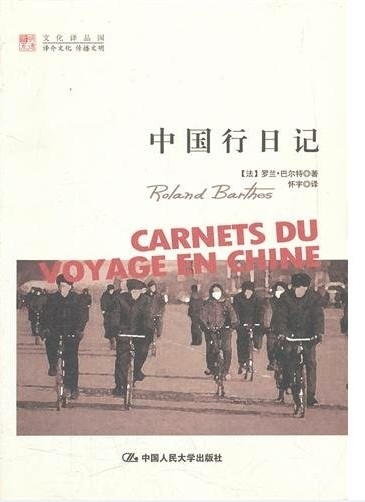
《中國行日記》
[法]羅蘭·巴爾特/著
懷宇/譯
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
2012年1月
列維·斯特勞斯說過,歷史,是片面的,即使它為自己做了辯解,也仍是片面的,它本身就是某種形式的片面性。作為80后,經(jīng)歷成長中種種價值幻滅與觀念更替,像許多朋友一樣,我努力在各種斷裂的敘述中尋找一個支點,信仰(或者幻想)這個支點可以厘清當(dāng)下的價值顛亂,實現(xiàn)某種精神上的支撐,讓我們可以更加完整而平穩(wěn)地看待自我和生活。換句話說,這其實是在玩一種拼圖游戲,游戲者從一開始就相信答案就在拼圖完成時展現(xiàn)。
隨著閱讀和經(jīng)驗的深入,我開始明白,要放棄企圖將各種碎片放進同一個圖框的做法,因為它們來自完全不同的經(jīng)驗世界:每個人談?wù)摰奈母锖透母镩_放都是具體和實在的,它們的相似性只在日期中,某個確定記載的日期就是歷史。歷史像一幅油畫失去了所有的色彩和筆觸,成為一張黑白印刷品。只有回到一個個日期,才能從旁觀者的眼中看到景觀、細節(jié)、身體、話語以及行動和它掩蓋的動機。
1974年4月11日,羅蘭·巴特來到中國,同行的還有索萊爾斯以及他大名鼎鼎的妻子茱莉亞·克里斯蒂娃等四人,時值“批林批孔”熱潮,五人在20多天中訪問了北京、上海、南京、洛陽和西安等城市,參觀了各地的重點景物、歷史古跡以及學(xué)校、醫(yī)院、人民公社、工廠。
作為法國公認的繼蒙田之后的散文大師,巴特把他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想都簡潔而鮮明地記錄下來,形成了藍色圓珠筆和碳素筆寫下的三本中國行日記,這些文字配合安東尼奧尼的影像,還原出一個70年代的中國。
動身前,巴特打算塑造一個多重意義的中國,“抽象地講,中國有著無數(shù)可能的意義:歷史概念的意義、倫理概念的意義,等等。但是,在法國人看來,中國只有一個意義。”但是下飛機后,巴特提出了一個問題:“那么,這就是中國嗎?”
我不禁回想起安東尼奧尼的《中國》:
“天安門廣場,
北京,五月的一天,
今天我們開始了短暫的中國之行,
把電影機對向這里,
中國的人民就是這部片子的明星,
我們不企望解釋中國,
我們只希望觀察這眾多的臉、動作和習(xí)慣。
從歐洲到達時,我們期待著爬山和跨越沙漠,
但很大一部分中國是可望不可及,非請莫入的。
雖然中國人打開了幾扇門戶,玩起了政治乒乓。
我們笑瞇瞇的導(dǎo)游,讓我們跟隨他們嚴格規(guī)定的路線……
同樣是規(guī)定路線的游覽,巴特一路感慨,在中國,連發(fā)型都是有規(guī)則的,“真讓人印象深刻!完全沒有時尚可言。零度的衣飾。沒有任何尋求、任何選擇。排斥愛美。”他進一步分析,服飾的完全一致所產(chǎn)生的趨變效果:“平靜、清淡、并非粗俗,以廢除色情為代價——愛美之荒蕪”。
巴特多次懷疑,中國人的性欲是如何表達的?為什么人人都像在坐禪,清心寡欲。
“這是一種沒有性器崇拜的文明嗎?出生率高嗎?”
“性欲,仍然是、永遠是一個完整的謎。”
“這種語言學(xué)并不屬于索緒爾語言學(xué)系統(tǒng)。沒有個人習(xí)慣用語。他們大概沒有談情說愛的和社會邏輯學(xué)方面的話語。”
“在這里,無任何色情。”
“我被剝奪的東西:咖啡,生菜沙拉,調(diào)情……我煩透了。”
短短幾天里,巴特經(jīng)歷了旁聽革命委員會報告,參觀商店、家庭、學(xué)校。其中斟茶次數(shù)繁多,各負責(zé)人思維呆板、尤其善于背誦數(shù)字,“統(tǒng)計”關(guān)鍵詞,“磚塊”匯總,一切都充滿了政治套話和辭不達意,在流露個人意識、情感的時候,俗套就立即跟隨出現(xiàn),“像是在掩蓋自己”。觀看表演時,法國代表團被圍在中間,不能與無關(guān)的中國人接觸。到了夜晚,巴特偏頭痛發(fā)作,無法入眠與惡心。“難受、心灰、恐慌。對于這一點,我最終認為,它象征著對白天生活的完全拒絕,象征著對俗套的厭惡……整個政治話語就像一種精神投入對象、一種壓抑對象”,讓人變得順從,個體完全被消解:
“我一點都不知道,我永遠也不會知道,我旁邊的小伙子是誰?他白天做什么?他的房間是怎樣的?他在想什么?他的性生活是怎樣的……”
在和醫(yī)生的座談中,巴特問到有沒有心理層面的疾病。
醫(yī)生回答我們是社會主義制度,引發(fā)潰瘍的心理疾病很少。通過唯物辯證法可以治愈?
那年輕人的性張力呢?
年輕人都引導(dǎo)到努力學(xué)習(xí)和工作方面去了。
婚前有無性自由呢?
性自由被認為是一種不道德行為,年輕人不接受……
“沒有任何偶遇事件、皺痕”,沒有細微差別,巴特感到乏味至極。在中國,唯一的能指等于毛澤東的書法和大字報。最后巴特下了總結(jié):
“絕對的政治集權(quán)制。就我個人來講,我無法在這種激進主義、這種狂熱的連續(xù)性、這種強迫性和偏執(zhí)狂的話語之中生活。無法在這種結(jié)構(gòu)、這種無斷痕的文本之中生活。”
巴特認為漢語是非常明確的,可以非常明確地表達人們的所思所想,但在當(dāng)時,新穎性已經(jīng)不再是一種價值,重復(fù)也不再是一種毛病。到處都是不假思索就被接受的觀念,強烈的、個人的思想只能在俗套的縫隙中才被解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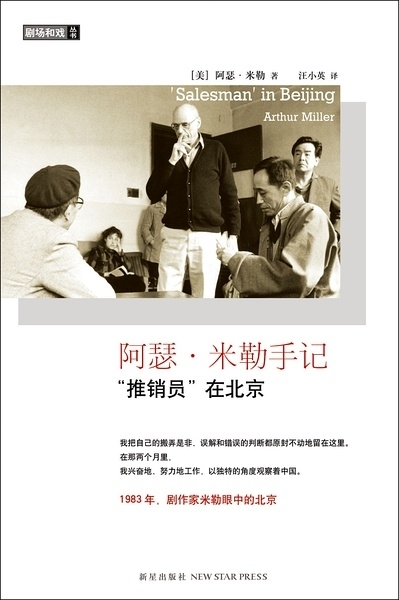
《阿瑟•米勒手記:“推銷員”在北京》
[美]阿瑟·米勒/著
汪小英/譯
新星出版社
2010年8月
巴特來到中國差不多1 0 年后,1983年3月21日,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第一次見到北京人民藝術(shù)劇院的導(dǎo)演和演員,那時他剛到中國,導(dǎo)演《推銷員之死》,演員里只有一個人懂英語,劇本的形式和它所講述的社會,對中國觀眾來說完全陌生,各種困難都讓這次合作顯得勉為其難。起初排練時,人藝的一位導(dǎo)演讀過劇本,宣稱演這樣的戲完全沒有可能。之后,好幾位演員也坦白,他們也不知道怎么辦才好。
米勒花了很大的力氣才讓大家相信:比夫堅決反對威利追求金錢,但這不是出于整齊劃一的政治覺悟或社會要求,而是出于個人的經(jīng)驗和道德,換言之,米勒是在根植當(dāng)時中國缺失的一種東西——個人意識,個人視角。一個人動輒心血來潮,不停地改換職業(yè),就當(dāng)時的中國社會來說,這簡直是天方夜譚(顯然這已經(jīng)成為當(dāng)下我們普遍的生活方式)。
米勒用愛、憐惜、幻想這些共通的情感和演員進行溝通。剛剛從文革極端平均主義中走出來的中國年輕一代已經(jīng)開始想要改善自身的物質(zhì)生活,“人們的穿著跟這個城市一樣灰暗,又讓我想起這兒有多窮。我已經(jīng)覺察到,中國急需發(fā)展經(jīng)濟,人們渴望得到很多東西——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物質(zhì)上的發(fā)達和享受知道的越多,這種渴望就越強烈。”
離開中國時,米勒感慨:
“總之,中國的難解有一次浮現(xiàn)出來。我知道中國觀眾和西方觀眾會在同一個地方發(fā)笑,我看見了他們?yōu)橥α鳒I。也許,我的問題是多余的。也許,當(dāng)中國人問這出戲發(fā)生的地點時,我應(yīng)當(dāng)仔細回答。既然他們不能化裝成外國人,當(dāng)這出戲發(fā)生在想象出來的地方——在那里的人有著中國人的面孔和黑直頭發(fā),他們的行為舉止卻如同另一個文明中的人。在這個想象的空間里,我們曾經(jīng)相遇,一起憑空造出了一座房子、一個家,一起掙扎求生。在這個想象的空間里,我們能夠分享彼此的所有。”
米勒希望文化的作用是讓人們品味文化核心的共通之處,而不是用來讓人們捍衛(wèi)自己的文化免受其他文化的影響。他看到的中國要溫和得多,街上有很多富有同情心的人們。“也許,謹慎已經(jīng)成為生存的必須,融入到了人們的血液中。但是,毫無疑問,不少人仍然遵從社會主義的道德標(biāo)準……值得注意的還有,他們自己的現(xiàn)代交響樂極有情感,很多人也喜歡聽莫扎特。總之,這里的人們似乎同時生活在幾個不同的世紀之中。”
觀看30多年的中國歷史,個人是在一點點被解放出來了。但我們依舊面對這樣一個現(xiàn)實,同一時代的中國人分成很多群體,活在幾個不同的世紀中,空洞的政治話語再也不能把這些群體簡單地團結(jié)起來。馬克思關(guān)于商品拜物教的理論認為有組織的生產(chǎn)最終會影響人們的存在和信仰,而中國恰恰已經(jīng)到了這樣一個生產(chǎn)高度組織的時代——關(guān)鍵在于你做什么,而不在于你想什么,我們需要佇立、反思和冥想。
在紀錄片《中國》的結(jié)尾,安東尼奧尼精辟地總結(jié):
“中國在開放它的大門,
但它仍然是一個遙遠的,
基本上不為人所知的國度。
我們只是看了它一眼
古老的中國有這么一句諺語:
畫虎畫皮難畫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米勒則用一種美國人特有的樂觀說道:
“古老的中國不會倒下,她會沿著曲折的歷史道路繼續(xù)前進——時而是世界的師表,時而是笨拙而固執(zhí)的學(xué)生。”
那么,這就是中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