査建英筆下的弄潮兒 by 燕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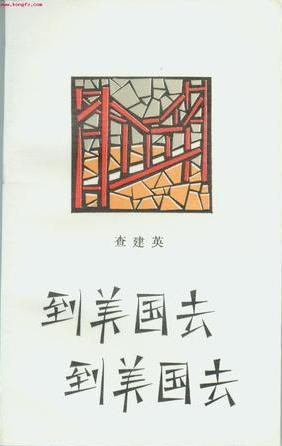
《到美國(guó)去,到美國(guó)去》
查建英/著
作家出版社
1991年
五年不見。
上一次見到作家査建英, 還是2006年。那時(shí),她帶著古根漢姆寫作基金回到中國(guó)已經(jīng)3年,每年在紐約和北京各住半年。
早在1995年,査建英“第一本比較成熟的”非小說英文著作《中國(guó)波普》(China Pop)在美國(guó)出版,她描述和分析中國(guó)市場(chǎng)化浪潮沖擊下的社會(huì)與文化轉(zhuǎn)型,以及身處其中的文化人和知識(shí)分子的種種面相。該書被美國(guó)《Village Voice Literary Supplement》雜志評(píng)為“1995年度25本最佳書籍”之一,還被不少大學(xué)作為中國(guó)文化課程教材。
1981年秋天,查建英從北大中文系畢業(yè),去了美國(guó)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xué)留學(xué);1984年又拿著南卡羅來納大學(xué)的英語碩士學(xué)位轉(zhuǎn)投哥倫比亞大學(xué),在夏志清先生門下攻讀比較文學(xué),同門的有日后成為魏晉文學(xué)專家的唐翼明(歷史作家唐浩明的兄長(zhǎng))。査建英的小說《到美國(guó)去!到美國(guó)去!》、《叢林下的冰河》開了1980年代“留學(xué)生文學(xué)”的先河,劉索拉、友友、嚴(yán)歌苓、虹影、劉西鴻等緊隨其后。
旅居紐約、芝加哥、休斯頓之后,査建英和家人于2000年前后搬到香港住了兩年。此間査建英一直用中文為香港媒體撰寫文章介紹北京,用英文向歐美介紹中國(guó)。近年的一些長(zhǎng)文陸續(xù)在《紐約時(shí)報(bào)》和《紐約客》刊發(fā),《讀書》、《萬象》也讓她實(shí)現(xiàn)了某種程度上的“文字還鄉(xiāng)”。
回到北京本來是為了新的寫作計(jì)劃,不料與1980年代文化熱中的一批“現(xiàn)象級(jí)”人物對(duì)談,談出一本《八十年代:訪談錄》。這本2006年5月在三聯(lián)書店出版并迅疾暢銷的訪談錄,正是我五年前第一次采訪査建英的緣起。
不見査建英的這幾年,不時(shí)“見”她出現(xiàn)在《鏘鏘三人行》的嘉賓席上。這是她獲得“在場(chǎng)感”、參與國(guó)內(nèi)公共討論的重要途徑。
除“寫作個(gè)體戶”之外,査建英另一個(gè)重要身份是紐約The New School中印學(xué)院的中國(guó)代表。“印度開了一個(gè)新的認(rèn)識(shí)中國(guó)的視角,就是中印比較,和中美比較很不一樣”,査建英這八年來組織了大量中印比較的學(xué)術(shù)研討,在紐約、北京和孟買做了許多實(shí)地考察。這位“地理文化決定論者”近年來格外關(guān)心的是,印度能為中國(guó)的發(fā)展提供怎樣的經(jīng)驗(yàn)和教訓(xùn)。
殊途同歸。
査建英1987年本來通過了哥倫比亞大學(xué)的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的口試,領(lǐng)了筆獎(jiǎng)學(xué)金,說是要回中國(guó)研究“美國(guó)的‘越戰(zhàn)’小說和中國(guó)的‘文革’小說”。臨別前,時(shí)任比較文學(xué)系主任的薩義德曾疑惑地問:“你是不是真的還會(huì)回到我們這兒?”果不其然,査建英最后沒有寫出博士論文——夏志清先生或許有些失望,沒有像研究自然辨證法的父親査汝強(qiáng)那樣走上治學(xué)之路,她選擇了英文為主、中文為輔的寫作——査建英自認(rèn)為不適合做一個(gè)站在講壇上的大學(xué)教師,“與其做一個(gè)特別糟糕的學(xué)者,不如做一點(diǎn)自己真正喜歡的事情”。
再次見到査建英是2011年年底,她在美國(guó)出版的新著《Tide Players》(《弄潮兒》),剛被英國(guó)《經(jīng)濟(jì)學(xué)家》評(píng)為“2011年最佳圖書”。該書集中采寫了張大中、孫立哲、潘石屹、張欣和王蒙、張維迎等企業(yè)家與知識(shí)分子,試圖立體描述當(dāng)下中國(guó)的發(fā)展?fàn)顩r。
于是,圍繞著這五年的“見與不見”,我們?cè)俅我环瑫痴劇?/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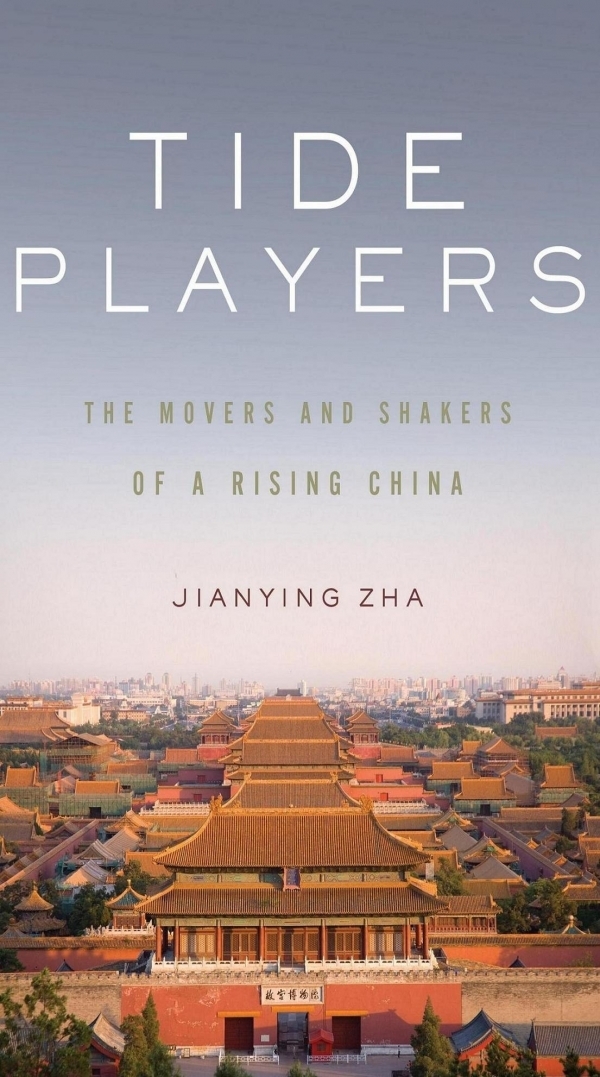
《弄潮兒》
( Tide Players : The Movers and Shakers of a Rising China)
Jianying Zha/著
The New Press
2011年3月
訪談
Q=燕舞 A=查建英
弄潮兒
Q:《八十年代:訪談錄》掀起熱潮后,您更多地回歸和介入國(guó)內(nèi)思想文化界了。這幾年在《紐約客》刊發(fā)的那些長(zhǎng)文,都被國(guó)內(nèi)網(wǎng)友第一時(shí)間主動(dòng)翻譯過來,像《紐約客》2010年11月8日封面頭條那篇寫王蒙的《國(guó)家公仆》。而2011年國(guó)內(nèi)出版的《紐約客》前任記者何偉(Peter Hessler)的《尋路中國(guó):從鄉(xiāng)村到工廠的自駕之旅》,不少媒體將其排在年度圖書評(píng)選榜首。描寫中國(guó)最深入的非虛構(gòu)作品的作者不是中國(guó)人,而是一位美國(guó)記者,這多少值得中國(guó)記者和寫作者反思吧。
A:何偉是《紐約客》前些年的駐華記者,是專職記者,我是自由撰稿,跟他們沒有長(zhǎng)期合約。現(xiàn)在歐逸文(Evan Osnos)接任,他們都得一年內(nèi)寫幾篇,我是沒有的。最早,他們跟我約稿時(shí),我寫出來他們不滿意,讓我改,我不愿意按照他們的思路改,也不愿意由他們來給我定選題,我是一個(gè)天生的個(gè)體戶,最后就變成自由撰稿了。
我2011年4月出的這本新書《Tide Players》(《弄潮兒》),還沒有中文版。昨天我在一個(gè)飯局上碰見“東西網(wǎng)”和“譯言網(wǎng)”的創(chuàng)辦人趙嘉敏,他說我這本書在大陸全部刊發(fā)不可能,但他想組織翻譯部分章節(jié)發(fā)表網(wǎng)絡(luò)版,還說國(guó)內(nèi)現(xiàn)在也有一些讀者已經(jīng)開始從網(wǎng)上的“蘋果商店”(Apple Store)買書了,買那些國(guó)內(nèi)買不到的書。
我這個(gè)集子里有三章是《紐約客》發(fā)表過的,但不是《紐約客》上發(fā)表的那個(gè)樣子。比如寫王蒙那篇,實(shí)際上《紐約客》刪掉了將近一半,所以《弄潮兒》里面就長(zhǎng)出來差不多一倍。《紐約客》只能是那么長(zhǎng),不可能再長(zhǎng)了,我這幾篇都是《紐約客》當(dāng)期封面的頭條,給的長(zhǎng)度已經(jīng)是最長(zhǎng)的了。
其他幾篇是沒發(fā)表過的,就是專為這本書寫的。《弄潮兒》是一個(gè)集子,基本上是人物系列,所以給《紐約客》的那幾篇人物我收進(jìn)去了。
Q:《弄潮兒》里主要寫了哪些人物?
A: 《弄潮兒》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企業(yè)家,即entrepreneur;第二部分是intellectual,算知識(shí)分子、知識(shí)人吧。我對(duì)知識(shí)人的定義比較寬泛,第一章是北大,我的母校。源起是一個(gè)個(gè)案,就是當(dāng)年的北大人事制度改革。我2003年從美國(guó)搬回北京來,就碰上北大改革最白熱化的時(shí)期,所以那是全書寫得最早的一章。這個(gè)爭(zhēng)論持續(xù)了一年多,之后我又追蹤,一直到前不久,這個(gè)改革有點(diǎn)無疾而終了。張維迎是這一章的主要人物,但里面是北大教授的群像:我在中文系的師兄比如陳平原、劉東,還提到甘陽、張永和這些人。王蒙那章的主要人物就是王蒙。張大中那章的二號(hào)人物是黃光裕,還有張大中的媽媽王佩英。
Q:我收到過王佩英慈善基金會(huì)贈(zèng)送的紀(jì)錄片《我的母親王佩英》和《王佩英評(píng)傳》,其中收錄的權(quán)威資料顯示, 文革受難者王佩英(1915年3月14日~1970年1月18日),終于在2011年6月9日被北京市高級(jí)人民法院終審判決無罪。
A:張大中其實(shí)很希望我寫他媽媽為主,而不是以他為主,但是出于英文讀者的考慮,我說還是得以你為主——你媽媽在里面只能是二號(hào)角色,因?yàn)樗氖虑槭且粋€(gè)歷史冤案,用中文寫意義更大,跟美國(guó)讀者講起來比較費(fèi)勁。
企業(yè)家里面還有一個(gè)人物是孫立哲(亦可參見《北京青年報(bào)》2011年10月21日?qǐng)?bào)道《孫立哲:一個(gè)赤腳醫(yī)生的傳奇》,網(wǎng)址為:http://bjyouth.ynet.com/3.1/1110/21/6371869.html——采訪人注),你們這個(gè)年紀(jì)的可能不知道,他是文革時(shí)期的風(fēng)云人物,毛澤東欽點(diǎn)的五個(gè)模范知青之一,是全國(guó)最著名的赤腳醫(yī)生。他是清華大學(xué)附中的學(xué)生,1969年初下到延安插隊(duì),之后變成一個(gè)“神醫(yī)”,特別有天賦,在當(dāng)?shù)刂斡藷o數(shù)農(nóng)民。可是“四人幫”倒臺(tái)以后就把他打下去了,他的命運(yùn)起伏極大。
后來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績(jī)考到北京第二醫(yī)學(xué)院(現(xiàn)為首都醫(yī)科大學(xué)),1982年出國(guó),以后轉(zhuǎn)行變成了一個(gè)出版家,又回來投資。中信出版社原來很糟的,他參與之后帶來很多版權(quán),出了很多暢銷書。像《誰動(dòng)了我的奶酪》、哈佛商學(xué)院的經(jīng)管系列,都是他最先帶動(dòng)起來的,可他們后來發(fā)生了一場(chǎng)糾紛,他又被踢出去了。孫立哲是一個(gè)很“神”的人,精力非凡,一邊經(jīng)商一邊滿世界飛去修各種學(xué)位,業(yè)余時(shí)間還免費(fèi)給人治病,甚至自己買進(jìn)口藥,送給貧窮的病人。很多這些老知青一代的人,一方面對(duì)知識(shí),一方面對(duì)服務(wù)社會(huì),有很深的情結(jié),單是財(cái)富不能滿足他們。
還有一篇是《紐約客》上發(fā)表過的,關(guān)于潘石屹、張欣的,就是以他們這個(gè)“土鱉”+“海龜”的組合,以地產(chǎn)這個(gè)行業(yè)為中心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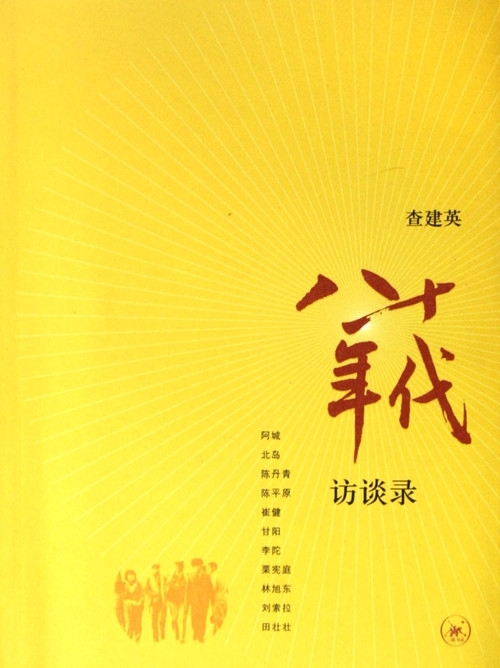
《八十年代訪談錄》
查建英/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2006年5月
企業(yè)家的human story
Q:寫王蒙那篇我讀得比較細(xì)。您和王蒙1990年代初就認(rèn)識(shí)了,私下接觸也挺多,但企業(yè)家這塊兒可能就沒那么熟,是后來再去訪談?
A:我對(duì)企業(yè)家的熟悉程度也都不一樣。寫潘石屹和張欣,開始認(rèn)識(shí)的時(shí)候并沒想寫他們,是先認(rèn)識(shí)張欣,就是幾個(gè)女朋友洪晃、張欣、劉索拉、寧瀛和我,這五個(gè)人老在一起吃飯,號(hào)稱“姑奶奶俱樂部”,一起神侃就認(rèn)識(shí)了。我那個(gè)時(shí)候都不知道張欣是干什么的,剛從國(guó)外回來嘛,第一次跟她一塊兒吃飯,她說“我是蓋房子的”。后來慢慢熟了,才知道潘石屹,才開始覺得他們挺有意思的。后來才決定寫他們,其實(shí)已經(jīng)有點(diǎn)像朋友了,那時(shí)候再訪談就不是純粹地拿著錄音機(jī),因?yàn)橐呀?jīng)有一個(gè)階段的了解。
孫立哲的第一任太太是我北大的同班同學(xué),關(guān)系特別好,但是她很早就得癌癥去世了。我那時(shí)候就在他們那個(gè)圈子里混,他們都是老知青,我是班上最小的,因?yàn)槲腋茫杂袝r(shí)候帶著我玩,一塊兒吃飯。史鐵生、孫立哲都是一個(gè)圈子的,都特別熟,很多都是清華附中的子弟或者父母都是清華的海歸教授。因?yàn)槭顷儽敝啵麄兓爻呛罄暇墼谝黄鸪猿院群龋艺J(rèn)識(shí)他們的時(shí)候才十八九歲,后來孫立哲的太太去世了我們還聯(lián)系著。
其中,最晚認(rèn)識(shí)張大中,也不是我找他要寫一篇文章,而是他找我。他的一個(gè)代理律師是北大法律系的,也是一個(gè)海歸,他送給張大中一本《八十年代:訪談錄》,張大中那時(shí)候(2007年)剛把他的公司賣給黃光裕了,沒有以前那么忙了。他看了這本書以后就有興趣認(rèn)識(shí)我,這個(gè)律師朋友就把我們湊在一起吃了一頓飯。吃飯當(dāng)中我才發(fā)現(xiàn)他有這么一個(gè)媽媽,由此對(duì)他更有興趣,因?yàn)槿绻麅H僅是一個(gè)企業(yè)家,好像也沒有那么特別。
吃完飯以后他告訴我,他最有共鳴的是《國(guó)家公敵》,《八十年代:訪談錄》他倒沒什么特別的感覺——我有那么一個(gè)哥哥,他有那么一個(gè)媽媽,他愿意跟我談。這樣才約了一起再聊天,越聊越覺得很有意思,就決定把他作為故事主人公寫篇英文的文章,最后我跟他也變成朋友了。關(guān)于她媽媽當(dāng)年受迫害致死的采訪,我推薦了郭宇寬去做,還給他們提供過見證人,恰好我的一個(gè)老朋友是他媽媽被押送刑場(chǎng)前的萬人公審大會(huì)的在場(chǎng)者。
我寫東西有一個(gè)特點(diǎn),可能他本來不是朋友,寫完往往就變成朋友了,因?yàn)槲也皇且淮涡圆稍L,會(huì)觀察得比較長(zhǎng);或者是他本來就是我的朋友,我覺得他值得寫,他也同意,我就寫了。你看《八十年代:訪談錄》里面,大部分人我都認(rèn)識(shí)很多年了,這種訪談就像朋友談話一樣。
Q:但這可能會(huì)有一定的同質(zhì)性,選題可能局限在一個(gè)相對(duì)比較小的范圍?
A:對(duì),這個(gè)限制在于,我的寫作前提是只寫我熟悉的,我熟悉的當(dāng)然就跟我平常的生活圈子、感興趣的范圍有關(guān)系。比如說,企業(yè)家其實(shí)是我相對(duì)不熟悉的,在我來說還是出了一下這個(gè)圈子。但是,我選的這些企業(yè)家,其實(shí)也是要有一段時(shí)間去了解,我不太愿意寫一個(gè)沒有深入了解的人。而且,就是寫企業(yè)家,我一般寫的是human story,是從人性的角度,以他們的成長(zhǎng)和心路歷程折射出一個(gè)時(shí)代或者一個(gè)歷史的瞬間,而不是只寫他們?cè)趺促嶅X、怎么成功,那種勵(lì)志故事更有商業(yè)性、更流行,但那既非我的強(qiáng)項(xiàng)也非我的興趣所在。
忠實(shí)于真相
Q:《國(guó)家公仆》追問得特別好,“中國(guó)最著名的作家是一位改革者還是一位辯護(hù)士”,王蒙看到后是一個(gè)什么樣的反應(yīng)?
A:發(fā)表之前他沒有看過。這是美國(guó)的行規(guī):發(fā)表之前你不能先給你寫到的人看稿,否則會(huì)被認(rèn)為你可能受到寫作對(duì)象的影響、下筆不客觀中立。發(fā)表之后,《紐約客》上的英文版和后來的中譯版王蒙都看過,未予置評(píng)。但我們的友好關(guān)系沒有受到影響。他是一個(gè)非常謹(jǐn)慎的人,這個(gè)態(tài)度我非常理解。我甚至覺得有點(diǎn)慶幸,因?yàn)楹芏嗳藖韱栁宜裁捶磻?yīng),他真的是一句沒說,我們照常來往,還一起上《鏘鏘三人行》;平常我們也有聯(lián)絡(luò),發(fā)發(fā)電子郵件什么的,一切正常。
我覺得他不作評(píng)論挺好。有些時(shí)候,不說話最好。他知道這是我的文章,我會(huì)文責(zé)自負(fù)。無論他怎么反應(yīng),這個(gè)文章已經(jīng)出來了。
Q:您寫的時(shí)候會(huì)不會(huì)有什么顧慮?
A:我其實(shí)是很擔(dān)心的,因?yàn)橐呀?jīng)認(rèn)識(shí)快二十年了,但也不能說是那么近的朋友,應(yīng)該說是我很尊重和喜歡的一個(gè)忘年交。畢竟,他有官場(chǎng)的經(jīng)歷、 “放逐”新疆16年的右派經(jīng)歷。我當(dāng)然非常擔(dān)心這個(gè)文章出來以后會(huì)對(duì)他有傷害,如果他從個(gè)人感情上接受不了,或者是這個(gè)文章引起的議論影響到他某些方面,我都會(huì)很過意不去。但是,作為作家的第一考慮,就是我要忠實(shí)于真相、忠實(shí)于事實(shí),我希望能盡可能的客觀。
他又是這么復(fù)雜、這么豐富的一個(gè)人物。為這么一篇文章我看了很多資料。他是一個(gè)高產(chǎn)作家,好多東西我都要看,他那三大本回憶錄我看了兩遍;然后跟他談,跟他周圍討厭他的和喜歡他的、佩服他的和感覺非常復(fù)雜的人都談過。最后寫出來的其實(shí)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我覺得還算實(shí)事求是吧。
但是文章出來以后,反應(yīng)是截然不同的,喜歡王蒙的人覺得我下手太狠了,認(rèn)識(shí)他這么多年,怎么能這么狠呢?不喜歡他的人,很多右派的朋友覺得我太同情他了,把他寫成了忍辱負(fù)重的那種感覺,認(rèn)為最后給他的評(píng)價(jià)其實(shí)相當(dāng)高,太體諒他了,沒有把他的所謂“嘴臉”寫出來,還不夠負(fù)面。
這是兩極的反應(yīng),但還是有很多作家朋友、美國(guó)的讀者,覺得把中國(guó)的復(fù)雜性寫出來了。
Q:文中也提到,在一些重大事件發(fā)生后或關(guān)鍵性的歷史時(shí)刻,您都會(huì)寫郵件詢問他的相關(guān)態(tài)度。比如,他在2009年法蘭克福國(guó)際書展上演講,稱“中國(guó)文學(xué)處在它最好的時(shí)候”、“中國(guó)可算是全世界的文學(xué)大國(guó)”,這引發(fā)國(guó)內(nèi)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一片嘲諷,您事后立即發(fā)郵件表達(dá)對(duì)這場(chǎng)爭(zhēng)論的失望,他簡(jiǎn)潔地回復(fù)道:“沒事。隨便。我顧不上這些事,也早習(xí)慣了。謝謝。”可在另一些更重要的歷史時(shí)刻,您去信詢問他的態(tài)度,他就“沒有任何回復(fù)”了。
A:這些都是事實(shí)。他為什么不回我,也可以理解。他回什么、不回什么,就很說明他和他所處的語境了,我放在那兒就行了,用不著再過多地評(píng)價(jià)了,事實(shí)本身是最意味深長(zhǎng)的。你看了以后,對(duì)這個(gè)人物的印象是更偏負(fù)面了嗎?
Q:沒有。我其實(shí)很少看虛構(gòu)類作品,以前對(duì)王蒙的文本的印象不是特別好,因?yàn)樗貏e喜歡用排比句,這在我看來就是特別煽情,有時(shí)甚至是一種語言暴力。他的回憶錄中與訪美有關(guān)的章節(jié)我倒是研究過,當(dāng)然因?yàn)橹庇X或某種偏見,我覺得他比較圓滑或者說有“生存智慧”。
A:太多的人這樣說他了,其中很多人自己也未見得有多么勇猛的表現(xiàn)。我持保留意見吧。
對(duì)他我已經(jīng)非常感謝了,我寫這么長(zhǎng)一篇文章,在這么長(zhǎng)的過程中沒有給他看過一個(gè)字。《紐約客》有非常嚴(yán)格和繁瑣的查證程序,他們直接給他打電話了,但是也不會(huì)告訴他這個(gè)文章是怎么寫的,不可能給他念的,只會(huì)說這里面直接引用到他的話,問他說沒說過這句話,這個(gè)話準(zhǔn)確不準(zhǔn)確。
他能夠給我這么大的信任,已經(jīng)非常不簡(jiǎn)單了。而且,文章出來以后,他并沒有說什么,頂多說過感謝我花了這么多心血,這還是在看文章之前。
Q:寫作期間,您要跟他談什么,都會(huì)提前告訴他嗎?
A:有過一次錄音訪談。他知道我在寫,但是怎么寫、寫成什么樣,他完全不知道。
其實(shí)這些年我在挑選中國(guó)人物的過程中,遇到過很多精彩的、可以寫得很有意思的故事,有些我已經(jīng)花了大量工夫準(zhǔn)備甚至寫了初稿,最后我都放棄了,因?yàn)榭紤]到這個(gè)被寫的人可能承受不了我這種比較“狠”的寫法。所謂的客觀筆法其實(shí)相當(dāng)重的,臉皮薄一點(diǎn)的人都受不了。
寫王蒙的文章出來以后,(華東師范大學(xué)歷史系教授)許紀(jì)霖給我來了一封E-mail,他剛看了翻成中文的版本,說你居然寫完這個(gè)還可以跟王蒙吃飯,簡(jiǎn)直不能想象。他就是研究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思想史的,他說這些年(寫到當(dāng)代知識(shí)分子的個(gè)案時(shí))是寫一個(gè)就得罪一個(gè)就斷交一個(gè),所以不能想象我和王蒙還能吃飯。
我說,這正說明王蒙的大度,而且我的預(yù)計(jì)基本上是對(duì)的。如果我覺得他完全承受不了,這篇我就不寫了。我想了半天,覺得他可以承受,他經(jīng)歷了那么多,那么穩(wěn)妥和看透,會(huì)看得出我沒有惡意,這么一篇文章也不會(huì)給他政治上帶來什么打擊。頂多他是一個(gè)有爭(zhēng)議的人物,他多少年來就是嘛,所以我覺得他可以承受得住,我從不認(rèn)為他是一個(gè)小肚雞腸的人。
有很多人覺得他就是太在意自己的形象和地位所帶來的特權(quán),斤斤計(jì)較;另一些人把他捧上天,一天到晚叫他大師,讓人起雞皮疙瘩。這兩種我都不是,是很認(rèn)真地對(duì)待他的,我覺得他可以感覺到這點(diǎn),也能接受我對(duì)他的一些批評(píng)。
Q:《弄潮兒》里寫到潘石屹和張欣的部分,他們也該讀到了?
A:發(fā)表以后,他們才讀到,之前沒讀到。《紐約客》給張欣打過電話,沒給潘石屹打電話,因?yàn)樗欢⑽模菚r(shí)候《紐約客》還沒有中文核查的專職人員。到了王蒙那篇,他們有了,就派了一個(gè)小時(shí)候移民去美國(guó)但中文很流利的人來查證。
《紐約客》向張欣查證過,還向相關(guān)的人查證過,但他們都是發(fā)表出來后才看到的。我說的客觀也只能說是盡可能的客觀,有些東西我在選材的時(shí)候也是要回避的,比如隱私;比如涉及腐敗——你寫了就可能把這個(gè)人抓起來了,那是不是要做這樣的事情,你得做一個(gè)考慮:他的腐敗是不是到了某種程度,還是只是大環(huán)境的一個(gè)反映?如果只是一個(gè)反映,你必須要寫到。
地產(chǎn)業(yè)有多少暗箱啊,我其實(shí)寫了潘石屹、馮侖他們?nèi)f通的第一桶金在海南是怎么淘的,當(dāng)時(shí)整個(gè)環(huán)境都很瘋狂,有點(diǎn)像開發(fā)西部時(shí)候的土匪。到后來拿地、拍地什么的,這在中國(guó)有很多暗箱、潛規(guī)則、權(quán)錢交易,要搞政府關(guān)系。但是我不會(huì)直接寫到他們哪一次如何操作這么具體,我只是寫了地產(chǎn)界的一般狀況。我說的客觀,也是有邊界與分寸的,是有很多技術(shù)問題需要把握的。我不能因?yàn)榘l(fā)表一篇文章而去傷害一個(gè)人。
Q:以前采訪您,好像您說上網(wǎng)的時(shí)間不是特別多,那像微博這幾年在中國(guó)大陸發(fā)展得這么迅猛,您上嗎?
A:我Blog、微博都沒開。前幾年新浪曾邀請(qǐng)過我,我沒接受,這里面有很多原因。我那個(gè)時(shí)代的人對(duì)沒有隱私這件事有一種很深的反感,什么《雷鋒日記》之類的,就是為了給別人看。“隱私”這個(gè)詞,以前漢語里聽不到的,現(xiàn)在開始撿起來,我就非常在意,你私人寫日記就不要放到網(wǎng)上去了。Blog已經(jīng)有點(diǎn)兒這種嫌疑,現(xiàn)在發(fā)展到更瑣碎的微博。老在那兒發(fā)布給別人看,你這一天在干什么、想什么。如果真的發(fā)表文章,應(yīng)該是最公眾的,不是私人日記、隨想什么的。可能這是我個(gè)人的一個(gè)心理障礙,我不習(xí)慣這樣,這個(gè)公與私的界限太模糊了。
在這個(gè)高科技、大批量快速生產(chǎn)的時(shí)代,我是一個(gè)保守主義者。80年代剛?cè)ッ绹?guó)上學(xué)我就開始用電腦,這都多少年了,我還是把電腦主要當(dāng)作文字處理機(jī),除了寫、編文章,僅限于收發(fā)E-mail,近年才開始用網(wǎng)絡(luò)做研究工具,查查資料什么的。
我本人對(duì)文字還是很挑剔的,對(duì)隨手就寫然后公布出去,是不太習(xí)慣的。我是一個(gè)低產(chǎn)作家,有些人很高產(chǎn),我很佩服,但也發(fā)現(xiàn)好多人高產(chǎn)高得不太講究。芝麻西瓜,什么都抓一把;一瀉千里,泥沙俱下。文字應(yīng)該是一個(gè)講究的東西,應(yīng)該沉靜下來用心對(duì)待、舍得花時(shí)間打磨,應(yīng)該沉淀、少而精。至少這是我自己更愿意選取的寫作態(tài)度。也許文字才是我的真愛吧。如果你真愛一個(gè)人,你自然會(huì)珍惜、檢點(diǎn)、細(xì)致地對(duì)待他,如果隨隨便便,不講究時(shí)間地點(diǎn)、也無所謂裝束舉止,天天破門而出招搖過市,那不是一個(gè)糙人或者一個(gè)輕狂濫情的薄幸之徒嗎?
所以我這樣的人不適合開微博、開Blog。但是,我不否定開微博,因?yàn)樗墒歉鞣N人組成、各種因素造成的。尤其是中國(guó)大陸網(wǎng)絡(luò)之外的言論、媒體空間很有限,有些公眾事件的報(bào)道和討論,只有網(wǎng)絡(luò)和微博能做。在美國(guó)做,就沒多大意義,美國(guó)主要是用它來社交,大家約會(huì)啊、八卦啊,中國(guó)當(dāng)然也有一大批這樣的,但微博在中國(guó)大陸確實(shí)是一個(gè)透明度、自由度都很高的民間監(jiān)督平臺(tái),在這個(gè)意義上我很尊重它。
Q:尤其像解救被拐兒童或其他公共事件的討論,它即使在微博上被刪掉,但只要這個(gè)事情發(fā)生了,相關(guān)微博內(nèi)容在一個(gè)很短的時(shí)間內(nèi)就傳播出去了。
A:而且會(huì)被成幾何級(jí)地?zé)o限轉(zhuǎn)發(fā)。我也有不少“公知”朋友開微博,他們的言論要不受限制地直接發(fā)布出來,只有通過這種形式。報(bào)紙上開專欄受很多限制,在電視上說也受限制,所以我非常理解他們?yōu)槭裁催@樣做。只不過我個(gè)人的成長(zhǎng)背景和性格使我不太適合選取這種方式去參與,所以選取了寫作,這種方式是我能控制的。
寫作完全是個(gè)體的事,我很少與人合寫。像《八十年代:訪談錄》我要跟每一個(gè)受訪人合作,這在我是一次例外。我還參與過我工作的研究所編輯的論文集。其他時(shí)候我都是單干戶,英文書也都是我自己寫,文章也沒有合寫的。
Q:我也上微博,但有時(shí)又發(fā)現(xiàn),國(guó)人在很多場(chǎng)合談?wù)摰脑掝}都來自微博,就覺得我們的話語資源太過貧乏,似乎不談?wù)撐⒉┥系脑掝}就無話可說了。
A:對(duì),但即使不開微博,也能聽到無數(shù)的信息,所以我不缺這個(gè)。其實(shí),我潛水去微博上看過,我注冊(cè)了一個(gè)賬號(hào),看了一段連自己的賬號(hào)都忘了。他們都說會(huì)上癮,我根本不上癮,看了看就煩了。我不看微博,信息也都到我這兒了。那些最敏感、最熱點(diǎn)的事件,從別的渠道,從電子郵箱,很多人就轉(zhuǎn)發(fā)給我了,或者在飯桌上就可以聽到。
Q:前面的談話中,您特別多地講到“吃飯”,飯局是不是也是您回北京這幾年了解中國(guó)的一個(gè)很重要的渠道?
A:當(dāng)然了。我本來就是一個(gè)好吃之徒,所以好飯局、好飯館我是不太容易拒絕的,在飯桌上就能聽到各種各樣的消息,包括這些人對(duì)這些消息的態(tài)度。
信息源是多方面的,關(guān)一個(gè),其他信息也足夠了。現(xiàn)在我覺得還得關(guān),你看我這里好多雜志寄過來,看都看不過來。好多信息是重復(fù)性的、不必要的。你的腦子像一個(gè)裝滿太多雜物的閣樓,塞滿了,反而你該看的書、該想的事、該認(rèn)真對(duì)待的人,你沒有時(shí)間也裝不進(jìn)去了。你成了信息的奴隸,對(duì)生活中一些真正重要的東西你反而麻木了,整天跟著時(shí)事跑、圍著八卦轉(zhuǎn)。所以,微博對(duì)我來說是不必要的。
Q:梁文道有個(gè)說法,他不愿意跟人在外面吃飯,因?yàn)樵谧蛔蟻砭投嫉皖^拿著手機(jī)發(fā)微博。
A:這太恐怖了,我最害怕這種人了,如果我的同齡人里有這么一個(gè)人,那更恐怖了。年輕人這么做還可以理解,他們就生在這么一個(gè)時(shí)代,年輕人也容易不自信、愛跟風(fēng),需要群體承認(rèn)、確認(rèn)他。可是到了這種“微博控”的程度,坦率說我覺得這是一種病,就像“照鏡狂”。如果一個(gè)中年人,一天到晚生怕一群陌生人不關(guān)注你、生怕“掉粉”,完全被你的所謂粉絲團(tuán)控制住了,你還有什么自我,這也太可憐了。
而且這種行為實(shí)在太不講究、太糙了,貌似他是高科技能手,他很in,但其實(shí)連基本的教養(yǎng)都沒有,惡俗無比。這種人出現(xiàn)在飯局上何止是敗興,應(yīng)該請(qǐng)他走路,out!因?yàn)樗唤?jīng)別人同意就把私人場(chǎng)所的門打開,搬到網(wǎng)絡(luò)上的公眾場(chǎng)所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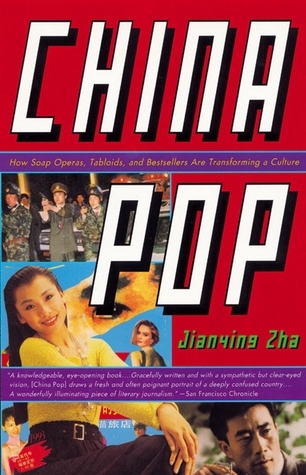
《中國(guó)波普》(China Pop)
Jianying Zha /著
The New Press
1996月4年
印度是中國(guó)的鏡子
Q:我最關(guān)心的還是您作為紐約The New School中印學(xué)院的中國(guó)代表這幾年所做的工作,因?yàn)橹杏”容^研究是國(guó)內(nèi)近年來的一大熱點(diǎn)。
A:The New School剛創(chuàng)辦印度中國(guó)研究所的時(shí)候,我就受聘參加了。2004年開始討論,2005年初正式成立。開始我對(duì)印度完全不了解,那時(shí)候印度也不太熱。2004年,美國(guó)一個(gè)大基金會(huì)投了一大筆資金,放到這個(gè)大學(xué)里面,他們要找一個(gè)駐中國(guó)的、一個(gè)駐印度的代表一起來做項(xiàng)目策劃和管理。此前一年,2003年我拿到了古根漢姆的寫作基金,搬回來寫關(guān)于中國(guó)的一本書,同時(shí)帶著我女兒在北京上小學(xué)。好不容易回來了,我也不想回美國(guó)去。所以覺得這個(gè)工作特別適合我,他們需要這個(gè)人住在中國(guó);另外那個(gè)印度代表駐孟買,但是都要兩邊跑,因?yàn)榭偛吭诩~約。我正好借此也可以常去紐約,就答應(yīng)了。
那時(shí)我對(duì)印度一無所知,極不了解。好在我們只是出資花錢的單位,在紐約籌辦項(xiàng)目,在中國(guó)、印度、美國(guó)三地分別、分批選拔相應(yīng)的學(xué)者來合作做研究課題,我負(fù)責(zé)中國(guó)這部分。開始真是兩眼一抹黑,我的一些朋友也很納悶,說你怎么搞到印度去了,印度有什么好研究的?
從那時(shí)候到現(xiàn)在,這七八年變化非常大:印度經(jīng)濟(jì)的高速發(fā)展、中印比較、中印美三國(guó)之間這種微妙的地緣政治關(guān)系,都變成了熱門話題。我們的課題也經(jīng)歷了好幾個(gè)階段、好幾期不同的成員,課題組有些人也變成了朋友,比如第一期里面的北大中國(guó)經(jīng)濟(jì)研究中心的教授姚洋,(記者)郭宇寬,我們一起去印度考察,也成了朋友。后來的中國(guó)成員包括許志永、盧思騁、李波等。印度打開了一扇新的窗口,在這個(gè)過程中,我學(xué)到了很多東西,由此不僅對(duì)印度增加了一些了解,而且印度提供了一個(gè)新的認(rèn)識(shí)中國(guó)的視角。中印比較和中美比較很不一樣。
Q:具體怎么不一樣?
A:印度與中國(guó)同為古老的亞洲文明,互為鄰居,可是我們彼此的研究興趣相當(dāng)弱、相當(dāng)差。對(duì)很多中國(guó)人來講,印度是在我們意識(shí)之外的,至少是在邊緣上,有很多出于無知的偏見,我們老是盯著西方,主要盯著美國(guó)、歐美,對(duì)吧?
我們對(duì)印度其實(shí)是很漠視的,他們對(duì)中國(guó)也有一種微妙的心理。本來他們?cè)跉v史上覺得自己是中國(guó)的老師,因?yàn)榉鸾叹褪菑乃麄兡莾簜鱽淼穆铮谖拿鹘涣髦校袊?guó)受惠于印度很多。然而1962年發(fā)生了中印邊境戰(zhàn)爭(zhēng),印度是戰(zhàn)敗者,他們認(rèn)為中國(guó)背叛了友誼,尼赫魯為此郁郁而死,所以他們對(duì)中國(guó)有一種傷痛的情結(jié),不信任、有敵意。
在經(jīng)濟(jì)發(fā)展方面,他們市場(chǎng)改革起步晚一些,至今走在中國(guó)后面,與我們又有一種競(jìng)爭(zhēng)心理。但他們是亞洲最大的民主國(guó)家,所以在政治制度上有一種優(yōu)越感。不只政治制度,在價(jià)值觀、精神文明、意識(shí)形態(tài)上,他們好像都有一種優(yōu)越感。你別看它有那么長(zhǎng)的被殖民史,很多印度人在文化上相當(dāng)自我,認(rèn)為印度文明在世界上最優(yōu)秀。
去實(shí)地考察以后,我發(fā)現(xiàn)問題遠(yuǎn)沒有這么簡(jiǎn)單。比如在這么一塊與我們同樣古老的亞洲文明土地上實(shí)行民主,實(shí)際運(yùn)行的經(jīng)驗(yàn)其實(shí)非常復(fù)雜,成敗得失,一言難盡。它為什么跟歐美式民主不一樣,英國(guó)人帶去的民主、法治是怎樣演變成了另一種樣態(tài)的民主、法治?這當(dāng)然與它的歷史文化有關(guān)系。而印度可以作為中國(guó)追求民主的一面鏡子。畢竟我們跟美國(guó)太不一樣了。
我本來就是一個(gè)地理文化決定論者,對(duì)地理文化是特別在意的,很多東西你得推到歷史的源頭上去看,不能光看現(xiàn)在是怎么回事——它為什么是這樣的,為什么中國(guó)文明的主流是儒家傳統(tǒng),而不是基督教、伊斯蘭教也不是佛教呢?為什么我們歷史上多數(shù)時(shí)期一直是王朝、帝國(guó),而不是一個(gè)真正意義上的封建制呢?有很多東西,都跟現(xiàn)在的問題直接相通、一脈相承,不看歷史就看不清今天。去看這么一個(gè)歷史悠久的鄰居,當(dāng)然有助于認(rèn)識(shí)我們自己。
比如對(duì)中國(guó)革命的認(rèn)識(shí),很多印度的左翼知識(shí)分子們對(duì)毛澤東是非常崇拜的,對(duì)中國(guó)革命持有非常浪漫化的觀點(diǎn),我認(rèn)識(shí)的好多印度左派學(xué)者都如此。那是因?yàn)樗麄冇凶约旱慕?jīng)驗(yàn)、自己的問題意識(shí),比如種性問題、不平等的問題。人們往往出于自己的問題,去從別人那兒取經(jīng)或者抓別人的東西來,就像我們愛把西方的某些東西拿來批判我們自己一樣,在這個(gè)過程中我們可能把西方浪漫化了。總之轉(zhuǎn)了一圈,印度是一個(gè)很有意思的參照體,一個(gè)學(xué)習(xí)、借鑒和理解我們自己的鏡子。這個(gè)工作讓我獲益匪淺。

查建英
作家,北京人,1978年-1987年先后就讀于北京大學(xué),美國(guó)南卡羅來納大學(xué)、哥倫比亞大學(xué),1987年回國(guó),90年代返回美國(guó)。著有:《八十年代訪談錄》、《Tide Players》、《China Pop》、《到美國(guó)去,到美國(guó)去》、《叢林下的冰河》等,2003獲美國(guó)古根海姆寫作基金。《China Pop》被美國(guó) Village Voice Literary Supplement 雜志評(píng)選為“1995年度25本最佳書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