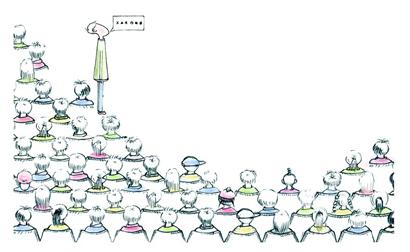
經(jīng)濟觀察報 施健子/文 拖著大隊人馬訪華的英國首相卡梅倫應該想不到,在離開北京差不多半個月后,他的兩日行程中最被關(guān)注的并不是兩國經(jīng)濟上的實質(zhì)性合作,而是他在北大的演講。11日演講結(jié)束后,一條微博在網(wǎng)上傳播:在提問環(huán)節(jié),北大學生的第一個問題是:“作為英國的領(lǐng)導人,您能從中國模式中學到什么?”卡梅倫略微思考了一會兒:“首先是奧運會的成功舉辦。”北大學子反響強烈,熱烈的掌聲一度打斷了他的發(fā)言。發(fā)帖者的點評是,這個問題就好像是在問,你從我家剛脫貧新蓋的金碧輝煌中能學到點什么?
另一個極端例子的發(fā)生地點同樣是在北大。13年前時任美國總統(tǒng)的克林頓到訪演講,互動環(huán)節(jié)充滿了火藥味。北大中文系學生馬楠在一個問題結(jié)束后站起來駁斥克林頓,“所謂真正的自由,應該是人民有權(quán)自行選擇他們想要的生活和發(fā)展方式。”現(xiàn)場情形被作家余杰記錄在案,他寫了一篇名為《“勇敢者”的游戲》的文章,在他看來,馬楠說的無非是“中國政治書本上的教條”而己。
但余杰的話并沒有贏得當時人們的廣泛認同,與現(xiàn)在更為多元化的意見形態(tài)相比,當時馬楠的發(fā)言幾乎贏得一邊倒的贊同,這個小女生甚至被樹為反對強權(quán)意識形態(tài)的先鋒。不過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在與克林頓“交鋒”兩年之后,馬楠選擇去到“人權(quán)狀況極其惡劣”的美國留學,后來定居并嫁給了一個美國人。
而在15年前,劉瑜還是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名本科生,后來她到了哈佛上學、劍橋任教又回到清華教書,這位寫出了暢銷民主啟蒙書《民主的細節(jié)》的政治學女博士并不否認,如果當年美國總統(tǒng)來到人大,她也會提出類似的問題,因為《中國可以說不》在當年的大學生里幾乎人手一本,她深受影響。
如果把時間再往前推一些,在1984年,新東方還沒有成立的時候,徐小平在北大團委工作,年輕人里最流行的是柏楊的書 《丑陋的中國人》。徐小平始終認為,在改革開放初始階段,我們卻擁有比現(xiàn)在更為開闊的思維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民族自信反而比現(xiàn)在要強很多。
問題的背后永遠比問題本身更值得探究。在將近30年的時間里,那些被稱為精英并一度是意見領(lǐng)袖的象牙塔里的年輕人們,他們倡導什么反對什么,到底背棄了什么又延續(xù)著什么?
發(fā)問的能力
在一個網(wǎng)站做出的統(tǒng)計中,歷次元首演講提問環(huán)節(jié),出現(xiàn)頻次最高的問題首先是兩國文化交流,其次是人權(quán)與民主,再次是臺灣問題,最后是國際關(guān)系。政治問題在元首的大學演講中無法回避,但中國這樣的提問模式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沿襲至今,經(jīng)過多層過濾之后保持了非常和諧的結(jié)構(gòu)。被點到有幸提問的學生在站起來的一瞬間立刻化身政府的新聞發(fā)言人,問題隔靴撓癢,態(tài)度則分化為兩重:或是極度自大,或是誠惶誠恐。
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09年訪華,與上海復旦大學的同學交流,在場一名同濟大學的學生提問:“請問在您的這屆政府中會采取哪些措施來共同構(gòu)建這個世界向著文化多元化發(fā)展?”類似這類大而空的問題在大學生的提問中并不少見。
這應該會讓他們好受很多,來訪的國家元首們在自己國家里,每天受到反對黨、媒體和社會團體的各種質(zhì)疑詰問,油煎煮炸,對于敏感問題并不存在擔心,但在中國碰到的這種與 “如何實現(xiàn)世界和平”等量的問題卻著實難倒了他們。
實際上,在常識和基本訊息的掌握上,我們名校的學生并不輸于人,只是少了儲備與輸出之間應有的關(guān)節(jié)。在我們的國家里,政治如同空氣一般深入生活,但大多在此浸潤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并不能真正了解那些每天掛在嘴邊的詞語的真正意義。
內(nèi)容或許可以理解為局限于認知,但方式的差異可以歸結(jié)到社會層面上。徐小平一針見血,“中國學生的提問看似很美好,卻觸及不到問題的本質(zhì)。他們?nèi)鄙僮罨镜拿裰鹘逃矝]有自由表達的訓練。”
劉瑜的解釋是,“學會恰當?shù)奶釂枺覀儽仨殦碛幸粋€長期而健康的公共領(lǐng)域和公共討論傳統(tǒng)。現(xiàn)在我們大到社會,小到班級,都少了以正常程序?qū)矄栴}的討論,因此我們自然也不具備這樣的發(fā)問能力。”她說,“恰當?shù)靥釂柺且环N能力。”
她舉了一個例子,英國議會預算審核,每年春秋各一次,到這個時候,上到電視報紙,下到學校課堂和家庭,都會有關(guān)于該問題的討論。“我們不能苛求我們的學生,我們從來就沒有這種氛圍,突然到了一個元首來訪的場合,我們也就沒有了應對能力。”
除了能力之外,或許還應該思考的是,我們在對這些元首提出的問題中,有哪個是我們真正想了解的?在美國,一位叫韋弗的小學生向奧巴馬提問,“你能幫忙改善校園午餐嗎?”緊接著,他又問道,“總統(tǒng)先生,你會灌籃嗎?”天然好奇心的缺失使我們的問題失去靈魂。在像一個政客、外交家和記者一樣提出問題之后,我們似乎找不到自己的真實身份和需求。
誰制造了這樣的學生?
提問的學生代表所呈現(xiàn)的狀態(tài)能在多大的程度上代表這個“被代表”的群體?外國元首司空見慣的程序是,那些坐在臺下的年輕人,在提前幾個月的時間里知道了演講的資訊并向?qū)W校提出申請,并由學校抽簽決定。但在中國,這意味著一種政治儀式,在幾次對提問學生的網(wǎng)絡(luò)“人肉”中,不難發(fā)現(xiàn)一個共同點是,這些學生都經(jīng)過了成份、成績等多方嚴格篩選,為了保證達到穩(wěn)定的效果,聽眾群里還會穿插一些還保留學生稚氣的年輕教師。
這成為很多人的一個論據(jù),他們一邊抒發(fā)自己對“代表”表現(xiàn)的不滿,另一方面,在許多不需要負責任的場合,比如網(wǎng)絡(luò)上,他們會用“如果是我,我就會如何如何”的句式表達自己的立場。但學生代表與他們身后的群體會有如此大的區(qū)別嗎?劉瑜的答案是否定的,雖然有產(chǎn)生不同聲音的可能性,但中國學生身體內(nèi)部普遍存在一個“對外”模式,“據(jù)我對中國學生的了解,在這種場合,張口就是官腔的并不在少數(shù)。”
徐小平認為這是中國教育體制失敗的一個例證,作為從業(yè)者,他甚至使用了“內(nèi)疚”二字。長期以來以一元化的教育模式帶來的制式反應已經(jīng)內(nèi)化到我們的思維當中,“在上課的時候,老師提供一個標準答案,我們要按這個答案來回答就能拿到滿分,這也養(yǎng)成了我們單一性的思考。說起西方,要不就是霸權(quán)主義,要不就是萬惡的資本主義,孩子的腦子里裝滿了成見和偏見,因此他們在提問時,往往帶有一個非常具有傾向性的預設(shè)立場,對于不了解的事情同樣如此,我們沒有足夠的好奇去了解別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
劉瑜曾經(jīng)在劍橋大學教授中國政治史,她在批作業(yè)的時候有個很深的體會,國外的大學有一個評分標準,比如說一篇 “論民主能不能促進經(jīng)濟發(fā)展”的論文,如果論文立場是肯定的,那作者也必須要提到可能性的駁論。
在幾年前,錢學森先生在“中國大學為什么培養(yǎng)不出杰出人才”的討論中也有過類似看法,他認為我們的學生缺乏獨立思考能力的同時習慣了被教育,而他的結(jié)論與我們的議題殊途同歸。
自大還是自卑
大學生們所表現(xiàn)出來的交流水平與所提問題是否提前被審核之間的對應關(guān)系并不是論證的重點。我們應該看到這樣的一個事實,如果沒有限制,我們的提問如此,是一所學校學生層次上的悲劇;反之,如果我們存在相應的選拔和限制機制,學生如此提問,完全是引導者以及國家心態(tài)存在問題變相解讀。
看看這些問題,“此時你站在講臺上,帶著偽善的微笑,這微笑背后是否還藏著真正的、壓制的初衷呢?”“您想從中國帶走什么?”無論是柏楊還是《中國可以說不》的四位作者,都很難用之前的絕對基調(diào)來定義今天中國人面臨的處境和心態(tài)。
徐小平所說的“犬儒主義”可以概括一部分,“我們失去了一種從容豁達的態(tài)度,具體到這個問題上,提問不是辯論,大學生不可以把魯莽當智慧,把大膽當勇氣。”這種心態(tài)下滋生的傲慢正一點點擴散,他說,“這是一種無知,我們的人均GDP,我們的環(huán)境問題,我們的廉潔指數(shù)都非常惡劣,為什么大家就未富先驕,未強先傲呢?”
劉瑜從她的專業(yè)角度出發(fā),“這或許與中國之前經(jīng)歷的長達150年的屈辱史有關(guān)系,我們就像處在青春期的少年,急于想證明自己,或者說得到別人的認可,這其實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是不太自信的表現(xiàn)。年輕的時候,不夠強大,總喜歡把自信建立在對別人的否定之上,成長之后,自信建立在自己做過了什么之上。”
徐小平在帶學生到美國大使館去簽證的時候,經(jīng)常教育學生要自信面對簽證官,但學生們的反應都是擔心會因此冒犯到簽證官。而奧巴馬到復旦大學演講的時候,一位學生小心翼翼的提了個問題,“您得了諾貝爾獎對您來說是不是意味著更多的壓力和責任?這會不會影響你解決世界問題的一些態(tài)度?”堪稱史上最安全提問。禮貌與平等并不是處理事物的兩種不同態(tài)度,相反,我們應該追求的是它們同時空的存在。
或許正像劉瑜所說,自信的國家和民族,不會那么的在意別人的批評和指責,也不會覺得別人的意見是在打壓你。大國的氣量是一個過程和階段,而我們還在路上。
鏈接
歷年元首演講中有代表性的學生提問
1998年時任美國總統(tǒng)克林頓在北京大學演講并回答提問
問題1:據(jù)我們所知,你來中國之前,在國內(nèi)表示,之所以去中國,是因為它太重要了,接觸是最好的壓制方式,你這句話是否是為了使這次訪華成行而向反對派作出的承諾?此時你站在講臺上,帶著偽善的微笑,這微笑背后是否還藏著真正的、壓制的初衷呢?請總統(tǒng)先生正面回答我的問題。
問題2:我個人認為,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對美國的文化、歷史、文學已有很多了解,對美國總統(tǒng)也知道得很多,我們還看了電影《泰坦尼克號》。但美國人對中國人民的了解卻似乎沒有那么多。也許他們只通過一些描寫文化大革命或農(nóng)村生活的電影來看中國。所以我的問題是,身為十年來第一位訪問中國的美國總統(tǒng),閣下計劃怎樣加強我們兩國人民的真正了解和尊重?
2003年時任英國首相布萊爾在清華大學出席 “圓桌會議”并回答提問
問題1:您大概是我爸爸的年齡,你像我父親一樣慈祥。您能不能像您對您的孩子那樣老實地告訴我們,您在伊拉克戰(zhàn)爭當中有沒有撒謊?
問題2:布萊爾先生,很榮幸能夠把您請到這里來。眾所周知大英博物館有大量的中國文物,對不起,我感到非常緊張。我喜歡你的領(lǐng)帶。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問你,中國的文物怎么跑到英國博物館來,你怎么回答?據(jù)報道,伊拉克博物館的很多文物被盜竊,這些失竊的文物會對大英博物館的收藏有所幫助嗎?
2004年時任美國副總統(tǒng)切尼在復旦大學演講并回答提問
問題:今年的總統(tǒng)大選是兩位耶魯人的競爭,您認為決定勝負的因素是什么呢?現(xiàn)在有越來越多的美國人生活在中國,你們準備怎么樣來贏得他們的選票?
2009年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在復旦大學演講并回答提問
問題1:因為您很難才能得到這個獎 (諾貝爾和平獎),所以我在想您是怎么得到這個獎的?還有您的大學教育怎么樣使您得到這個獎項?我們很好奇,想請您給我們分享一下您的校園經(jīng)歷,如何才能走上成功的道路?
問題2:總統(tǒng)先生,我是上海交通大學的學生。我的問題是,您來中國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你給中國帶來什么?又想從中國帶走什么?
問題3:我想問一個您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問題。您是如何看待您得獎的?您得了獎對您來說是不是意味著更多的壓力和責任?這會不會影響你解決世界問題的一些態(tài)度?
2010年英國首相卡梅倫在北京大學演講并回答提問
問題1:“作為英國的領(lǐng)導人,您能從中國模式中學到什么?”
問題2:為什么西方領(lǐng)導人總是來中國給我們上課教我們?nèi)绾蚊裰鳎?
- 破解帝國興衰的氣候密碼系列之馬背民族的遷都偉業(yè)(上篇) 2010-11-22
- 北京有何禮物 2010-11-19
- 北京東城區(qū)兩年間投放五千萬元文化產(chǎn)業(yè)扶持資金 2010-11-16
- 英政府要定期檢測民眾“幸福感” 2010-11-16
- 唐寧街新主人:卡梅倫 2010-11-10


 新浪微博網(wǎng)
新浪微博網(wǎng) 豆瓣網(wǎng)
豆瓣網(wǎng) 人人網(wǎng)
人人網(wǎng) 開心網(wǎng)
開心網(wǎng) 轉(zhuǎn)發(fā)本文
轉(zhuǎn)發(fā)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