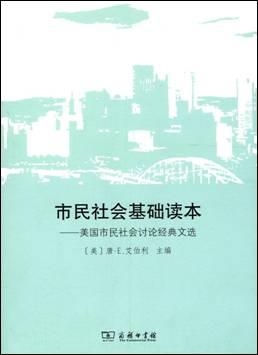導(dǎo)語:“公民社會(huì)”在理論上的最低限度應(yīng)該是存在不受國(guó)家干預(yù)的公共空間,再進(jìn)一步,這些處于國(guó)家與個(gè)人之間公共空間可以凝聚個(gè)人的意見并形成共識(shí),并由此再進(jìn)一步轉(zhuǎn)化為國(guó)家意志。但如果國(guó)家與個(gè)人之間不存在公共空間,或者,只有一些“偽公共空間”(即由國(guó)家干預(yù)下組合起來的公共空間),用“公民社會(huì)”的概念來解釋當(dāng)下的事情不僅沒有意義,而且也肯定是錯(cuò)的。
《市民社會(huì)基礎(chǔ)讀本》已經(jīng)出版一個(gè)多月了。“市民社會(huì)”(Civil So-ciety)是日本人的譯法,其實(shí)更應(yīng)該譯成“公民社會(huì)”。“市民社會(huì)”是九十年代開始為國(guó)內(nèi)學(xué)界熟悉的概念,它在西方的源頭雖然有黑格爾主義的意義,但90年代的興起卻基本上擺脫了黑格爾的詮釋,而與東歐國(guó)家的共產(chǎn)主義制度崩潰相關(guān)。在東歐的黨國(guó)制度結(jié)束后,重建公民社會(huì)成為聚焦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轉(zhuǎn)型的一個(gè)核心議題,而在東歐制度解體之前,東歐的一些知識(shí)分子就已經(jīng)不斷地提出“公民社會(huì)”的議題,哈維爾、亞當(dāng)·米奇尼克等人都認(rèn)為可以而且應(yīng)該不去理睬執(zhí)政者將要做什么,會(huì)給出什么承諾。在極權(quán)制度下,知識(shí)分子最正確的策略是自覺地將自己當(dāng)做一個(gè)“自由公民”,承擔(dān)一個(gè)“自由公民”的責(zé)任。就像哈維爾所說:相對(duì)于政治的荒謬,保持個(gè)人尊嚴(yán)的生活方式,是后極權(quán)制度下唯一道德的存在。
90年代初,也是“西學(xué)東漸”,“市民社會(huì)”或“公民社會(huì)”的概念一度成為國(guó)內(nèi)學(xué)界的熱點(diǎn),鄧正來就組織了一些討論,雖然很快無疾而終。不少人試圖用這個(gè)概念解釋中國(guó)當(dāng)時(shí)愈加自由化的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和吃喝嫖賭的社會(huì)生活,尋找至少在表面上呈現(xiàn)出多元化社會(huì)生活的正面積極意義,但,當(dāng)然對(duì)不上號(hào)!當(dāng)時(shí)一些西方學(xué)者也試圖做這一工作,卜正民和傅堯樂1997年編了一本《中國(guó)公民社會(huì)》的論文集,試圖對(duì)90年代以后經(jīng)濟(jì)多元化后的一些公共空間(行業(yè)團(tuán)體)進(jìn)行研究,但由于其中有對(duì)威權(quán)政治的嚴(yán)厲批評(píng),早就譯完的書一直無法出版。這件事本身也恰好證明了卜正民對(duì)中國(guó)社會(huì)生活的良好愿望的失敗。
我自己在很長(zhǎng)時(shí)間里對(duì)用“公民社會(huì)”來解釋中國(guó)當(dāng)下的事情是不以為然的。記得有一次一位朋友來講阿拉善聯(lián)盟的運(yùn)作,然后用“公民社會(huì)”的概念來解釋。我當(dāng)時(shí)就表示,“公民社會(huì)”在理論上的最低限度應(yīng)該是存在不受國(guó)家干預(yù)的公共空間,再進(jìn)一步,這些處于國(guó)家與個(gè)人之間公共空間可以凝聚個(gè)人的意見并形成共識(shí),并由此再進(jìn)一步轉(zhuǎn)化為國(guó)家意志。但如果國(guó)家與個(gè)人之間不存在公共空間,或者,只有一些“偽公共空間”(即由國(guó)家干預(yù)下組合起來的公共空間),用“公民社會(huì)”的概念來解釋當(dāng)下的事情不僅沒有意義,而且也肯定是錯(cuò)的。
但最近兩年,情況似乎有點(diǎn)變化。體制外的社會(huì)運(yùn)動(dòng)正不斷地穿透和壓迫權(quán)力的邊界,公共空間雖然還是灰色的,隨時(shí)可以被國(guó)家干預(yù)甚至被行政吸收,但事實(shí)上卻還是不斷地出現(xiàn),始終頑強(qiáng)地存在。就如卜正民在15年前所認(rèn)為的:“公共空間”即使在“法律上”被取消了,并不等于現(xiàn)實(shí)中就一定完全不見。相反,“國(guó)家—社會(huì)”這樣的基本關(guān)系一定會(huì)在各個(gè)層面,哪怕是以碎片的方式,散落地存在,并同樣發(fā)揮社會(huì)整合作用。只是不知道會(huì)否像80年代的經(jīng)濟(jì)改革,先在灰色地帶做,甚至長(zhǎng)期地以灰色的方式存在,然后,最終被追認(rèn)!只是,政治的空間,從無到有的演變,總會(huì)困難得多。
于是,這本《市民社會(huì)基礎(chǔ)讀本》就變得重要起來。“公民”是需要養(yǎng)成的,施蒂格勒(經(jīng)濟(jì)學(xué)諾獎(jiǎng)得主)在他的回憶錄中說他的工人父親在大蕭條時(shí)期每天到廣場(chǎng)上去參加工人集會(huì),手上拿著一本《羅伯特議事規(guī)則》,這就是“公民”的養(yǎng)成。《市民社會(huì)基礎(chǔ)讀本》可以幫助我們學(xué)習(xí)怎樣做一個(gè)公民。這是本精選出來的集子,大部分內(nèi)容都很好,最后一篇?jiǎng)t是哈維爾的“政治、道德與文明”,缺點(diǎn)是太理論化了一些,還是給知識(shí)分子準(zhǔn)備的,不能像施蒂格勒的父親那樣,薄薄一冊(cè),簡(jiǎn)單明了地運(yùn)用。
by 嚴(yán)搏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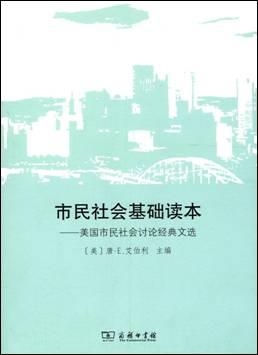
作者: [美國(guó)] 唐·E.艾伯利
譯者: 林猛 / 施雪飛 / 雷聰
出版社: 商務(wù)印書館
《市民社會(huì)基礎(chǔ)讀本》已經(jīng)出版一個(gè)多月了。“市民社會(huì)”(Civil So-ciety)是日本人的譯法,其實(shí)更應(yīng)該譯成“公民社會(huì)”。“市民社會(huì)”是九十年代開始為國(guó)內(nèi)學(xué)界熟悉的概念,它在西方的源頭雖然有黑格爾主義的意義,但90年代的興起卻基本上擺脫了黑格爾的詮釋,而與東歐國(guó)家的共產(chǎn)主義制度崩潰相關(guān)。在東歐的黨國(guó)制度結(jié)束后,重建公民社會(huì)成為聚焦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轉(zhuǎn)型的一個(gè)核心議題,而在東歐制度解體之前,東歐的一些知識(shí)分子就已經(jīng)不斷地提出“公民社會(huì)”的議題,哈維爾、亞當(dāng)·米奇尼克等人都認(rèn)為可以而且應(yīng)該不去理睬執(zhí)政者將要做什么,會(huì)給出什么承諾。在極權(quán)制度下,知識(shí)分子最正確的策略是自覺地將自己當(dāng)做一個(gè)“自由公民”,承擔(dān)一個(gè)“自由公民”的責(zé)任。就像哈維爾所說:相對(duì)于政治的荒謬,保持個(gè)人尊嚴(yán)的生活方式,是后極權(quán)制度下唯一道德的存在。
90年代初,也是“西學(xué)東漸”,“市民社會(huì)”或“公民社會(huì)”的概念一度成為國(guó)內(nèi)學(xué)界的熱點(diǎn),鄧正來就組織了一些討論,雖然很快無疾而終。不少人試圖用這個(gè)概念解釋中國(guó)當(dāng)時(shí)愈加自由化的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和吃喝嫖賭的社會(huì)生活,尋找至少在表面上呈現(xiàn)出多元化社會(huì)生活的正面積極意義,但,當(dāng)然對(duì)不上號(hào)!當(dāng)時(shí)一些西方學(xué)者也試圖做這一工作,卜正民和傅堯樂1997年編了一本《中國(guó)公民社會(huì)》的論文集,試圖對(duì)90年代以后經(jīng)濟(jì)多元化后的一些公共空間(行業(yè)團(tuán)體)進(jìn)行研究,但由于其中有對(duì)威權(quán)政治的嚴(yán)厲批評(píng),早就譯完的書一直無法出版。這件事本身也恰好證明了卜正民對(duì)中國(guó)社會(huì)生活的良好愿望的失敗。
我自己在很長(zhǎng)時(shí)間里對(duì)用“公民社會(huì)”來解釋中國(guó)當(dāng)下的事情是不以為然的。記得有一次一位朋友來講阿拉善聯(lián)盟的運(yùn)作,然后用“公民社會(huì)”的概念來解釋。我當(dāng)時(shí)就表示,“公民社會(huì)”在理論上的最低限度應(yīng)該是存在不受國(guó)家干預(yù)的公共空間,再進(jìn)一步,這些處于國(guó)家與個(gè)人之間公共空間可以凝聚個(gè)人的意見并形成共識(shí),并由此再進(jìn)一步轉(zhuǎn)化為國(guó)家意志。但如果國(guó)家與個(gè)人之間不存在公共空間,或者,只有一些“偽公共空間”(即由國(guó)家干預(yù)下組合起來的公共空間),用“公民社會(huì)”的概念來解釋當(dāng)下的事情不僅沒有意義,而且也肯定是錯(cuò)的。
但最近兩年,情況似乎有點(diǎn)變化。體制外的社會(huì)運(yùn)動(dòng)正不斷地穿透和壓迫權(quán)力的邊界,公共空間雖然還是灰色的,隨時(shí)可以被國(guó)家干預(yù)甚至被行政吸收,但事實(shí)上卻還是不斷地出現(xiàn),始終頑強(qiáng)地存在。就如卜正民在15年前所認(rèn)為的:“公共空間”即使在“法律上”被取消了,并不等于現(xiàn)實(shí)中就一定完全不見。相反,“國(guó)家—社會(huì)”這樣的基本關(guān)系一定會(huì)在各個(gè)層面,哪怕是以碎片的方式,散落地存在,并同樣發(fā)揮社會(huì)整合作用。只是不知道會(huì)否像80年代的經(jīng)濟(jì)改革,先在灰色地帶做,甚至長(zhǎng)期地以灰色的方式存在,然后,最終被追認(rèn)!只是,政治的空間,從無到有的演變,總會(huì)困難得多。
于是,這本《市民社會(huì)基礎(chǔ)讀本》就變得重要起來。“公民”是需要養(yǎng)成的,施蒂格勒(經(jīng)濟(jì)學(xué)諾獎(jiǎng)得主)在他的回憶錄中說他的工人父親在大蕭條時(shí)期每天到廣場(chǎng)上去參加工人集會(huì),手上拿著一本《羅伯特議事規(guī)則》,這就是“公民”的養(yǎng)成。《市民社會(huì)基礎(chǔ)讀本》可以幫助我們學(xué)習(xí)怎樣做一個(gè)公民。這是本精選出來的集子,大部分內(nèi)容都很好,最后一篇?jiǎng)t是哈維爾的“政治、道德與文明”,缺點(diǎn)是太理論化了一些,還是給知識(shí)分子準(zhǔn)備的,不能像施蒂格勒的父親那樣,薄薄一冊(cè),簡(jiǎn)單明了地運(yùn)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