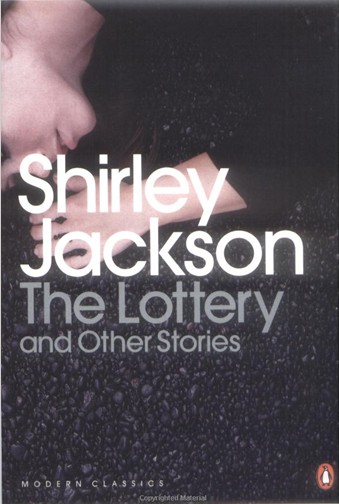
作者:The Lottery and Other Stories
出版社: Penguin Classics
出版日期:2009年10月
by羅四鸰
如果你的朋友們紛紛都從橋下跳下去,你會不會也跳下去呢?對此,美國女作家雪莉·杰克遜的回答是:“Yes!”何以見得呢?于是,32歲的杰克遜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這便是1948年6月26日發(fā)表在《紐約客》上的短篇小說《摸彩》(The Lottery)。《摸彩》的故事很簡單:6月27日,美國某個300人的村莊舉行著一項古老的摸彩活動。沒有人知道這項傳統(tǒng)的由來,所有的儀式都變得有些敷衍,但無論是大人還是小孩都必須參加,甚至腿斷了而不能出席的克萊德?鄧巴也由其妻子代抽簽。第一輪由戶主代表全家去抽簽,那張畫著黑點的“彩票”被哈沁森太太的丈夫比爾抽到。于是下一輪抽簽在哈沁森先生、哈沁森太太以及他們的小女兒小兒子一家四人之間進行。盡管哈沁森太太表示反對,甚至要求已經(jīng)出嫁的大女兒也參加最后一輪抽簽已降低概率,但并不能阻止厄運的降臨:哈沁森太太——這場儀式的唯一遲到者抽到了那張彩票。哈沁森太太在廣場中央尖叫“不公平不公正”,可是此時,村子里的人開始紛紛對她扔石頭,以便盡快結(jié)束這場儀式,可以趕回家吃午飯。
《摸彩》很短,一萬來字,猶如一個恐怖的寓言,一個月后,杰克遜在《舊金山紀事報》上對她的讀者說:“要解釋我想在這個故事中想表達什么非常困難。我猜想,我是希望通過講述一個發(fā)生在現(xiàn)在,發(fā)生在我村子里的古老野蠻儀式,讓我的讀者感到震驚,震驚于他們自身生活中無意義的暴力和普遍的非人性所構(gòu)建的戲劇般的事實。”其實,杰克遜所要表達的,幾乎正是法國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在其1895年出版的《烏合之眾》所表達的:群體究竟通往何處?在勒龐看來,群體的從眾心理會讓約束個人的道德和社會機制失效,“孤立的個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時,他不能焚燒宮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這樣做的誘惑,他也很容易抵制這種誘惑。但是在成為群體的一員時,他就會意識到人數(shù)賦予他的力量,這足以讓他生出殺人劫掠的念頭,并且會立刻屈從于這種誘惑。出乎預料的障礙會被狂暴地摧毀。”經(jīng)歷過集中營集體瘋狂年代、生活在冷戰(zhàn)恐懼中的杰克遜,對群體更是不抱任何希望。“一個人可能是偉大的,但一群人就成了一頭畜生,而且是一頭自己會吃掉自己的畜生。”即便是人人有平等機會參與的民主形式,在杰克遜看來,依然可能是殺害個體的一種集體施暴方式,并打著一個堂而皇之的幌子,一如《摸彩》中哈沁森太太之死。而最令人恐怖的是,即便是民主,也無法阻止人性的黑暗。哈沁森太太要求已出嫁的女兒參加抽簽以降低中簽概率、一位村民把石頭放到哈沁森太太小兒子手里讓他砸自己的母親等可怕的細節(jié),讓杰克遜的母親都為此與之翻臉。
頗為諷刺的是,震驚的讀者的反應以及招致的群體怨恨似乎更讓杰克遜震驚。小說發(fā)表的那個夏天,不斷有讀者因此取消《紐約客》的訂閱,給雜志和她寄去惡毒的信,不僅有右派,更有熱愛民主的左派。那時,杰克遜每天差不多要收到8到10封信,還不包括每周《紐約客》給她寄去的裝滿讀者來信的包裹。1960年,在一次演講中,杰克遜回憶說:“我完全沒有想到過,會有如此多的人愿意坐下來給我寫那些我甚至都不敢打開看的信。那個夏天,在我看過的三百封奇怪的讀者來信中,其中只有十三封是友好的,他們幾乎全部來自我的朋友。”
幸虧,杰克遜對自己的小說非常有信心:“即使我只寫作和出版了這么一篇故事,人們也一定永遠不會忘記我的名字。”她的丈夫,文學批評家斯坦利·海曼說:“她總是很驕傲南非聯(lián)盟禁了《摸彩》,因為她覺得他們至少理解了這個故事。”而對于自己的作家妻子,他的評價是:“她猶如我們這個時代敏感而又自信的解剖家。”而今,時間已經(jīng)證明,他們兩人是對的。《摸彩》不僅被視為最經(jīng)典的短篇小說之一,還被改編成電視、電影,搬上舞臺,更是進入美國中學大學教材。我正是在我的課堂上讀到這篇小說的,老師以此教導我們認識集體無意識行為以及置身其中的個體。彼時,傳來地球另一頭多個城市出現(xiàn)打砸搶的消息,一位無辜市民被砸穿顱骨。我才真正感覺到《摸彩》的恐怖,原來這個故事并不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