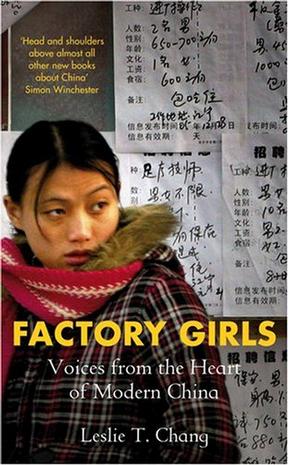
Leslie T. Chang(張彤禾)/著
Picador USA
2009.02
by張彤禾
1.
十九世紀(jì)下半葉,華北遭遇干旱和饑荒,逃荒的人使得東北的人口開始膨脹。我的家庭也在這次經(jīng)濟(jì)急速發(fā)展中脫穎而出。我的曾祖父張雅南,買了一個(gè)榨油廠和一個(gè)面粉廠,運(yùn)用這投資賺來的錢成為六臺最大的地主。1890年左右,張雅南監(jiān)督建造了一座有五個(gè)堂屋八個(gè)廂房的大宅院。祖先的牌位和畫像占領(lǐng)了堂屋,而活人則在廂房里吃飯、勞作、睡覺。中國家庭就是這樣生活的——死人把活人擠到一邊,而恪守孝道則嵌入到每一個(gè)房子的建造工程之中。這個(gè)宅院被命名為“新發(fā)源”,意思是“新的發(fā)源地”。宅院四周有高墻,毛瑟槍從每個(gè)角落的高處伸出,還有武裝民兵保護(hù)它不受強(qiáng)盜侵犯。一個(gè)家族有多富裕要看這個(gè)家吃的是什么,而在新發(fā)源,即使是雇來的幫手也能吃上豆沙包。
1898年我的祖父張春恩出生,幾乎村子里的每個(gè)人都姓張。從幼年起,他在家里的私塾上學(xué),長篇大論地背誦上溯到孔子時(shí)期的四書五經(jīng)。這些文字他懂不懂并不重要:教育是要塑造一個(gè)孩子循規(guī)蹈矩的言行舉止,早早地灌輸他溫良恭儉的美德。學(xué)習(xí)的終極目的是通過科舉考試,成為朝廷命官——這個(gè)制度基本上持續(xù)不變已長達(dá)一千年。
但那個(gè)世界在我祖父還是個(gè)小男孩的時(shí)候已經(jīng)開始土崩瓦解。十九世紀(jì)和西方的接觸讓中國碰得遍體鱗傷;十九世紀(jì)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在兩次鴉片戰(zhàn)爭失利之后,清朝君主被迫簽訂了一連串“不平等條約”,開埠通商,給予西方列強(qiáng)和日本經(jīng)濟(jì)和法律的特權(quán)。國內(nèi)改革派人士大肆譴責(zé)傳統(tǒng)教育造成了中國的屈辱衰落。他們的努力終于在1905年正式廢除了科舉制度,各地開始設(shè)立傳授現(xiàn)代知識的新學(xué)堂。1911年,我祖父剛剛十二歲,清朝覆亡,共和政體取而代之。
我的祖父還是個(gè)孩子時(shí),已經(jīng)下定決心要離開家了——和現(xiàn)在一樣,所有通往成功的道路都是指向村外的。他的哥哥張奉恩以后有一天會主持家業(yè)。但是作為正房的第二個(gè)兒子,我的祖父占了個(gè)優(yōu)勢:他可以離開。1913年春天,他入讀吉林中學(xué)。這是本省第一個(gè)教授新學(xué)的學(xué)校,它略過傳統(tǒng)的四書五經(jīng)而主張教授數(shù)學(xué)、歷史、地理和自然科學(xué)。三年之后,祖父離家去上北京大學(xué),全國現(xiàn)代學(xué)校系統(tǒng)的翹楚。
當(dāng)時(shí)北京大學(xué)的多數(shù)學(xué)生來自沿海一帶富裕的商賈家庭;我的祖父是個(gè)局外人,有些像個(gè)科羅拉多州采礦小鎮(zhèn)拿獎(jiǎng)學(xué)金的孩子出現(xiàn)在哈佛大學(xué)。和我祖父同時(shí)期在北大,有位在圖書館工作的,名叫毛澤東。
如果傳統(tǒng)的價(jià)值體系完好無損,我祖父很可能取得大學(xué)最高學(xué)位,順利地在政府找到工作。但是新學(xué)已經(jīng)把他帶往意想不到的方向:祖父獲得一個(gè)省級獎(jiǎng)學(xué)金,送他去美國留學(xué),于是他念完大二就退學(xué)了。他娶了一位叫李秀蘭的年輕女士,是家里給定的親——婚后第三天,他登上了開往美國的輪船。
我的祖母當(dāng)時(shí)在北京女子師范學(xué)院讀書,這也是全國最早收女學(xué)生的院校之一。她的本科是體育和音樂。她參加學(xué)生示威游行,抽煙,還改了個(gè)新名字:李薌蘅, 她喜歡這兩個(gè)更罕見的字。畢業(yè)之后她在省會吉林市一所高中教書。
2.
我的祖父1920年到達(dá)美國。那是個(gè)私釀金酒,愛撫晚會和黑幫教父的時(shí)代,但是他簡直沒注意過這些時(shí)髦事。日記的字里行間都是關(guān)于他探索值得學(xué)習(xí)的課程和中國的政治局勢。這兩個(gè)主題相互關(guān)聯(lián):通過在美國掌握正確的技能,他才了解能幫助祖國成為一個(gè)現(xiàn)代國家必備的知識。他心不在焉地學(xué)了點(diǎn)兒文學(xué)和經(jīng)濟(jì)學(xué),最終鎖定了采礦工程:發(fā)展工業(yè)必能拯救中國。
幾千個(gè)中國學(xué)生在二十世紀(jì)的頭二十年去到美國,這也是最早的出國留學(xué)大潮。他們視西學(xué)為幫助中國最有效的辦法,因此傾向于學(xué)習(xí)實(shí)用的學(xué)科,比如經(jīng)濟(jì)學(xué),自然科學(xué),尤其是工程學(xué)科——從1905~1924年間大約三分之一的中國留學(xué)生選擇了工程學(xué)。我的祖父在密歇根礦業(yè)學(xué)院求學(xué),那里靠近加拿大邊境的一個(gè)古老的銅礦地區(qū)。他于1925年畢業(yè),全班四十四個(gè)學(xué)生中排名三十三。顯然對他,新學(xué)很不容易應(yīng)付。
我也是偶然發(fā)現(xiàn)祖父的日記。我父親說家里這些年經(jīng)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內(nèi)戰(zhàn)、去臺灣、來美國,他們把一切家當(dāng)都棄之不顧了。我開始調(diào)查家史一年多以后,我和父親通電話,問他有沒有屬于他父親的東西。意料之外的是,他說他身邊有兩本日記,一本是我祖父在美國寫的,另一本是全家戰(zhàn)時(shí)住在重慶時(shí)寫的。兩本日記大概有一千多頁。“沒什么意思,”我父親說。“他就寫了一些像是‘今天日本軍隊(duì)逐漸逼近城市’這樣的東西。”“其實(shí),”我說,“那很有意思。”
透過他日記的字里行間,我逐漸了解我從來沒見過的祖父。他是一個(gè)上下求索的年輕人,夢想能從事各行各業(yè)。他像農(nóng)民工一樣干一行,換一行,很快心生厭倦又很焦慮他學(xué)得不夠。他孤獨(dú)寂寞漂泊無定。自強(qiáng)是日記里不變的主題。完成學(xué)業(yè)后,我的祖父在東北部和中西部的工廠和礦山做了兩年實(shí)習(xí)訓(xùn)練。他在芝加哥上夜校學(xué)習(xí)電機(jī)。一篇篇日記里零星夾雜著他想要記下的陌生單詞:古德曼標(biāo)準(zhǔn)短壁機(jī)、水泥沙子爐渣比、金字塔泵平爐攪拌機(jī)高爐波紋底架門。
在美國的那些日子,我的祖父改了他的中文名字。新選擇的漢字,莘夫,出自一個(gè)古老的成語,莘莘征夫,翻譯過來就是“許多勤勉出征的男子”——我的祖父立志成為這樣的人:一大群人,致力于盡忠服務(wù),而自我則消隱在名字里。
祖父在1927年夏天回到中國。他回家的第一天,他的父親在村里辦了一場接風(fēng)慶典,慶祝他最寵愛的兒子千里迢迢從美國給家里帶回榮耀。第二天,一家之主拿出一根叫做“家法”的木棍——傳統(tǒng)的家庭用家法來懲戒小孩和傭人——打了他一頓。在美國,他的兒子從文學(xué)專業(yè)轉(zhuǎn)到學(xué)礦業(yè)工程,而竟不先征得家長的認(rèn)可。姑且不論這位父親遠(yuǎn)在一萬公里以外,加上對美國大學(xué)體制毫無所知。在中國家庭里,父親的話就是法律。這一頓好打,我祖父好幾天都不能坐下來。
他的父親想要他留在家里幫忙管理家業(yè),但是這個(gè)年輕人拒而不從: 他厭恨張家大院生活的糾葛,很高興能逃脫。他在中國遙遠(yuǎn)的東北哈爾濱的穆棱煤礦得到礦長的職位。
1931年,日本軍隊(duì)長驅(qū)直入東北的南端。六個(gè)月內(nèi),日本軍隊(duì)占領(lǐng)了整個(gè)東北,建立了偽滿洲國。日本人來了之后,我的祖父到了關(guān)內(nèi)。
1937年戰(zhàn)爭爆發(fā)的時(shí)候,我的祖父在河南一個(gè)煤礦當(dāng)?shù)V長, 他幫忙把設(shè)備從河南運(yùn)到八百公里外的四川內(nèi)陸。作為國家資源委員會——負(fù)責(zé)戰(zhàn)時(shí)建設(shè)國家工業(yè)基礎(chǔ)的政府機(jī)關(guān)——的一名官員,他被派遣到偏遠(yuǎn)礦區(qū),監(jiān)督戰(zhàn)略性物資的生產(chǎn)。他通常會先去到一個(gè)地方,等到情況安定時(shí)再給我祖母寫信。五個(gè)孩子,一個(gè)個(gè)都出生在邊遠(yuǎn)的礦業(yè)城鎮(zhèn)。老大藹蕾出生在哈爾濱煤礦,那時(shí)我的祖父從美國回來后在那里工作;我的伯伯立豫和我父親在河南中部的煤礦地區(qū)出世。四川煤礦,小姑姑藹鎣出生;湖南汞礦,叔叔立程。我祖父的理想主義在這些與世隔絕的地方留下足跡。大多數(shù)留學(xué)歸來的學(xué)生生活在大城市,但是祖父認(rèn)為他的工作在國家相對落后的地方更有意義。
個(gè)人關(guān)系被切斷了——在戰(zhàn)爭的混亂局勢中,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別人失去聯(lián)系。一家人會到一個(gè)新的地方,剛送孩子入學(xué),接著幾個(gè)星期之后又離開。伯伯立豫跟我說,他小學(xué)六年搬了七個(gè)地方。和農(nóng)村老家聯(lián)系非常困難:寫給東北的家書必須繞遠(yuǎn)路避過封鎖線。更令人驚奇的是,人們這樣還能再次找到彼此。戰(zhàn)爭快結(jié)束的一天,一個(gè)叫趙鴻志的很帥的大學(xué)生走進(jìn)重慶礦業(yè)局員工餐廳,認(rèn)出了我的祖父。他家和我們十多年前在河南煤礦就有了交情。趙鴻志受邀到家里吃晚飯,并開始追求我的大姑姑, 他們從小就認(rèn)識。
戰(zhàn)爭期間也有家人重聚。我祖父的哥哥留在家里照顧家業(yè),他的兒子張立教, 到北京上學(xué),當(dāng)時(shí)我的家人也住在北京。傳統(tǒng)中國家庭里,親兄弟和嫡堂親是一樣的親。我的祖父祖母給立教住的地方,給他付學(xué)費(fèi);我伯伯和我父親從孩提時(shí)候就學(xué)著向“立教哥”看齊。以后為躲避日軍進(jìn)犯一家人搬到重慶的時(shí)候,立教也和他們同行。
對我的祖父來說,戰(zhàn)爭時(shí)期令人沮喪。戰(zhàn)爭不光奪取生命造成毀壞,工作難以為繼,事業(yè)中斷,交通阻隔。偶爾他也會懷疑這樣工作是否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