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慶全:沒有故事都能看出大片來。
沈志華:所以我們這套書沒有過多過激的觀點,做什么絕對化的結論都很少。主要就是講歷史上的事,但是我不知道為什么沒有一家出版社。
徐慶全:我給你解釋,為什么咱們好多書其實沒有什么問題出不來?現在在我們這個地方,我們這個出版界,我是在雜志社,也算出版界。現在有一種出版界有一種很不好的做法,我稱之為叫“自我放大化”,或者“自我限制化”,“自我放大化”是什么?中宣部下一個指令,我們就是這么一個指頭這么粗,到了省地這一級,就變成這么粗了,到了地市的出版社就這么粗了,就一層一層放大,這種自我放大化,導致很多的出版社老總放大到自我約束的地步,考慮“我出了以后會不會怎么著”,首先把自己放大住了,所以你的書出不來。你這個書當中很精彩的反映的那部分都沒放進來,因為他的文章我讀過,07年我們四個人,沈志華、章詒、我,還有謝泳,我們四個人合寫了一本書叫《50年無祭而祭》,我很早就看了這些東西,寫得很精彩,后來我拿到這個書以后,覺得這個書只有前半部分,沒有后半部分,我還納悶,說實在也沒有什么大的問題。
沈志華:后來是廣東人民想了一個招兒,因為我在寫那書的過程當中,寫了幾篇論文,一個問題一個問題的研究過,比如說知識分子會議問題、中共八大的問題、波匈事件的問題、莫斯科會議等。他說你干脆以論文集的形式出版,因為都是大陸發(fā)表過的,估計能通過,這么著,后來就把這本書編出來了,編出來,但是我一直覺得就那一篇沒發(fā)表,就給塞進去行了。他說十八大以后出也許就可以了,結果十八大以后出還是不行。這就是這本書的整個來源,我想下面講兩個事,一個講我整體的想法是什么?就是寫這本書。第二個把最后那一章大概的內容跟大家介紹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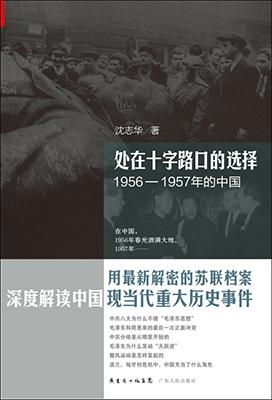
副標題: 1956--1957年的中國
作者: 沈志華
出版社: 廣東人民出版社
中國的思考與選擇
沈志華:其實我原來那個題目也差不多,叫“思考與選擇”。我覺得中共這個政權,其實從一開始面臨著一個“合法化”的問題,因為中共向所有的革命黨一樣,不是通過選舉掌握政權的,而是通過革命,通過暴利推翻了一個政權建立了一個新的政權。這個歷史過程,從歷史發(fā)展的角度來講,是有它存在的合理性的,特別是在中國,通過王朝更替建立新的政權不乏先例,這有很多,要不然現在還是在周朝,其實有這個更替。但是進入現代社會有一個問題,就是還能不能繼續(xù)走原來歷史的循環(huán)的路子,王朝更替的路子?不行了。從18世紀特別19世紀以后,隨著現代化的發(fā)展,國際聯絡的打通,現在人們越來越考慮到這種合法性的問題,對于一個中共這樣的執(zhí)政黨來講,其實他也面臨這樣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最好的一個解決機會就是1956年。為什么呢?就是從革命黨自身來講,它提出的目標到1955年基本上完成了,或者說到1956年1月基本完成了。你要推翻舊的社會呢?那你已經都推翻了,你不是消滅國民黨反動派嗎?那你已經都消滅了,地主、富農、資本家也都沒了,反動的知識分子也都被你改造了,社會也都統一了。
徐慶華:稍帶著打了一場朝鮮戰(zhàn)爭。
沈志華:對了,打了一場朝鮮戰(zhàn)爭,國際威望也提高了。你所要求的那個社會制度的改造,也在制度層面上實現了,所謂“制度層面實現”就是“三化一改”已經完成了。所以在這個時候你又有那么高的威望,又得到了全國多數人的認同,應該說1955年到1956年,共產黨的威望非常高,就是在社會各階層當中,大家當時都是比較認同的,認為中國共產黨掌握政權以來給中國換了一個面貌,帶來了新的發(fā)展各個方面,特別是中蘇關系比較好的情況下,蘇聯的大量援助等等。在這樣一個情況下又出現了一個國際背景,就是蘇共二十大。因為中國制度學的是蘇聯,但是蘇聯到蘇共二十大的時候,其實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問題就出現了,但是到了蘇共二十大正式提出這個問題,他們要修改這個制度,用現在的話講就是改革,就是蘇聯人已經認識到他們自己那個社會制度是有問題的。當然怎么改?這個還差得很遠。也跟中國改革開放提出的問題是一樣的,但是當時的蘇聯解決思路還沒有成熟。在這個時候,中共其實也開始發(fā)現問題了。從不同的角度,就不展開說了,展開說就很復雜了,反正也發(fā)現問題 。
其實蘇聯提出批判斯大林,提出批判個人崇拜,搞民主化,搞經濟擴大地方權利等等一系列的措施,八大也都提出來,所以中共那會也意識到這個問題,毛澤東甚至提出兩個“萬歲”,兩個“萬歲”知道是什么嗎?說“共產黨萬歲,民主黨派也要萬歲”,意思就是長期共存,毛還甚至說過這個話,說多黨制也可以考慮嘛。他至少是有這種空間,有這種條件,逐步實現國家的選舉制、議會制,從一黨專政變成走向多黨制,就有這種空間,有這個可能。所以我覺得1956年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國內國外的條件也都具備。但是出現了種種的問題,主要的問題就是波匈事件。波匈事件現在談的人不多,但是你要到東歐,這二十年就是圍繞著波匈事件,我老去開會他們談的都是這個。波匈事件是值得好好寫一本書的,我下次我就寫這本書,到底波蘭、匈牙利怎么發(fā)生的這個事?這個事對這個社會到底有什么影響?其實對他們本身的影響不是很大,因為主要就是反思,說起來也很復雜。就是原來斯大林是跟這些東歐各國共產黨說,你們走你們的路,我們走我們的路,這個社會主義是條條大路通羅馬,也不一定都學蘇聯,這是1944年到1946年斯大林說的話,所以當時東歐各國共產黨都走自己的路,那個時候的社會主義陣營是多元的,到冷戰(zhàn)出現,就是1947年美蘇對抗以后,斯大林突然發(fā)現,不能讓他們多元,一多元“我”指揮誰去,“我”說話誰都不聽。
徐慶全:冷戰(zhàn)沒有一方就不行,團結一方才行。
沈志華:還有共產黨的情報局的成立,很多人以為共產黨的情報局成立是為了跟美國對抗,當然不錯,是跟美國對抗,但是他主要的方針和戰(zhàn)略不是對美國去的,而是對這七個東歐國家去的。因為要內部整蘇(徐慶全補充,就是華沙條約那會),所以就有批鐵托等人的,后來一直懷疑毛澤東是是“鐵托”。從那以后1947年,特別是1948年2月捷克政變以后,到1952年,整個東歐的蘇聯化實現了、完成了。這是在高壓強制推行一種體制的這種狀態(tài)下,而且東歐國家的共產黨都分兩派,一個是本土派,一個是莫斯科派,就是二戰(zhàn)的時候都逃到蘇聯去的,在共產國際參與工作的這批人,這批人戰(zhàn)后都回到各國,然后就和本土派,當時在國內堅持反法西斯的人就形成了兩種觀點,當然莫斯科派就非常親蘇,而這些民族主義的人比較強烈。后來在1948年到1952大清洗當中,斯大林基本上把東歐本土派的民族主義情緒比較高的人全殺了。不是吊死就是槍斃。
徐慶全:我給你插一句,他講的這些東西我可以講講中國的情況,中國跟東歐有點相反。咱們到延安以后,或者從長征開始一直到延安,我們也存在兩派,一個是本土派,一個是莫斯科派,莫斯科派是王明,從蘇聯回來的,所以毛澤東稱為“言必稱馬列”的這些人,這個結果什么呢?毛通過一次整風,把身邊幫派全給滅了,跟東歐不一樣,東歐是本土派給滅了。
沈志華:所以蘇共二十大一批判斯大林,莫斯科派受壓,本土派又起來了,這是東歐當時的情況。
其實中國,開始時毛是非常有信心的,他認為中國絕對不會出匈牙利事件,當時1956年中國共產黨號召要搞“雙百方針”的時候,中共高層有很多人擔心,說這樣做,這不是自己給自己找麻煩嘛?但是毛澤東很有信心,說不會的。赫魯曉夫也很擔心,說“毛澤東同志您不能這么做?聽說你們那兒百花齊放,毒草也可以放出來,我們這兒鏟還來不及呢?”毛說我們情況跟你們不一樣,你們那兒階級斗爭沒搞好,我們階級斗爭已經搞完了,搞得很好,一個“正反”我就我就殺了70萬人,反革命都沒了,誰來造反,沒了,沒人造反。所以當時,對波匈事件的反應,毛最初的想法是覺得,中國沒有問題,中國的問題在哪兒?中國不是沒問題,也有問題。因為當時波匈事件處理是劉少奇和鄧小平去的,回來以后11月3號開中央全會,向全黨向毛匯報這個事,當時的會議記錄我看了,他們討論的時候這點中央是非常一致的,“如果處理不好這個政權還會出問題”。原來認為沒問題,政權已經鞏固,因為敵人不存在了,敵人不存在沒人奪你的權,你出什么問題?除非就是帝國主義打進去,那是另一回事,國內是不會出這個問題的 ,因為敵對的階級已經不存在了,大規(guī)模的急風暴雨似的階級斗爭已經過去了,這是八大的結論。波匈事件讓中共領導人提醒還是有問題的,這個問題不是出在原來意義上的階級敵人,而是人民。就是被你統治的老百姓,因為他們會起來造反,因為匈牙利這個事件主要就是市民起來鬧事。波蘭事件還有些不同,但性質也差不多,主要是波茲南事件,問題這不就出來了,所以那個時候毛提出了一個“正確處理內部矛盾”的問題。這個問題提得對,是,你現在執(zhí)政黨處理得就是你和執(zhí)政黨和人們之間關系的問題,那這個問題出來以后,再往下這點中央都是一致的,我看劉少奇,朱德,周恩來大概這個想法是一致的,要解決執(zhí)政黨和老百姓關系的問題。這個問題不是現在才提出來的,不是十八大提的,是八大就提的,結果過了十個代表大會還沒解決。
徐慶全:我們現在做得簡單,“維穩(wěn)”兩個字就解決了。
沈志華:當時就出了兩個思路,毛的一個思路,是比較傳統的。比如看毛澤東他在西柏坡的很多講話是特別值得注意的,就是當他要掌握這個政權,“我要進紫禁城了,我要坐上金鑾寶殿會出現什么問題?”這是毛當時想的,他一路走的時候說“咱進京趕考”,“不做李自成”,想來想去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所以毛最擔心的就是這個隊伍自身的腐敗。他一直讓黨內警惕出現李自成那樣的問題,就郭沫若寫一個甲申300年記,毛澤東發(fā)全黨閱讀,大家都看看李自成是怎么進北京城,后來又怎么被趕出來的。就是這支隊伍腐敗了,農民軍腐敗了,所以他一直講什么“糖衣炮彈”的問題,什么資產階級的進攻等等。這個是毛非常擔心的問題,那么在1956年底,1957年初的時候他還是從這個角度提出問題,就是要整黨,這個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執(zhí)政黨,所以把黨要干部要清廉,取消官僚主義,主觀主義等等,他覺得這個問題要解決了,矛盾就不存在了,天下就坐穩(wěn)了,隊伍就一代一代傳下去了,這是毛的一個主要理念。劉少奇、周恩來包括陳云的我看他們的發(fā)言,包括后來做的一些決議,他們主要認為主要是政策的問題,
徐慶全:體制問題。
沈志華:比如他說工人不滿,為什么?你工資太低,你給提高工資不就完了,農民不滿,為什么?你把他限制太死了,你不讓他養(yǎng)豬、養(yǎng)鴨你都集體化了,他能滿意嗎?你放寬點,你讓他多養(yǎng)點豬,多養(yǎng)點鴨子,養(yǎng)點雞不就完了。知識分子不滿意,你允許私人辦學就可以了嘛。嫌房子少你讓他蓋房子,提了好多類似這樣的問題,對共產黨不滿主要是,其實那會還談不到兩極分化,也沒有這個詞,但是“干部特殊化”這個問題要解決,比如說房子多了、有專車,有警衛(wèi)員,有廚師這個都應該去掉等等。他們的思路是從政策上解決,化解這個矛盾,這個社會就應該不會出大的問題。所以這個時候還沒有發(fā)生正面的沖突,至少你看會議記錄沒有,但是做法就不一樣了,毛澤東就號召整風整黨,但是你看周恩來、劉少奇他們從來不提這個事。這個也難怪,因為一個延安整風大家都怕了,這毛又提整風還要整誰?所以我看了底下好多做報道,在云南做的報導說這個整風跟延安絕對不一樣,這個不做組織處理,不是背靠背的,就是學習,主要是學習文件。劉少奇到中央黨校做報告也是說,整風就是學習嘛,其實這是跟毛的想法是不一樣的,你就能看出來,誰想做什么事?
徐慶全:我跟他的觀點有點不一樣,我得說幾句,你老拿著麥克風,就成麥霸了。你們對他熟悉嗎?我跟他1993年認識的,他比我長一輪,算我的老大哥。我寫過一篇文章叫《游擊隊員沈志華》,網上應該有,專門寫他的光輝事跡。
咱們從十八大以后,一般十八大以前書法家題字都提“觀海聽濤”四個字,十八大以后書法家寫字都愛寫“好好學習”,這個沈志華就是好好學習的典范。我說他好好學習他是非常努力,非常嚴格要求自己的人,我比他小一輪,但是我一點沒有斗志,他的斗志蠻強,我跟他有一個習慣都是一樣的,我們幾乎都是早上起來,我一般都是3點半就起床,他也一樣,但是他睡得比我晚,我一般9點鐘睡覺,不好意思農民的習慣,他可能得11點睡,但是3點半起,我一般3點半起來干活干到11點半就不干了,下午和晚上看電視或者晚上喝酒去了,他一直干到晚上7點,所以他很努力,他的成果是一本一本出。我寫關于他的經歷的《游擊隊員沈志華》你們可以自己查,但是強調一點,我在那個文章當中講了一些他做學問的方式。沈志華做學問,我覺得他基本呈現的一種方法叫“二重證據法”,這個是王國維提出來的。
王國維1925年在清華大學,他認為當時在20年代我們的考古發(fā)掘,地下出了很多材料,出了很多器物,用史書的材料再結合地下出土的材料,兩種材料來互證,王國維叫“二重證據法”,我覺得沈志華真從這種做學問的方式,他不止是二重,他是三重。我們看這個書當中,他文章當中提到的材料來源,他講了四個方面的材料來源。他是跟各種各樣的材料在一起互證,超出了王國維提倡的二重證據法,所以他的學問做的非常的扎實,扎實得你讀他的書,你根本在史料上根本挑不出毛病。當然我跟他講,吃飯我們倆爭吵,他得有些觀點——他當然是老大哥,學問不分老少,我倒想介紹一下這本書,當時沈志華志華講了半天,講了他的研究心得,我覺得咱們今天是做這本書的,介紹一下。
抉擇之因
徐慶全:沈志華講叫“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講的是1956到1957年的中國,實際上在我看來這個題目出得非常好,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不僅是中國,其實東歐和蘇聯也是這樣,也處在1956年到1957。蘇聯和東歐剛才講的也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這是從書名來講,比他其他書名都好得多,所以我說出版社取得書名比較高。比你那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