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2月7日晚上,我對(duì)著《深圳舊志三種》一書發(fā)了一會(huì)呆,然后決定給校勘整理者張一兵打個(gè)電話。我對(duì)2006年海天出版社能出版這樣一本書充滿好奇,前幾天已經(jīng)和責(zé)編之一于志斌聯(lián)系上,了解到一些內(nèi)情。欲知更多故事,我還需要和一兵大哥聊聊。

“一兵大哥”這個(gè)稱呼,我是跟著摯友姜威叫的。張一兵和姜威是黑龍江大學(xué)的校友。南下闖深圳的“黑大”畢業(yè)眾同學(xué)相互聯(lián)系很熱絡(luò),顯得異常抱團(tuán),好像離家越遠(yuǎn),同學(xué)這層關(guān)系就越珍貴。姜威酒局的發(fā)動(dòng)原因,幾乎有一半與“黑大”有關(guān),他介紹過很多師兄師弟和我認(rèn)識(shí),初次見面的場(chǎng)合大都是酒桌。酒桌上認(rèn)識(shí)的朋友,姓名容易記不準(zhǔn),要么是一方已經(jīng)喝高,要么是兩人爭酒斗醉,再次見面時(shí)往往還是分不清誰是誰。從頭再來!先罰一杯“加深印象”酒,一杯下肚,感情已經(jīng)深似海,所以喝它個(gè)“一口悶”,再喝一搜“巡洋艦”,然后執(zhí)手相看醉眼,痛心疾首,掏心掏肺,有難同當(dāng),海誓山盟。看起來就要抵達(dá)“從來不需要想起,永遠(yuǎn)也不會(huì)忘記”之境界,誰知換個(gè)日子換個(gè)酒桌再次相遇還是“似曾相識(shí)燕歸來”。黑大之黑,頻頻舉杯,先到者已醉,后來者可追。
身兼東北人與黑大校友,張一兵卻不喝酒,任你山呼海勸,他自巋然不動(dòng)杯,這讓我印象深刻。印象更深刻乃至讓我大吃一驚者,是他出版了一本《深圳古代簡史》。記得那是1997年,姜威把大家招到一起,以慶賀新書出版為名,大喝其酒。我接過張一兵工工整整簽名送我的新書,嘴上沒說,心里有些不以為然:深圳還有古代史?硬編的吧?和洛陽、西安怎么比?那時(shí)候我正在深圳商報(bào)“文化廣場(chǎng)”周刊發(fā)動(dòng)各方高人討論深圳文化。說深圳是“文化沙漠”,我當(dāng)然不同意,但說深圳“歷史悠久”,我那時(shí)也持保留意見。“大俠你不對(duì),”一兵大哥認(rèn)真地說,“你這看法不對(duì)。我原來也不熟悉深圳,我也認(rèn)為深圳沒歷史。我是來了深圳,整這本書,才改變了看法。你看看我這本書就明明白兒白兒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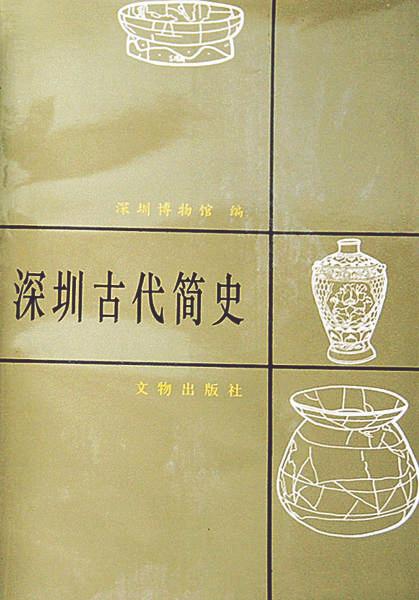
張一兵后來接受媒體采訪時(shí)也常提到,來深圳之前他對(duì)此地改革開放以前的歷史所知甚少,也以為這里不過是個(gè)落后的邊陲小鎮(zhèn),至于古代,一片荒地吧。他來深圳的第一份工作偏偏就是在深圳博物館研究深圳歷史。接觸到原始史料后,他的看法改變了:深圳不僅有歷史,還有十分富有特色的古代歷史,這些歷史是跟當(dāng)時(shí)中國發(fā)生的歷史大事聯(lián)系在一起的。他經(jīng)常說,深圳地區(qū)的繁榮至少可以追溯到漢武帝時(shí)代,那時(shí)候朝廷在各地設(shè)立鹽官,第一個(gè)鹽官就是南海郡的番禺鹽官,漢代的番禺最東面的轄區(qū)就是深圳地區(qū)。至今考古界在現(xiàn)在的番禺都沒有發(fā)現(xiàn)古代鹽場(chǎng),所以古鹽場(chǎng)應(yīng)該分布在深圳、東莞一帶。由此看來,深圳地區(qū)是漢代主要的食鹽產(chǎn)地之一。北宋初期,深圳、東莞地區(qū)的鹽場(chǎng)每年大約產(chǎn)鹽132萬公斤……。
像這類表述,他腦子里裝了太多模版。一旦話題有跡象轉(zhuǎn)向此方向,他馬上滔滔不絕,娓娓道來;然后話題會(huì)開枝散葉,但不管如何跑題,都跑不出深圳史范圍。2月7日晚上我和他通話,因話題所限,我經(jīng)常需要打斷他自己衍生出來的講述。我心里也清楚,如果時(shí)間充裕,聽他古今中外地“滿嘴跑深圳火車”,一定過癮。
他太熟悉深圳的歷史了,建筑、文獻(xiàn)、地名等等,他都熟悉。電話里我們倆開聊不久,他就說到一個(gè)地名,說這個(gè)地名困擾了他很多年了,到現(xiàn)在也沒解開,只有個(gè)猜測(cè)。“這是個(gè)村兒,村名,叫象角塘,就在坂雪崗大道一側(cè)……”
“坂雪崗大道?”我趕緊截?cái)嗨按蟾纾揖妥≡谯嘌彺蟮酪粋?cè)啊,我怎么不知道象角塘?”
“大俠啊!你住坂田啊。”張一兵笑了幾聲,“我也住坂田啊。”
“嗨!”我嘆了口氣,“原來是鄰居啊。那象角塘在哪里?”
他說了一堆村名,用來互相證明各自的方位。我哪里知道這村那村,所以我還是不知道象角塘在哪里。不管了。“這個(gè)村名有什么特別?”我問。
“你想啊,深圳有過大象嗎?我找不到文獻(xiàn)證明深圳有大象生活過。即使有,大象有角嗎?你見過長角的大象嗎?那么,象角塘這個(gè)村名是什么意思呢?”
我茫然。做夢(mèng)我都?jí)舨坏竭@樣的問題。
“我猜啊,”他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自己是在“猜”,“這個(gè)村子原來有一道石崖,東北叫石砬子,深圳這邊叫嶂。這個(gè)村,就在這個(gè)嶂的腳下。現(xiàn)在已經(jīng)見不到這個(gè)嶂了,我猜是采石給采平了。你聽明白了嗎大俠,嶂,象,在白話里是同一個(gè)讀音。以訛傳訛多年,嶂就成了象;而廣東話里角和腳又同音,同音一再訛變,就轉(zhuǎn)不回去了,就成了象角塘了。猜測(cè),我這是猜測(cè)。找不到證明。”
我突然想起,他現(xiàn)在有個(gè)新職務(wù),是深圳地名學(xué)會(huì)的會(huì)長。
【待續(xù)】
胡洪俠/文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802028547號(h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