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克飛/文
在上世紀初到50年代的美國,還有后來的一些新興國家,關于城市建設都有一種論調(diào):“只要我有足夠多的錢,就能把城市建設好”,也就是俗稱的“大氣魄和大手筆”。
它主要依托于西方世界自20世紀以來的一系列空間規(guī)劃和設計方法論,包括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理論、柯布西耶的“光明城市”理論,以及始于19世紀90年代流行于北美各大城市的城市美化運動。這些理論并非一致,柯布西耶對城市功能區(qū)的劃分、對效率的極致追求,就是對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的顛覆。但總體來說,它們有著“大氣魄和大手筆”的共通性。
紐約就是例子,它曾倡導城市郊區(qū)化和建筑現(xiàn)代主義化,著力建造城市地標。它以“攤大餅”的模式擴大城市規(guī)模,然后為了加強區(qū)域間聯(lián)系,開始修建復雜的交通網(wǎng)絡。
擁有巨大隱形權力、主宰紐約城市重建的羅伯特·摩西就滿足了許多人對“魄力”二字的錯誤想象。他沉迷于摩天大樓和高速公路,以“拆拆拆”方式切除所謂的“城市癌變組織”,瘋狂清理貧民窟,消滅無數(shù)街區(qū)。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里,簡·雅各布斯將摩西式的想法乃至霍華德、柯布西耶等人的理論譏諷為“一廂情愿的神話”。認為他們不是從理解城市功能和解決城市問題出發(fā),來規(guī)劃設計一個以人為核心的城市,反而或是以“反城市”的“田園”為目標(如霍華德),或是用假想的烏托邦模式(如柯布西耶),來實現(xiàn)整齊劃一、非人性、標準化、分工明確、功能單一的所謂理想城市,并對違背這一模式的街區(qū)進行殘酷清理。“這不是城市的改建,這是對城市的洗劫。”
城市建設從不是電腦游戲。在《模擬城市》之類的游戲里,玩家可以建造一座夢幻城市,而在現(xiàn)實中,每座城市都必須面對真實的人。簡·雅各布斯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所倡導的,正是城市規(guī)劃背后的人文精神。
1916年,簡·雅各布斯出生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州斯克蘭頓,1952年任《建筑論壇》助理編輯。在負責報道城市重建計劃的過程中,她逐漸對傳統(tǒng)的城市規(guī)劃觀念發(fā)生了懷疑,認為美國大城市正面臨某種災難,并于1961年寫作了《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一書。
在她看來,城市活力來源于多樣性,城市規(guī)劃的目的在于催生和協(xié)調(diào)多種功用來滿足不同人的多樣而復雜的需求。正是那些遠離城市真實生活的城市規(guī)劃理論、烏托邦的城市模式和機械的、單一功能導向的城市改造工程,毀掉了城市的多樣性,扼殺了城市活力。
這本書激怒了當時的美國城市規(guī)劃者們,認為簡·雅各布斯不過是婦人之見。可歷史證明,正是簡·雅各布斯的理念改變了美國的城市建設。
但,城市規(guī)劃是一個“永無終點”的項目,它也受制于太多因素。時至今日,簡·雅各布斯的理想城市仍未真正出現(xiàn),各種新問題卻層出不窮。

《殺死一座城市:縉紳化、不平等與街區(qū)中的戰(zhàn)斗》
[美]彼得·莫斯科維茨 /著
吳比娜 賴彥如 /譯
理想國 |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22年7月
彼得·莫斯科維茨在《殺死一座城市:縉紳化、不平等與街區(qū)中的戰(zhàn)斗》中寫道,縉紳化為城市帶來金錢、新的居民、整建后的房地產(chǎn),但同時也摧毀了城市。它抹殺了簡·雅各布布斯最看重的多樣性,城市因此難以孕育獨特、大膽的文化。
所謂縉紳化,即指房租不斷上漲、連鎖品牌入駐、熟悉的面孔越來越少、在地文化逐漸消失。舊社區(qū)重建后,地價及租金上升,吸引高收入人群遷入,原有的低收入者則不得不遷走,這就導致了縉紳化進程一再深入,也讓城市距離活力和公正越來越遠。
五十年后的西村發(fā)生了什么
簡·雅各布斯與彼得·莫斯科維茨對城市的研究相隔五十年,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研究對象——紐約西村。
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雅各布斯曾探討紐約西村的魅力,以此印證當時主流城市規(guī)劃觀念的錯誤。當時的西村,擁有小而有多樣的街道景觀,多種職業(yè)、階級與種族的居民,多樣的文化,在雜亂中迸發(fā)出強大生命力。
彼得·莫斯科維茨將自己視為雅各布斯書中的角色之一,他在西村長大,“十歲的時候,能夠自己一個人走路到哈德遜街的小學,因為路上的人我都認識,爸媽根本不必擔心。”
但50年后,當莫斯科維茨大學畢業(yè)回到紐約,發(fā)現(xiàn)西村已面目全非,充滿童年回憶的建筑被推倒、重建,取而代之的是聞所未聞的財富象征,天價房租迫使他搬離西村……
莫斯科維茨忍不住提問:“一度昭示著多元平等,成為最佳楷模的西村,如今變成全美最昂貴、紐約族群最單一的社區(qū),這對美國城市的未來意味著什么?而那些被迫離開這個新的西村的人們,他們又怎樣了呢?”

《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
[加拿大]簡·雅各布斯 /著
金衡山 /譯
譯林出版社
2020年7月
于是,便有了致敬《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的《殺死一座城市》。彼得·莫斯科維茨試圖以美國四座大都市——新奧爾良、底特律、舊金山、紐約——為例,逐一分析其城市格局與人口結構的變遷根源所在。政府與財團的共同規(guī)劃,使城市更有利于資本的累積而不利于窮人生存。
對于一般的紐約人來說,西村的變化僅僅是“酷”與“不酷”的區(qū)別,但對于簡·雅各布斯來說,西村這類地方的存在,證明城市可以不需政府干預而自我運轉,無須太多外力幫助就可達到平衡。她認為“小店家、吸引藝術家和作家的便宜租金、長短不一的街廓,以及多用途混合的分區(qū)政策,讓西村的街道成為觀看人來人往的好地方,也讓社區(qū)成為一個親密的系統(tǒng)……多樣性的建筑,從高級華廈到舊出租屋,意味著一群多樣的人可以負擔不同的租金從而入住同一個社區(qū),不會因為收入多寡、族裔背景而被區(qū)隔。”
縉紳化則將這些街區(qū)推向另一個方向:老居民搬走、在地文化消失、財富和白人開始涌入紐約小區(qū)。“對紐約的窮人來說,縉紳化不是一種社區(qū)特質無形的改變,而是他們真切面對的群體驅逐、金權暴力,還有悠久在地文化的鏟除。”
縉紳化是城市的系統(tǒng)暴力
《殺死一座城市》中寫道:“縉紳化不只是一種時尚或潮流。嬉皮士和雅皮士們比起被他們驅離的老居民財力更強,但個別的行動者沒有能力控制房屋市場,憑一己之力改變城市。縉紳化也無法由個別投資者行為來解釋:在新奧爾良擁有五棟房子的房東跟底特律的公寓主并沒有彼此商量策略。縉紳化下有勝利者也有受害者,雙方都在同一場游戲里,盡管他們都不是游戲的設計者。”
換言之,縉紳化并不是個體行為,也不是某個階層的獨立行為,彼得·莫斯科維茨將之視為城市的系統(tǒng)暴力。
1979年,《不平衡發(fā)展——自然、資本和空間的生產(chǎn)》一書的作者尼爾·史密斯提出了對于縉紳化可能最具影響力的學術觀點:租隙理論。他認為過往越缺乏投資的空間,在縉紳化時越能夠獲取利潤。當然,這一點立足于經(jīng)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資本會流向有最高獲利回報、獲利可能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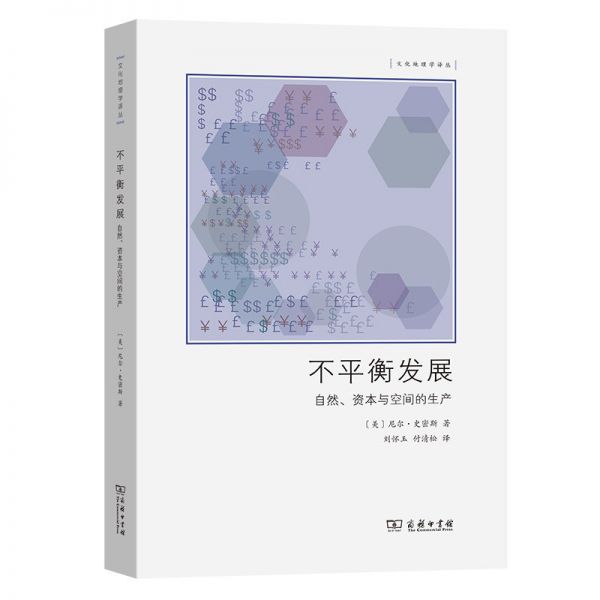
《不平衡發(fā)展:自然、資本和空間的生產(chǎn)》
[美]尼爾·史密斯 /著
劉懷玉 付清松 /譯
商務印書館
2021年5月
對于城市而言,租隙理論和縉紳化的最大后果在于它被變成一個企業(yè)。城市必須要更有“商業(yè)精神”,城市規(guī)劃者要更像“經(jīng)理人”,城市也會像企業(yè)一樣,以“盈利”為第一目標。
在莫斯科維茨看來,這正應了簡·雅各布斯的箴言:“要把一個地方變得單調(diào)、貧瘠、粗鄙,天價資金、機關算盡和公共政策,三者缺一不可。”
縉紳化是每個工業(yè)化國家都會面臨的問題,但嚴重程度不一。在缺乏完善住宅法規(guī)的國家,縉紳化才會造成大規(guī)模的被迫遷移和生存危機,美國就是例子。德國和瑞典等國家的情況好得多,這是因為這些國家意識到完全私人主導的土地市場無法滿足窮人需求,因此采取各種手段,至少將一部分土地保留于市場機制之外,通過法規(guī)限制讓人們能夠負擔其價格。但美國社會顯然無法意識到這一點,“在美國,每年都有1萬戶受補助的租屋單元消失。美國對于窮人的住宅政策,大多數(shù)都是零星而隨機,沒有經(jīng)過縝密的計劃,也從來不是以成長為導向的市政府、州政府的首要目標。”
對于先發(fā)國家來說,城建發(fā)展較早,城市重建的難度也比后發(fā)國家要大得多。因此,天災往往成為縉紳化的契機。
2005年,卡特琳娜颶風給新奧爾良帶來了災難性破壞,之后便是重建。但也正是“重建”,讓這座城市的氣質面目全非。新奧爾良曾是美國最多樣化、最有趣的城市之一,多元文化、語言和各種建筑風格并存,也是黑人爵士樂的發(fā)源地,但重建讓這一切都不幸消失。
重建中的公共輿論是冷酷的。時任州長凱瑟琳·布蘭科說要“用一生的風暴來創(chuàng)造一生的機會。”一位房地產(chǎn)投資者表示“我們不希望暴風雨前的人回到這里。”《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衛(wèi)·布魯克斯在颶風發(fā)生一周后的文章中說:“如果允許人們回來,新奧爾良將再次成為犯罪猖獗的貧窮城市,我們?yōu)槭裁匆试S這種情況發(fā)生?”這些言論與政策制定者的思路是一致的。
颶風后重建的新奧爾良,公共住房項目基本關閉,私人住房取而代之。開發(fā)商重塑了社區(qū)的形貌,使之以白人為主,利潤更為豐厚。如今,這座城市已恢復到卡特里娜颶風前的人口,但黑人居民比風暴前減少了十萬人,千篇一律的連鎖品牌入駐,充滿人情味的多元社區(qū)日漸衰落。如今的新奧爾良,已經(jīng)完全專注于經(jīng)濟增長,不再修復或回顧卡特琳娜帶來的傷痛。
但如果將縉紳化歸結為私人資本的進入,那就非常片面。縉紳化的無處不在,更多是因為一個足以影響政策的角色——政府。過去半個世紀,聯(lián)邦政府一再削減社會住宅、社會福利、公共交通的預算,城市只能自力更生,依靠自身稅收去承擔基礎服務。這使得城市政府只能鼓勵商業(yè)和產(chǎn)業(yè)發(fā)展,吸引高收入或中高收入的家庭移入城市。也就是說,城市必須要盡全力吸納那些有錢和中上階級的居民,以這部分群體的稅金和購買力為倚仗,解決財務缺口。
對于大多數(shù)美國城市,乃至世界上的許多城市來說,發(fā)展中的問題解決起來都復雜而困難,縉紳化卻是一個簡單直接輕松的選擇。紐約前市長邁克爾·布隆伯格就曾提出:“如果我們能再讓幾個億萬富翁住在紐約,我們的許多問題都會得到解決。”但這也是飲鴆止渴的做法。
簡·雅各布斯構想的城市能否重現(xiàn)
簡·雅各布斯對城市和街區(qū)的構想,或許確實有不合時宜的一面,但仍然是許多人所憧憬的。
她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寫道,老城市和老街區(qū)雖然看起來缺乏秩序,但實際上背后卻有神奇的秩序在維持著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同時,它也會帶來真正的多樣性和差異性,真正體現(xiàn)城市文明,“讓互不相識的人能夠在文明的、帶有基本的尊嚴和保持本色的基礎上平安地相處。”
城市建設就像一個巨大的實驗室,難免會有錯誤與失敗,但也提供了學習的契機。可惜的是,城市建設的實踐者們卻往往忽視了那些失敗,僅僅遵循于一些表象原則和大而化之的概念。
縉紳化的受害者并不僅僅是貧民,當一個階層被驅趕,意味著會有另一個階層變成新的城市底層。“如果城市是一架梯子,縉紳化把每個人都往下推了一級,最弱勢的人被徹底地推下去,中產(chǎn)階級則落到底層,甚至有錢人也會感受到來自上層的壓力。”
“只有那些完全不依賴政府服務的人——那些有私人交通工具、負擔得起私立學校學費、有足夠資金購買房產(chǎn)或承受租金漲幅的人,才能漂浮在縉紳化掀起的海浪之上。”更糟糕的是,即使是這部分“幸存者”,也必須面對縉紳化導致的無聊城市。
彼得·莫斯科維茨在《殺死一座城市》中給出了幾種解決方案:“借由政府擁有土地興建公共住宅,或立法采取嚴格的管制,控制租金或土地價格上揚,或是我們可以通過住宅補貼這類政策,防止攀升的土地價格致使人民迫遷。”
不過在目前情況下,人們似乎只能期盼市場力量能自行解決問題。若沒有重大法規(guī)革新,那么在可見的未來,城市的中心將越來越具吸引力,窮人將被流放到郊區(qū),直到城市與郊區(qū)的租隙降低,縉紳化無利可圖,才會又開始新一波的空間重組。
將一切交給時間,或許是無奈又可行的方法。就如雅各布斯所說:“單調(diào)且缺乏活力的城市只能是孕育自我毀滅的種子。但是,充滿活力,多樣化和用途集中的城市孕育的則是自我再生的種子,即使有些問題和需求超出了城市的限度,它們也有足夠的力量延續(xù)這種再生能力并最終解決那些問題和需求。”
但愿如此。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80202854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