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片來源:圖蟲創(chuàng)意)
陶力行/文
雖然中原農耕政權被外族侵占的情況不少,如拓跋鮮卑立國北魏、女真滿族立國大清等,但這些入侵者多位居中原東北部的草原、平原與森林的混合地,且其入侵都發(fā)生于中原統(tǒng)一政權臨危、松動或崩潰之時。就中原北部的草原游牧政權而言,他們鮮有入駐中原,雖然攻擊中原是一種常態(tài)。從千年尺度看,草原游牧政權與中原農耕政權之間大致保持平衡。而且,兩者還時常呈現出周期性共振。然而,歷史總有意外。蒙古的橫空出世破壞了游牧與定居之間的“平衡律”與“共振律”,其不僅將整個中原政權吞并,還建立起了前現代幅員最為遼闊的帝國。放在草原政治框架下,蒙古是一個特例。
Barfield在《危險的邊疆》一書中做出了解釋,其觀點可作如下概括:草原政權的基本單位是以血親為基礎的部落,由于血親的先天性和不可跨越性,由部落組成的草原帝國多是行動能力有限、結構松散的聯盟性帝國,但成吉思汗打破了血親原則,其通過“重族伴輕家族”的做法建立了一支擴張性更強、效率更高的軍事力量,其繼承者又利用這一力量締造出了橫跨整個內亞的蒙元帝國。
Barfield得出結論的方式并非基于蒙古內部視角的歷史回溯,而是跨時空的歷史比較。他將上述觀點嵌入在以下兩個觀點之中:(1)草原游牧政權與中原政權是共存的,組織形式是共振的,即要么同時“合”,要么同時“分”;(2)蒙古是草原政治的偏離,一旦蒙元帝國垮臺,草原政治與中原政治又會恢復至共存。
為論證上述內容,《危險的邊疆》將考察尺度拓寬至兩千年,依時間序列分析了不同的游牧政權與中原政權——包括匈奴與漢、突厥與隋、回鶻與唐、瓦剌和韃靼與明等——的互動過程,并對草原游牧帝國與中原帝國之間的共存性、蒙古的崛起、草原政治的最終沒落、外族占領中原等現象做出了描述和解釋。雖然該作體量龐大,涉及政權對象甚多,但仔細閱讀可發(fā)現,作者的核心落腳點是蒙古。
一
《危險的邊疆》初版于1989年,在當時語境下,該作有多處創(chuàng)新,可歸結為四點。第一,將考察視野延伸至游牧內部,平衡了過往研究中過強的“中原中心主義”。雖然游牧政權在軍事方面很強大,但在經濟與文化方面均不如中原政權,因為經濟與文化是累積性發(fā)展的產物,而游牧的流動性不利于累積。其結果是,根據材料說事的后世研究者會不期然地將中原立場作為敘事起點。
Barfield結合不同學科的理論成果將碎片化的游牧信息整合,提供了對沖中原視角的敘事。例如,他指出,在中原政權看來,所有游牧政權都是虎視眈眈的侵略者,但在游牧政權眼里,中原農耕政權只是一個合適的敲詐對象而非征服對象。Barfield認為,征服意味著管理,而對游牧政權而言,管理農耕政權是件吃力不討好之事,與其殺雞取卵地征服,不如百試不爽地敲詐。
第二,用共存觀或相互依賴觀代替對立觀。傳統(tǒng)觀點從對立角度解讀游牧政權和中原政權的關系,但Barfield從戰(zhàn)略角度否認了這一說法。他指出,游牧部落因為講究血親原則,相互之間通常會有較強的排他性,即便組成帝國聯盟,各自依然會保留較強的自主性,這意味游牧政權雖然在軍事實力方面勝于農耕政權,但不會將后者樹立成“永恒的敵人”,因為游牧社會的內部張力會使任何一個游牧部落都有陷入兩線作戰(zhàn)的可能。
為說明兩者的共存性,Barfield在解析游牧的國際政治戰(zhàn)略時,區(qū)分了針對中原的“外部邊界戰(zhàn)略”以及針對草原的“內部邊界戰(zhàn)略”,并指出兩種戰(zhàn)略相互聯動。例如,當游牧政權聯盟成草原帝國時,帝國首領會敲詐中原政權以獲取維系草原聯盟的資源;當草原內戰(zhàn)興起時,各游牧政權又會嘗試與中原政權結盟,以求重建草原聯盟或制衡其他游牧政權。Barfield的意思是,“游牧帝國聯盟只有能將自身與中原經濟相聯系時方能存在”。
第三,用三分法代替二分法,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新的歷史想象。傳統(tǒng)研究采用二分法,即將內亞國際關系敘述成游牧政權與農耕政權的拉鋸。對中原政權來說,如此敘述合情合理,因為中原政權眼里的所有北方外族均是同質的“蠻夷”,但引入地理分析后會發(fā)現,外族內部其實也有差異,有些外族能夠入駐中原,有些外族卻只能止步于中原之外,且所有成功入駐中原的外族,除蒙古以外,均發(fā)軔于中原東北部。二分法無法解釋這一差異。
Barfield重新區(qū)分了內亞政權類型,即位于中原地區(qū)的漢人政權、位于草原地區(qū)的游牧政權以及位于中原東北部地區(qū)的混合態(tài)政權,并在此基礎上概括出了內亞國際關系的循環(huán)論以及蒙古例外論。所謂循環(huán)論,是指“中原農耕帝國和草原游牧帝國幾乎同興同衰,以及衰落之后,位于中原東北部的半游牧政權會立馬乘虛而入進駐中原”的過程在兩千年內亞歷史中重復出現過三次。所謂的蒙古例外論,是指蒙古作為草原部落成功入駐中原,打破了外族入駐中原的東北慣例。
第四,行動者視角與結構視角相結合。結構論者通常假定歷史結果是特定條件匯聚的結晶,敘事上采取還原論。例如,Lattimore注重文化條件,在解釋草原游牧社會與中原政權的不兼容時,提供的說法是草原游牧社會沒有“文化英雄”;在解釋蒙元政府為什么可以部分架空文人官僚時,說是蒙古吸收了喇嘛教文化,找到了替代品。但在Barfield看來,這些說法由于缺乏視野比較顯得很不可靠。
結構會對個體起作用,但不會對所有個體起相同作用,一旦某一結構下的個體呈現出明顯的差異性分布時,結構論就會立馬捉襟見肘。蒙古原本只是一個小部落,而且是草原諸多部落之一,但從十二世紀下開始不斷壯大,不斷吞并其他部落。從Barfield的眼光看,蒙古與草原其他部落的外部條件極為相似,如果只關注結構而不關注行動者,即成吉思汗本人的能動性,那就無法理解蒙古與其他部落的分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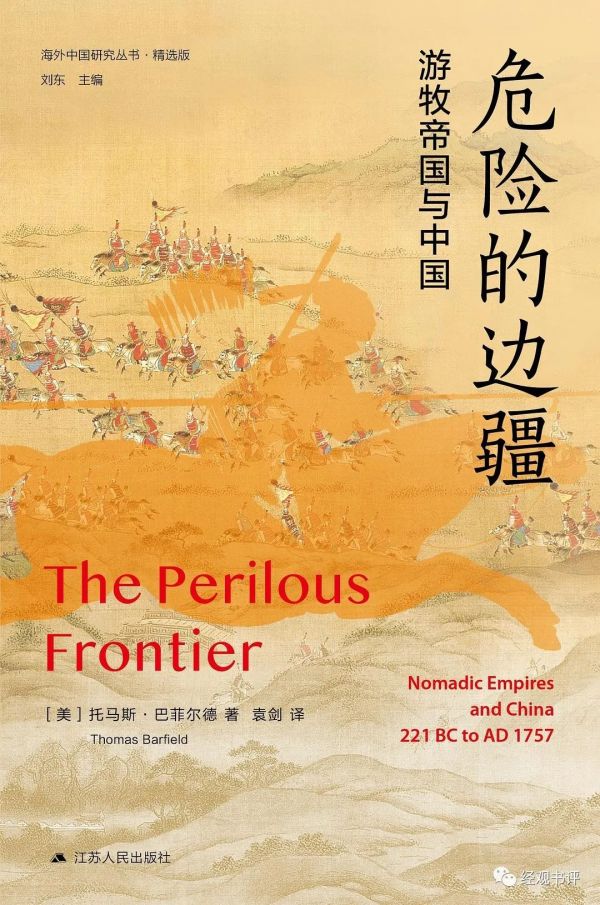
《危險的邊疆:游牧帝國與中國》
[美]托馬斯·巴菲爾德(Thomas Barfield)/著
袁劍 /譯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23年4月
二
就上述四點而言,《危險的邊疆》算得上是一部具備宏大視野且有理論指向的創(chuàng)新之作。但是,這不意味著該作沒有改進空間。接下來,我將批判性地分析一下該作。
第一,“把游牧政權的攻擊行為定性為敲詐而非征服”就存在問題,因為這是一種基于動機論的解讀。研究者可以觀測行為、猜測動機并根據猜測推理行為,但不能言說動機,原因有三:一、動機只是行動者證成行為的心理宣稱,但所有心理宣稱都不可考察;二、心理宣稱和行為并不一一對應,一個動機可產生多種行為,不同動機也可促成同一行為;三、動機總是在變動,行動從啟動至完成,行動者可以不斷嵌入新的動機,以至于動機性表述即便由行動者本人坦白也會顯得不那么可靠。
一個行為最初可能是為了敲詐,但如果攻擊行為能夠獲得持續(xù)的正向反饋,那目的就有可能升級為征服。同樣可能的是,一個行為最初是為征服,但久攻不下后,目的被降級至敲詐。這里值得討論的并非如何定性攻擊行為,而是如何描述及解釋攻擊行為的發(fā)生頻率、發(fā)生方式和強度。如果游牧的攻擊行為多止步于既定邊界,那旁觀者似乎只能假定:游牧政權對于中原政權而言沒有軍事優(yōu)勢,即所謂的平衡律及共振律,只是兩者軍事實力相當的表征。
然而,Barfield沒有對兩者軍事實力的對等做出解釋。這種不解釋不是Barfield獨有的問題,而是大多數學者共有的誤區(qū),因為他們忽視了中原政權相對于游牧政權的優(yōu)勢,只用“視覺直觀”做出判斷。關于農耕政權的軍事優(yōu)勢,可參考趙鼎新《儒法國家》中的說明,即“相較于貧瘠的草原,農耕區(qū)的土地有更強的生態(tài)承載能力,這就使農耕者有發(fā)展打敗對方的軍事實力和有可能吸收同化對方的人口優(yōu)勢”。反之,游牧政權因為沒有強大的物資儲備能力,缺乏打持久戰(zhàn)的能力,所以多有敲詐,鮮有征服。
第二,歷史循環(huán)論是一種忽略細節(jié)的粗暴歸納,而非規(guī)范性表述。循環(huán)論的語法只適用于“剛體”行為的表述,如太陽繞著地球轉,鐘擺現象等。放在歷史學不合適——無論是國家還是組織,都是有機體而非剛體。
相對于人的目光而言,剛體高度穩(wěn)定,而有機體總是在變動。如果歷史學研究者想引入循環(huán)論語法,就必須將非剛體說成是剛體,帶來的結果就是簡化甚至取消歷史細節(jié)。Barfield在敘事游牧帝國與中原帝國的共時性時就以忽視歷史細節(jié)為代價。他之所以會歸納出共振現象,是以漠視“不同政權以不同原因建立或以不同原因潰敗”這一事實為代價的。
第三,錯誤的解讀夸大了中原政權對于草原帝國穩(wěn)定的意義。Barfield認為,游牧帝國之所以會敲詐中原但鮮有征服中原,是因為不征服可以令其持續(xù)性地從中原那里獲取維系帝國完整性的資源。這一觀點是從功能主義角度解讀敲詐,并不可信,因為游牧帝國的形成總是發(fā)生于敲詐得手之前,研究者無法從時間序列上判定兩者間存在因果關系。
其實,草原帝國一旦形成,即便沒有敲詐也未必會有帝國的崩潰。如Barfield自己所言,游牧帝國從中原帝國那里獲取的物資通常只會被分配于帝國下的各部落精英。對于這些精英而言,獲得分配是一種因接受聯盟而獲得的附加性獎勵,但這些精英之所以愿意接受聯盟,是因為聯盟可以令其免于中原帝國給予的恐懼。在歷史過程中,附加性獎勵的意義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免于恐懼的意義是不確定的,也是難以測量的。
第四,認為“血親原則是游牧部落的專屬”以及“蒙古削弱血親話語是成吉思汗個人意志的表達”存在問題。血親原則是篩選個體的話語標準,由于血親的先天性和不可超越性,血親話語本身就意味著封閉性,即一個群體流動性越弱、同質性越高,其越會講究血親話語。但是,封閉性并非游牧社會的獨有特征,而是所有小規(guī)模社會的共性,農耕社會規(guī)模小的時候也會講究血親,例如農耕社會的長子或嫡子繼承制。
這里值得討論的是:在何種情況下,血親話語在統(tǒng)治階級內部會被削弱?如果用歷史的眼光看,當群體規(guī)模在短時期內因戰(zhàn)爭吞并或商業(yè)流動迅速擴大后,血親話語逐漸削弱是一種常態(tài)性現象,就這點而言,成吉思汗削弱血親話語本身,就是由其領導的部落不斷擴張的附隨物。
第五,夸大了成吉思汗的個人作用,將蒙古軍隊的組織性、效率以及戰(zhàn)斗力解釋為“成吉思汗因為在乎族伴而擁有更多的追隨者”的結果存在問題。追隨者之所以會持續(xù)追隨某條路徑,是因為這條路徑能帶來正向反饋,追隨者一旦獲取不了正向反饋,就會隨之離去。因此,要說明蒙古軍隊的高戰(zhàn)斗力需要提供更宏觀的結構性理由。
其實,中原東北部的政權之所以比草原政權更容易入駐中原,是因為東北部是草原、平原以及森林的混合態(tài),其多樣的生產模式賦予了東北部政權比草原游牧政權更多的行動彈性。就這點而言,蒙古只需不斷擴大自己的行動彈性,其入駐中原的概率就會提高。回溯歷史可發(fā)現,蒙古的擴張確實是一個不斷收編農業(yè)經濟,不斷擴展自身補給能力,不斷擺脫草原性,不斷積累與農耕政權作戰(zhàn)經驗的過程。
Barfield雖然是一名人類學家,但在寫作時不斷引入比較視野,所以讀起來會有社會學之感。引入比較視野的好處在于能夠有效屏蔽作者自身的價值偏好、快速剔除大量干擾因素、準確抓取關鍵變量,但其難度在于如何選取合適的事實進行比較以及如何準確地解讀這些事實。如果這兩個問題沒有解決好,依舊會給對方辯友打開詰問的后門。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854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