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節(jié)期間,張藝謀新作《第二十條》在各大影院熱映。該片片名取自刑法“第二十條”,講述的是關(guān)于“正當(dāng)防衛(wèi)”法條背后的公理人情。其實在現(xiàn)實中,總是會有這樣那樣吵不完的法律熱點爭議。中國政法大學(xué)刑法學(xué)研究所所長、“法考男神”羅翔的《法律的悖論》一書,通過分析法律中經(jīng)典的案件,辨析了法律中的盲區(qū),揭示了法治的核心,并引導(dǎo)讀者探討和思考法律中的悖論。書中可以讀到的,不僅是法律知識之繁雜,更有批判性思維和接納多元觀點之重要。

《法律的悖論》
羅翔 著
果麥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
法律與道德
司法實踐中,如何正確適用正當(dāng)防衛(wèi),尤其是一些出現(xiàn)傷害結(jié)果的案件,如何正確區(qū)分正當(dāng)防衛(wèi)、防衛(wèi)過當(dāng)、互毆、傷害的界限,對于很多檢察官而言都是一個難題。其中一個難點就在于,如何準(zhǔn)確認(rèn)定行為人是否具有防衛(wèi)意圖。
影片《第二十條》中,韓明為了說服張貴生放棄上訪,拿出案發(fā)時的視頻錄像一幀幀進行分析解讀,認(rèn)定張貴生與“咸豬手”的打斗從最初的正當(dāng)防衛(wèi),轉(zhuǎn)化為互毆,甚至是故意傷害。此時的韓明,站在事后的角度,以理性冷靜局外人的視角,圍繞暴力升級的時間點,將整體案件割裂進行分析。雖然他參考了很多既往判例,對案件的分析和處理好像也符合法條規(guī)定,但卻沒有做好對法、理、情的兼顧。
冰冷的法律邏輯,需要考慮人類的情感嗎?需要,又不需要。這是一個悖論性的回答。從公認(rèn)的前提推導(dǎo)出兩個互相矛盾的命題,就是悖論。悖論包括真悖論和假悖論。假悖論就是所謂的“似是而非”,看似合理但其實不合理;真悖論則是“似非而是”,看似荒謬的結(jié)果卻被證明是真實的。
羅翔認(rèn)為,悖論的出現(xiàn),提醒我們:人類是有限的,理性是有瑕疵的,也許我們永遠無法把握對世界整體性的全局認(rèn)識,無法完全開啟上帝視野。這就像盲人摸象,每個人都認(rèn)為自己摸到了大象的全部,但其實不過是摸到了大象的部分。
法律與道德、理性與感性,是一場古老的爭論。中國古代有儒法之爭,主要涉及的正是法律與道德的沖突。儒家認(rèn)為道德是可以影響法律的,但是法家認(rèn)為道德絕對不能干涉法律,法不容情。
法家強調(diào)“刑名”,所謂律法與名實相符,大致相當(dāng)于后世的演繹邏輯,大前提小前提結(jié)論。比如西漢的法律規(guī)定,毆傷父親者梟首。結(jié)果張三的父親與他人斗毆,張三用木棍去打他人,不料卻誤傷其父。按照法家的觀點,那就應(yīng)該嚴(yán)格按照法律規(guī)定,判處張三死刑。但是按照儒家的觀念,法律不應(yīng)該那么機械,要考慮背后的情理。西漢大儒董仲舒就提倡“《春秋》決獄”,也就是用儒家的道理來軟化機械的法律。如果犯罪者的動機是好的,就可以從寬甚至免罪,所謂“君子原心”,論心不論跡。
“張三傷父案”是西漢武帝時的一個真實案件,廷尉張湯請教董仲舒應(yīng)該如何處理。董仲舒舉了《春秋》的一個典故,來說明張三沒有主觀上的故意。春秋時期的許悼公生病,太子許止給父親送藥,結(jié)果父親一命嗚呼。太子很傷心,覺得自己有錯,把國君之位讓給弟弟,自己郁郁寡歡而死。《春秋》經(jīng)文說“許世子弒其君”,但《春秋公羊傳》認(rèn)為,許止的動機是好的,不算為罪。董仲舒以此典故主張張三不構(gòu)成犯罪,張湯聽取了董仲舒的意見。
在羅翔看來,不講道德的法律,只把民眾當(dāng)作威嚇的對象,這樣法律將淪為純粹的工具,民眾喪失人格和尊嚴(yán),法律人遲早也會成為刀筆吏,甚至成為酷吏。但只講道德的法律,也很虛弱無力,太過理想而不現(xiàn)實。所以,后世的封建統(tǒng)治者采取儒法合流,內(nèi)法外儒,用儒家的理想主義來約束法家殘酷的現(xiàn)實主義。
犯罪之惡
《第二十條》的故事啟示我們,必須準(zhǔn)確把握正當(dāng)防衛(wèi)制度的立法本意,不能站在事后的角度,去分析和判斷防衛(wèi)人的行為動機和主觀目的,不能割裂案發(fā)原因和自然演進過程,將整體案件切片看待,也不能簡單以防衛(wèi)行為造成的后果重于不法侵害造成的后果,就排除防衛(wèi)人具有防衛(wèi)意圖,而應(yīng)當(dāng)把自己代入現(xiàn)場、代入當(dāng)事人的角色,綜合案件起因、案發(fā)具體環(huán)境、矛盾激化過程、雙方力量差異、行為人一貫表現(xiàn)等方面,作出客觀全面、符合常情常理的判斷。
在刑法中,這樣需要綜合考慮的情況比比皆是。
2021年,一名高校女生因為罹患抑郁癥,從海外購買精神類藥品。她如實填寫了收件地址,被輕松抓獲,后被控走私毒品罪。通過這起案件,大家才知道麻醉藥品、精神類藥品既是藥品,又是毒品。刑法第347條規(guī)定:“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無論數(shù)量多少,都應(yīng)當(dāng)追究刑事責(zé)任,予以刑事處罰。”法院考慮到此案情有可原,而且被告身患重度抑郁,經(jīng)鑒定為限制刑事責(zé)任能力人,最后對其判處了緩刑。雖是緩刑,女生也被貼上了犯罪的標(biāo)簽,她的人生軌跡被改變了。
這涉及犯罪本質(zhì)的爭論。犯罪是一種惡,這種惡是因為“它是犯罪所以邪惡”,還是因為“邪惡所以成為犯罪”呢?隨意虐殺他人,自然是一種邪惡的行為,所以刑法將其規(guī)定為犯罪。但是抓幾只鸚鵡,在刑法中也可能是犯罪,這也是因為行為本身邪惡嗎?
《法律的悖論》指出,早在古羅馬就有自體惡和禁止惡的爭論,自體惡是指某種行為的惡是與生俱來,該行為本身自帶的。禁止惡則是指某種行為因為法律的禁止所以成了惡,惡并非行為本身所具有的。“因為邪惡所以犯罪,還是因為犯罪所以邪惡。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視角,它既是邏輯問題,又是現(xiàn)實問題。但無論如何它都不是書齋中的空談。”
“從形式上來看,這符合走私毒品罪的構(gòu)成要件。麻醉藥品、精神類藥品既是藥品也是毒品,但只有當(dāng)毒品具有一定的擴散性,才可能危及不特定多數(shù)人的身體健康。即便將此罪侵犯的法益歸結(jié)于毒品管理秩序,那也應(yīng)該還原為對公眾健康的威脅。”因此,羅翔認(rèn)為,以治病為目的購買精神藥品不應(yīng)該以犯罪論處。2023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毒品案件審判工作會議紀(jì)要》終于規(guī)定:“因治療疾病需要,在自用、合理數(shù)量范圍內(nèi)攜帶、寄遞國家規(guī)定管制的、具有醫(yī)療等合法用途的麻醉藥品、精神藥品進出境的,不構(gòu)成犯罪。”
無數(shù)個案推動了法治的前進,但起到推動力量的每個個體,卻不得不承受百分百的痛苦。《法律的悖論》認(rèn)為,犯罪是一種惡,這種惡不僅因為它是刑法所規(guī)定的犯罪,被貼上了犯罪的標(biāo)簽就成為一種惡,更為重要的是因其內(nèi)在的道義上的可譴責(zé)性而成了一種惡。缺少二者中任何一種的惡,都不是犯罪。
穩(wěn)定與靈活
現(xiàn)實中,法的穩(wěn)定性與靈活性,始終存在一定的張力。如何既尊重立法權(quán)威,又進行合理的司法修補,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
法律并不等于真理。無論哪個國家和地區(qū),立法錯誤其實都比比皆見。美國阿肯色州曾出現(xiàn)一個明顯的立法錯誤——嬰兒獲得父母同意也可以結(jié)婚,讓人大跌眼鏡。法條表述如下:“年齡在18歲以下,并且沒有懷孕的人如果要領(lǐng)取結(jié)婚證明,必須出示父母同意的證明。”后來發(fā)現(xiàn)這一烏龍是誤寫了“沒有”兩字。
羅翔認(rèn)為,法律肯定是需要解釋的,立法者把一些經(jīng)常發(fā)生的行為用語言進行規(guī)定本來就很困難,用條文來窮盡它所應(yīng)涵蓋的所有情節(jié),無異于一種過于理想的刑法烏托邦。加上社會生活的不斷變化,立法時不能預(yù)見的事情發(fā)生是自然而然的。
從罪刑法定原則出發(fā),司法機關(guān)不能創(chuàng)造新的法律,不能進行不利于行為人的類推解釋,但卻允許擴張解釋。一般認(rèn)為,盡管擴張解釋與類推解釋之間,很難劃出一個涇渭分明的“楚河漢界”,但兩者還是有很大區(qū)別的。擴張解釋是將刑法規(guī)范可能蘊含的最大含義揭示出來,是在一定限度內(nèi)的解釋極限化;類推解釋是將刑法規(guī)范本身沒有包含的內(nèi)容解釋進去,是解釋的過限化。在民事領(lǐng)域,允許法官探究法律精神,類推定案。但在刑事領(lǐng)域,不允許法官做對行為人不利的類推解釋,因為刑罰指涉的是公民的自由、生命、財產(chǎn)等最基本的價值,如被濫用,后果不堪設(shè)想。在某種意義上,少打擊一些過分行為,總比濫施刑罰要強得多。
清末修訂的《大清新刑律》草稿補箋,就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如果法律規(guī)定道路禁止牛馬通過,那么舉輕以明重,自然也禁止駱駝和大象通過;池塘禁止垂釣,自然也禁止撒網(wǎng)捕魚。但是,這種自然解釋其實已經(jīng)超越語言的限制了。牛馬包括駱駝嗎?垂釣包括撒網(wǎng)嗎?
羅翔覺得,無論如何,司法不能突破語言極限創(chuàng)造對行為人不利的規(guī)則。醉酒駕駛機動車構(gòu)成危險駕駛罪,但如果毒駕呢?是不是更應(yīng)該構(gòu)成危險駕駛罪,如果這樣的話,那醉酒開飛機是不是也可以解釋為醉駕呢?原則一旦突破,后果不堪設(shè)想。所以羅翔說,對于入罪的當(dāng)然解釋,必須要卡兩個標(biāo)準(zhǔn):一個是實質(zhì)標(biāo)準(zhǔn),舉輕以明重,另一個則是形式標(biāo)準(zhǔn),不能超過語言極限。
公元1142年,在南宋臨安大理寺獄中,岳飛被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毒殺。岳飛之死讓大家知道了什么叫“莫須有”:也許有。幾百年后,崇禎皇帝以“通虜謀叛”罪名逮捕了袁崇煥并將其凌遲,京城不明真相的百姓們竟然恨袁崇煥入骨,行刑之日,紛紛出錢買袁崇煥身上割下的肉吃,還罵袁崇煥是個“叛徒”。可事實真的如此嗎?恐怕未必,否則就不會再有對這兩位英雄翻案之事了。
刑名關(guān)乎性命,自當(dāng)慎之又慎,保持謙卑和敬畏。在羅翔看來,人們像螞蟻一樣,生活在有限的世界,但在我們的視野以外,還有更多、更美、更神奇的存在。法律追求公平與正義,雖然公義眼不能見,但這并不意味著它不存在。“很多人認(rèn)為法律人是理性的,感性是職業(yè)大忌。但哲學(xué)家阿奎那提醒我們:凡是在理智中的,無不先在感性之中。”
【相關(guān)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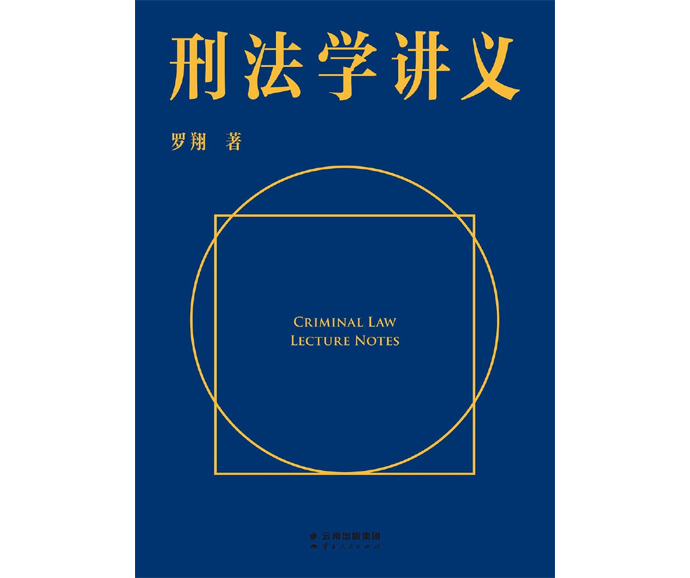
《刑法學(xué)講義》
羅翔 著
果麥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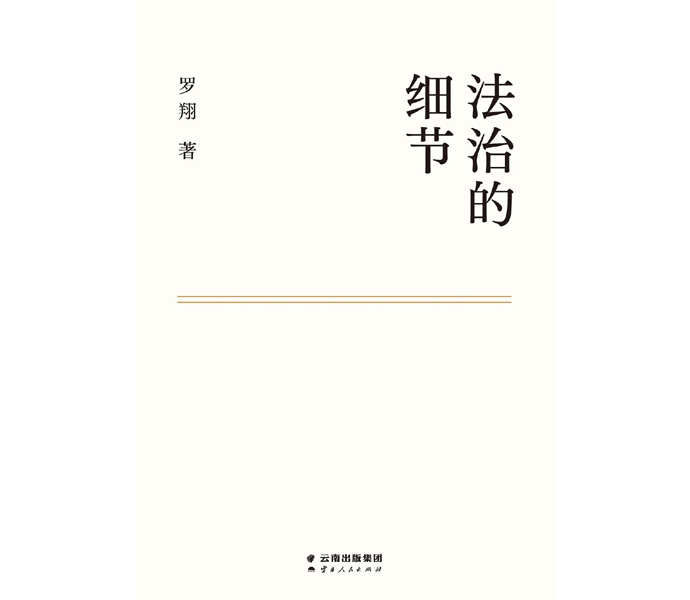
《法治的細節(jié)》
羅翔 著
果麥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
文章來源:齊魯晚報
作者:季東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802028547號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80202854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