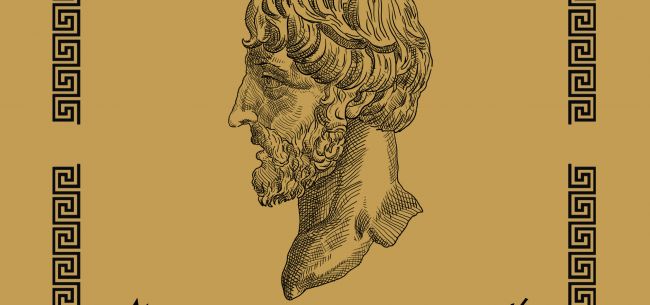
傅北宸/文 公元166年,在世界史上是別有興味的一年。
《后漢書》卷八十八的《西域傳》,有這樣的一條記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
這里的“大秦”是指的古羅馬,自此,處于歐亞大陸的東西端的兩個彼此稱呼對方為“大秦”(古羅馬稱中國為Sinoa,即“秦”)、但并未自稱“大秦”的國家有了第一次外交接觸。這兩個國家彼此以自身的世界觀忖度著對方,雖然一條蜿蜒在它們之間的、橫跨數個文明帶和氣候帶的“絲綢之路”將它們間接連接起來,但它們從未有過事實上的直接接觸,而相互靠近的緣由卻差不多。中國溝通羅馬,想與之聯(lián)手夾擊匈奴,定遠侯班超曾于永元九年(公元97年),遣甘英使大秦,但甘英大概只是“抵條支”(李白詩《戰(zhàn)城南·去年戰(zhàn)桑干源》中說的“洗兵條支海上波”即是指此),到達了波斯灣以西一帶的帕提亞(即史籍中之“安息”),并沒有真到羅馬城。巧得是,羅馬也有聯(lián)合賽里斯(因絲綢,亦稱中國為賽里斯(Serice——絲、絲綢的意思)共同夾擊帕提亞的企圖。而這些大戰(zhàn)略小心思都在羅馬的努力下通過海道從越南在166年天雷勾地火,出現(xiàn)了一道曙光。
無論如何,這是絲綢之路首尾端的兩大巨擘第一次接榫,更重要的,這同時也是羅馬至少兩代皇帝的心照。事實上,羅馬的安敦尼王朝始終沒有放棄溝通中國的努力。
《后漢書·西域傳》中的“安敦”是安東尼(和安敦及安敦尼為同一詞源,只是譯字不一。以下同)的譯音。羅馬歷史上,習慣將安東尼·庇護和他的養(yǎng)子兼繼承人馬可·奧勒留·安東尼一起,并稱“兩安東尼”——這種稱呼源于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兩朝安東尼的統(tǒng)治,也許是人類歷史上惟一一段以一個偉大民族的幸福安寧作為執(zhí)政核心的時期。”《后漢書》上記載的這個年份,正值馬可·奧勒留在位,所以這個“大秦王安敦”是誰,不言自明。
一
2007年11月20日,在新加坡,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在會見中資機構的代表時提到,他前一天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演講之后,一個新加坡孔學會的人問及孔子思想,溫總理說,“環(huán)顧歷史,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都到哪里去了?他們像一股青煙消失了。”——這是羅馬帝國馬可·奧勒留在他的一本書里的一句話,這本書叫《沉思錄》。
溫家寶表示,他把這本書放在床頭,可能讀了有100遍,天天都在看。這直接導致了《沉思錄》成為2008年度暢銷書榜第一名,而《沉思錄》在1988年引進中國,迄彼出現(xiàn)了至少27個譯本,2009年3月4日《沈陽晚報》記者蓋云飛報道稱,單是2008年,就出現(xiàn)了18個新譯本。譯本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是最早的1958年梁實秋譯本,一是北大何懷宏譯本。前者開山漢譯,后者一稿十投,都有一段軼事。
馬可·奧勒留在位的第5年是45歲,按現(xiàn)在的平均壽命而言他正值春秋鼎盛,這一年就是公元166年,他在這一年達成了養(yǎng)父安敦尼的政治遺愿——聯(lián)通了中國。中國和羅馬的史書都沒有記載這次聯(lián)通的結果,當時在位的皇帝是漢桓帝,是后來讓諸葛亮“未嘗不嘆息痛恨”的敗家子之一,除了大基數上的負能量和沒出息,166年的黨錮之禍,已經把他弄得惱羞成怒且心煩意亂。
奧勒留所在的歷史時期命名為“安敦尼王朝”,這個時期的羅馬帝國有6位皇帝,按次序分別是涅爾瓦、圖拉真、哈德良、安敦尼、馬可·奧勒留和康茂德。之所以如此稱謂是因為其時的羅馬統(tǒng)治者一般都認為,安敦尼的統(tǒng)治時期是羅馬帝國最發(fā)達最繁榮的時代,并認為元首本人就是最理想君主的摹本,并把王朝中康茂德之前的五任皇帝評價為“五賢帝”,奧勒留是五賢帝的最后一位。
屋大維統(tǒng)治晚期,政治遺囑建議羅馬的疆域不再擴張,此后直到羅馬分裂,其疆域一直保有著橫跨歐亞非三個大陸的龐大體量。極度不發(fā)達的交通、極度遼闊的幅員和繁星滿天的種族信仰所伴生的運轉不靈兼供血不足,直接導致了巨人癥帝國的統(tǒng)治矛盾叢生蔓長且無處不在。以奧勒留為例,如果形容他的統(tǒng)治期,最接地氣的莫過于中國詩人王勃的16字咒“時運不濟、命運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
奧勒留于162年繼位成為羅馬帝國皇帝。在前一年,帕提亞的沃洛吉斯四世(Vologases IV)繼位,開始入侵亞美尼亞和敘利亞,重奪埃德薩,奧勒留的養(yǎng)父安敦尼在憂憤中去世,奧勒留“奉命于危難之間”,接過了充滿了硝煙的權杖,而這場戰(zhàn)爭一直打到奧勒留特使抵達中國洛陽的那一年——羅馬有心東來,中國卻無暇西顧。
奧勒留的羅馬處境遠不止于此,在北方邊境,馬科曼尼人、夸狄人、薩馬坦人、愷悌人和扎則基斯人等日耳曼部族都相繼發(fā)動叛亂。巧合的還是公元166年——叛亂的先頭部隊一度沖進北部意大利。奧勒留當局被迫開啟了全民皆兵模式,把奴隸和角斗士都編入軍隊。終奧勒留一生,這身撲火隊長的行頭一直沒能脫下。180年3月17日,他死在了征討馬科曼尼人的多瑙河邊的Pannonia省(現(xiàn)威尼斯),只是他并非戰(zhàn)死而是死于瘟疫,而這場瘟疫也是奧勒留繼位初期的種因。

沉思錄
[古羅馬]瑪克斯•奧勒留 / 著
梁實秋 / 譯
譯林出版社
2018年9月
二
奧勒留繼位做的第一舉措,就是邀請安敦尼的另一養(yǎng)子維魯斯共理國事,這是羅馬帝國史上首度出現(xiàn)兩帝共治。隨后羅馬安息戰(zhàn)爭的東方戰(zhàn)事,奧勒留就托付給維魯斯處理,維魯斯率兵攻陷并焚毀了塞琉西亞和泰西封,與此同時一些士兵染上莫名且致命的傳染病,軍隊因此撤回國內。這些近東作戰(zhàn)的士兵帶來了天花和麻疹,大瘟疫序幕拉開。死亡之霾悄無聲息地從小亞細亞半島暴風一般席卷了帝國東部,旋即迅速蔓延到西部的意大利、高盧和日耳曼地區(qū),羅馬帝國所有的行省都無一幸免。兩個共治皇帝均病歿于這次瘟疫。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這次史上稱為“安東尼瘟疫”的傳染病,正是以奧勒留(馬可·奧勒留·安東尼·奧古斯都)的名字命名的。
這是傳染病學史上的一次大事件,也是人類歷史上十大惡性傳染病事件之一。它繼古希臘“雅典大瘟疫”之后,拜占庭“查士丁尼瘟疫”之前,為一千多年以后蔓延歐洲的黑死病風暴(即歐洲中世紀大瘟疫)開了先河。這場瘟疫,使包括社會精英在內的眾多人口集體斃命。如雅典,在167-171年間,首席法官的職務就因候選人病死而無法補足。考慮到相似體制的行政單位還有許多,不少地方的基層治理能力就因此遭遇重創(chuàng)。羅馬史學家迪奧卡稱,當時羅馬一天就有2千人因染病而死,占總傳染人數的1/4;而在有些地方,瘟疫造成總人口的1/3死亡。估計總死亡人數有500萬。
奧勒留當局不得不從普通奴隸或角斗士隊伍中招募新兵。但老兵的安撫與新人的入職,無不需要大筆資金維持,而帝國的銀礦開采也因瘟疫而陷入停頓,如東方商業(yè)重鎮(zhèn)亞歷山大港的銀幣鑄造完全停止,商品價格普遍上漲而地租卻巨幅下跌。梁實秋曾如此描述“民窮財困,局勢日非,瑪克斯(即馬可·奧勒留)被迫出售私人所藏珠寶,籌款賑災。此種困窘情形,在瑪克斯在位之日,一直繼續(xù)存在。內憂外患,交相煎迫。”這場瘟疫就像巨人泰坦的鐵拳,將帝國的各級秩序敲得搖搖欲墜,幾乎所有的行業(yè)均震蕩備至。
這場瘟疫足足肆虐了7年之后才趨于消停。當在公元191年再度大規(guī)模爆發(fā)的時候,奧勒留已經去世11年了。
兵戈瘟疫之外也并非全部,還有洪水泛濫,此處不贅。窮其執(zhí)政期間,奧勒留如同暴風雨中海上的一葉小舢舨,無時無刻不處在鞍馬倥傯和顛踣動蕩中。人類萬物的恒性在于追求平衡,外面越是風雨雷電,內里越是風淡云清,否則必然走向崩潰和滅失。你既然理解太平天國運動中的曾國藩、寧王之亂中的王陽明,那你也必然會理解奧勒留為什么成了“哲學家皇帝”了。
三
《沉思錄》這個名字是后人編輯成書時加的,奧勒留寫的時候從未想到過要公之于眾,這原本就是寫給自己看的,實際上就是自說自話和自我調節(jié)。奧氏是斯多亞派哲學家不假,但事事處處都是斯多亞派,那他本人只是作為學派標本存在么?自然不是。只是浸染既深,所思所想均自然而然循律而行,如孔子所說的“從心所欲不逾矩”,這個律就是斯多亞學派要義。另一方面,任何一種學說都是發(fā)展的,凡發(fā)展又是前無古人的探索,故而,《沉思錄》的呈現(xiàn)形式是斯多亞派吉光片羽的集大成者。中文首譯者梁實秋也曾體會到,“瑪克斯并不曾努力建立哲學體系,所以在《沉思錄》里我們也不必尋求一套完整的哲學。他不是在作哲學的探討,他是在反省,他是在表現(xiàn)一種道德的熱誠。”
《沉思錄》全書共12卷488條,基本無成書的體例和整體線索,一條幾十字或幾百字不等,或者說大體則有定體則無。這點和孔子的《論語》極其相似,且在為人處世自我修養(yǎng)方面的用力也相差無多,特別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儒學理學及宗教融為一爐,而這部“斯多亞派哲學最后一部杰作”正是倫理學和宗教的融合,一致的路徑使得接受理解相對容易。該書輯錄于不完整的手稿,且作者是寫給自己的備忘,除了自己不需要別人理解,一個例證是:羅馬官方用語是拉丁文,而奧勒留特意用希臘文寫作——這不是更小眾?但這似乎才是作者的目的,自我隱晦的力求不足為外人道。加之譯者特別是梁實秋則追求完整呈現(xiàn)本來面貌,所以全書表達重復或不完整、含義晦澀、邏輯矛盾的地方很多,但就梁譯本而言,全書當得起八個字:華疵互見,原始確切。很多讀者說人生寶典云云,應視為大不以為然。老實說,該書的完整和深邃雅致遠遜于《論語》。
《論語》是對話錄或授課筆記,《沉思錄》則是心音外放的隨手貼集,這是奧勒留的一個機密小宇宙——像赫拉克利特一樣,斯多亞派哲學信奉人都是宇宙的一部分,每人都是一個小宇宙,是大宇宙的縮影。小宇宙中再派生幾個小小宇宙,亦無不可。
那他為什么要用文字記下來,或者說,這樣做是為什么呢?
在《沉思錄》卷六的第十二,奧勒留有一個原因式的表述:
“如果你同時有一個繼母一個親娘,你會相當地孝順你的繼母,但是你會時常地投入你的親娘的懷抱。朝廷與哲學現(xiàn)在便是你的繼母與親娘。要時常地回到親娘那里去獲得你的安寧,這樣你便可以較能容忍你的朝廷生活?你的朝廷生活也可以較能容忍你。”
作為皇帝不能不顧朝廷,因為皇帝是一種工作,工作帶來的,躲不掉推不開,忍無可忍也得忍,奧勒留所謂“有兩個理由,使你安心接受你的遭遇:一是為你而才發(fā)生的……”;而作為獨立肉身的本人,唯一和徹底地固化在工作中,亮化在陽光下……是會死人的。器滿則溢,必須有一個騰挪空間,這是《沉思錄》的動因和嗜癖。寫下來就留住了精鶩八極心游萬仞的苦悶和頓悟,留住了就能時時翻閱,而每一次翻閱都是一次發(fā)泄和溫習。
“一般人隱居在鄉(xiāng)間,在海邊,在山上,你也曾最向往這樣的生活。但這乃是最為庸俗的事,因為你隨時可以退隱到你自己心里去。一個人不能找到一個去處比他自己的靈魂更為清靜——尤其是如果他心中自有丘壑,只消凝神一顧,立刻便可獲得寧靜。”
中國古語中有三個隱的境界:大隱隱于朝,中隱隱于市,小隱隱于野。奧勒留立存此照之后,原則上就是大隱,隱于朝堂,境界最高。但他超越了這個境界,他是在朝堂,是身份極其特殊且單一的——皇帝。皇帝必然是孤家寡人的心術施用者,故而如果非要加一個名號,他應該是極大隱。
《沉思錄》中談及最多的就是死。
“頂長的壽命和頂短的都是一個樣。”“以愉快的心情等候死亡。”“有一個幫助我們蔑視死亡的方法,雖然不大合于哲學,卻是頗為有效——那便是列舉一下那些頑健卻又長壽的人們。他們比起短命而死的人們又好了多少呢?……他們送了許多別人入葬,結果他們自己也入葬了。……永恒之內,只活三天的嬰孩的壽命和長達三世紀的一個Nestor的壽命是一樣的。”
奧勒留就用死亡的理所當然為底線為軸,看自身、看別人、看人際關系、看處理方法、看理性和善惡、看宇宙、看神、看靈魂……他的頂線就是宇宙和神,而神和靈魂屬于同一譜系,彼此成全。
奧勒留相信神是確實存在的,并且還做了論證:
“如果有任何人問‘你在什么地方看見了天神?你如何能確信天神之存在?……’我這樣回答:他們是甚至是眼睛都可以看見到的;再說,我也沒有看見過我自己的靈魂,但是我尊敬它。”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854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