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向陽/文 熱播反黑劇《狂飆》中的高啟強(qiáng),僅僅靠著自學(xué)一本薄薄的《孫子兵法》,苦學(xué)20年,就煉成了黑幫老大,煉成了魯迅所描繪的高級(jí)“流氓”——“無賴子加壯士加三百代言”。高啟強(qiáng)顯然屬于社會(huì)流氓階層的高段位,賴在無恥墮落,壯在無情殺伐,惡在無底線茍營。魯迅所說的“三百代言”,本是日語中用來描繪社會(huì)階層中的一些不法宵小之徒,如訟師、訟棍、不可靠的律師、玩弄詭辯者等,類似高啟強(qiáng)手下的那幫打手幫兇,如唐小龍?zhí)菩』⑿值埽F(tuán)取勢而成反社會(huì)幫派。

《狂飆》
徐紀(jì)周 朱俊懿 白文君 /著
青島出版社
2023年2月
根據(jù)魯迅先生的考證,中國社會(huì)的流氓階層最早有兩個(gè)來源:一是孔子之徒,所謂儒;一是墨子之徒,所謂俠。儒俠階層,素以文武行事,“這兩種東西本來也很好,可是后來他們的思想一墮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所謂的流氓。”。
這里的“思想墮落”,實(shí)際上指的就是儒俠兩個(gè)社會(huì)階層的地位墮落,在一個(gè)社會(huì)力量階層激烈變動(dòng)的時(shí)代或者“政治衰弱”之際,一旦社會(huì)權(quán)力空間中出現(xiàn)了大片的真空地帶,家道敗落的儒夫俠客末流,很容易由社會(huì)地位墮落進(jìn)而刺激其思想墮落,化身為新興流氓階層,把整個(gè)社會(huì)“鬧的亂七八糟,一塌糊涂”(魯迅語),其中也有極個(gè)別超級(jí)幸運(yùn)兒迎來命運(yùn)加冕時(shí)刻——甚至推翻政府,沐猴而冠。魯迅先生1931年在上海東亞同文書院進(jìn)行的一次名為《流氓與文學(xué)》的演講中,特別列舉了中國歷史上三個(gè)著名的流氓英雄:劉邦、劉備和朱洪武,三位都由草根流氓起家,最終黃袍加身,搖身一變成了“高祖”、“先祖”和“太祖”。
如此看來,如果要理解中國古代社會(huì)的權(quán)力變遷,流氓作為一個(gè)不見容于正史的特殊社會(huì)階層,實(shí)際上扮演著一種拉動(dòng)歷史杠桿吱吱作響的潛藏之重要力量。用歷史學(xué)者陳寶良的話來形容,就是“兩千多年來,流氓意識(shí)深刻影響著傳統(tǒng)中國”。他們?cè)谄胀ㄈ穗y以目及的灰色地帶游走,流氓階層一端與各種社會(huì)權(quán)力珠胎暗結(jié),另一端又掛著“替天行道”的正義旗幟,文化底色中還夾雜了復(fù)雜多面的宗法社會(huì)制度意識(shí)和思維傳統(tǒng),而“皇帝垂拱、士族當(dāng)權(quán)、流民出力”這一幕,更是中國歷史上曾反復(fù)出現(xiàn)的一幅構(gòu)建超級(jí)穩(wěn)定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權(quán)力譜系圖景。
流氓墮落史:從游俠、流民到流氓
流氓是如何墮落的?
除了社會(huì)變遷和時(shí)代轉(zhuǎn)換的影響外,流氓的演變史也經(jīng)歷了從早年的理想化到近世的世俗化、職業(yè)化、物質(zhì)化、卑賤化等若干發(fā)展階段,這其中,由游俠而流民,由流民而流氓,歷史演變中的一個(gè)明顯趨勢就是流氓階層的社會(huì)地位越來越墮落,行事方式越來越職業(yè)化,發(fā)展空間越來越“原子化”,社會(huì)聲譽(yù)也相應(yīng)越來越卑賤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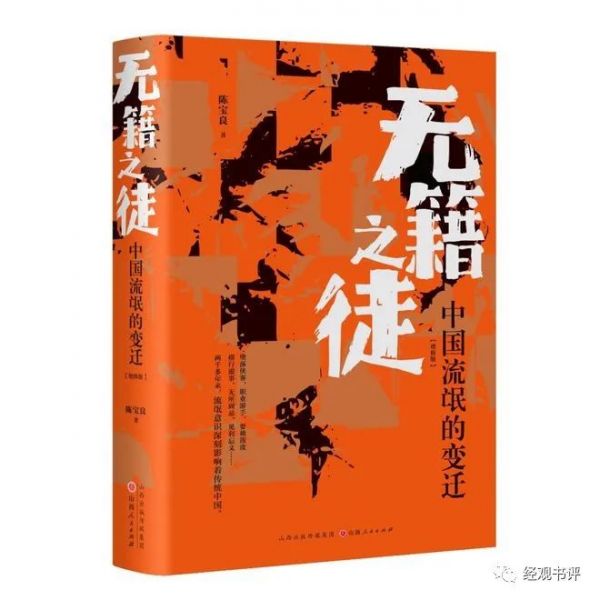
《無籍之徒: 中國流氓的變遷(增修版)》
陳寶良 /著
漢唐陽光 |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2年12月
學(xué)者陳寶良在《無籍之徒:中國流氓的變遷》一書中,通過各種搜羅爬梳,從“四書五經(jīng)”到“二十四史”,從先秦諸子到《全唐文》,從野史筆記到官方實(shí)錄、司法文書、乃至于各種地方志,上窮碧落,稽古鉤沉,發(fā)微抉隱地為人們展現(xiàn)了一部中國社會(huì)流氓階層演變的全景歷史圖畫。
根據(jù)不同時(shí)代和社會(huì)制度的流變,中國社會(huì)的流氓演變過程大體可以分為三個(gè)階段:第一階段是從遠(yuǎn)古到秦漢時(shí)期,以“游俠”為代表,典型人物如西漢的著名游俠朱家、郭解等,其特征是任俠仗義、快意恩仇,甚至不惜舍身取義。
第二階段是從魏到明清時(shí)期,以“游民”中的末流為代表,典型人物有《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等小說里的主人公如曹操、劉備、宋江、李逵、西門慶(這些小說人物雖然為小說家之摹寫,也是世情和流氓真實(shí)樣貌之折射),以及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等等,其特點(diǎn)是奸詐用狠,殺人嗜血,而且暴力和仁義在流氓文化中已經(jīng)被巧妙地縫合在了一起,稱得上是天衣無縫。
第三階段為清末以來現(xiàn)代意義上的“流氓”群體,這些無業(yè)游民活躍在中國近代最早開埠的上海等大都市,利用租界這樣的不同勢力角逐的灰色地帶茍營謀盜,代表人物有流氓大亨黃金榮、張嘯林、杜月笙等,其特點(diǎn)是宵小之徒,“遇事生風(fēng)”,組織和行事方式更加隱蔽,生存空間也更顯逼仄。
歷史上,流氓演變的一個(gè)明顯趨勢就是世俗化、職業(yè)化和卑賤化。早期的游俠是儒、墨之末流,在先秦貴族政治制度崩壞之后,周室既微,上下不順,社會(huì)秩序大亂,失去世業(yè)和依傍的流民中,祝宗卜史、禮官樂工的上層流民演變成為游俠中的儒士,而農(nóng)工之家的下層流民則成了游俠中的俠士。游俠的夢(mèng)想本來是要挽狂瀾于既倒,匡扶孔夫子所念念不忘的周制,這也從根本上決定了游俠的生存基礎(chǔ)和遠(yuǎn)大理想皆不合時(shí)宜,更難以施行。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史書中記載的朱家、郭解等游俠故事,融合了太多的文學(xué)想象和個(gè)人情懷。司馬遷是第一個(gè)在史書中為游俠立傳的史家,在《史記·游俠列傳》中,他由衷贊美游俠的美德:“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困厄”。其實(shí),司馬遷在遭遇李陵之難后,敢于為這些“不軌于正義”后來被誅殺的游俠作傳,不僅僅體現(xiàn)了一種史家之獨(dú)到眼光,更深的緣由是《史記·游俠列傳》本來就是一篇“激憤之作”,史家自傷身世而寄寓來者,才有借他人酒杯澆胸中塊壘的開創(chuàng)之勇。
班固《后漢書》之后,史家便不再為游俠列傳,這不只是游俠精神的幻滅,更是社會(huì)情勢的變遷。漢高祖時(shí)期的著名游俠朱家“專趨人之急”,救人于困厄,引得無數(shù)俠客“延頸愿交”;西漢名俠郭解力折公卿,一諾千金,民間藉藉有聲,聲震朝廷,最終犯事被誅殺。這些尚義大俠游離于社會(huì)正統(tǒng)秩序之外,尤為愛惜自己的羽毛,“殺人如剪草”,他們推崇的“私義”,雖遠(yuǎn)非今天社會(huì)公共空間所界定的“正義”范疇,但其磊落光明的人格精神和快意恩仇的豪放品行,不僅為后世文人小說家所追慕而反復(fù)書寫,更迎合了社會(huì)底層民眾關(guān)于正義和權(quán)力欲望的“民間想象”。
漢初,游俠對(duì)社會(huì)既定的正統(tǒng)權(quán)力秩序構(gòu)成了嚴(yán)重威脅,至漢景帝,游俠勇夫被批量絞殺后,游俠作為“一種富有魅力的精神風(fēng)度和行為方式”(陳平原語),就只存在于中國漫長悠久的武俠類型小說的文學(xué)想象中了。
魯迅先生形容這一變遷為“真老實(shí)的逐漸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俠”,真正的游俠以慷慨赴死為終極歸屬(歸于義),而剩下的茍活的小流氓們,只能以奸詐茍且為生存方式,且專趨于利。這便是從東漢末年和魏開始的流氓演變的第二時(shí)期。中國最著名的兩部經(jīng)典通俗小說《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有大量的記錄,其中不乏小說家言的加工附麗,但小說中摹寫的諸多經(jīng)典流氓人物和流氓行徑,其影響和遺毒不可謂不歷久彌遠(yuǎn),深入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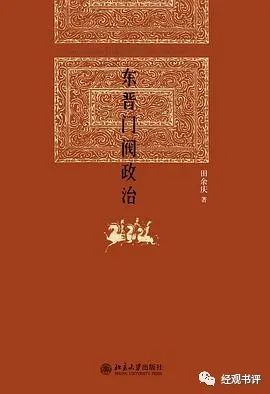
《東晉門閥政治》
田余慶 /著
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
2012年5月
流氓的精神氣度和行事格局越變?cè)叫。跈?quán)力征逐引發(fā)的社會(huì)結(jié)構(gòu)變化中,影響力卻越來越大。當(dāng)代知名歷史學(xué)者田余慶在《東晉門閥政治》中指出,“皇帝垂拱、士族當(dāng)權(quán)、流民出力”,就是漢末特有的一種社會(huì)穩(wěn)定之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后來,這一幕在數(shù)千年歷史中不斷重演,每一次社會(huì)動(dòng)蕩都會(huì)滋生出一大批流民中的末流,或像朱洪武從軍從戎,或像宋江者流落草為寇,職業(yè)流氓和不安分流民以及不滿現(xiàn)狀的底層農(nóng)民嘯聚起義,充當(dāng)引發(fā)社會(huì)權(quán)力變化的暴力杠桿,一次又一次的農(nóng)民戰(zhàn)爭中,在撬動(dòng)顛覆既有秩序、重新建立超級(jí)穩(wěn)定的社會(huì)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進(jìn)程中,流民一直扮演決定性的力量。
流民兇猛,和中國歷史上基于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之上的宗法制度息息相關(guān)。在“士、農(nóng)、工、商”固定等級(jí)化的社會(huì)結(jié)構(gòu)中,流民不僅沒有位置,更被視為一股隨時(shí)對(duì)主流權(quán)力秩序構(gòu)成巨大威脅的潛在危險(xiǎn)暴力。在歷史語境中,“流”是指無籍的失業(yè)之民,即所謂的無業(yè)游民;氓的本意是指出身卑賤的“草野之民”。失去了住所、土地、職業(yè)和社會(huì)身份,家園不再,走投無路,流民群體就成了社會(huì)中最不安全的“火藥桶”。
自魏以降,每逢戰(zhàn)亂則流盜紛起,承平時(shí)則路少遺民,到了明代中后期,因變亂流民引發(fā)的流氓群體數(shù)量激增,為一時(shí)之冠。洪武皇帝就系流民出身,早年混跡游方道僧行列以謀生,后來又投奔農(nóng)民軍隊(duì)尋找發(fā)跡生路,依靠他的狡黠善學(xué)和流浪多年的社會(huì)生存技能,終煉成了流氓大亨。太祖上位之后,對(duì)于流民的管制不可謂不苛刻,另一方面,明朝流民之流弊,遺毒也最熾烈。洪武年間,從每天的“宣諭”制度開始,到在南京建筑“逍遙樓”專門收治和懲處流民,甚至于還有對(duì)游方道僧大開殺戒的“鏟頭會(huì)”,這些專門針對(duì)流民的嚴(yán)刑峻法也只是維持了明初幾十年的安寧。明朝中期綱紀(jì)廢弛,豪強(qiáng)兼并,社會(huì)階層分化所產(chǎn)生的喇唬(詐騙犯)、光棍(當(dāng)時(shí)特指職業(yè)流氓)、把棍(惡棍)、打行(打手)、衙蠹(與官府相通的流氓)、閑漢(小混混)、秦淮健兒(惡少)、豪強(qiáng)大猾、太監(jiān)等等新興流氓階層,充塞閭巷,到處橫行滋事。
明末的流氓隊(duì)伍中,游惰之習(xí),幾乎染及四民,其中尤以士風(fēng)墮落為甚,屬于流氓群體的一個(gè)新變種。這些所謂的游士“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已;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而已。究其為害,更甚于游民也”。更有一種“罷閑官吏、山人詞客”,成天“播煽流言”,訕謗朝政,徒亂人國。加之明末閹黨熾盛,太監(jiān)每每和東林黨的迂闊儒生們針鋒相對(duì),不僅社會(huì)撕裂,政治領(lǐng)域也愈加流氓化,流氓文化迎來了卑賤下流的新巔峰。
清末以后,流氓演變進(jìn)入第三階段。這一時(shí)期,流民被“無賴”一詞所取代,流氓的社會(huì)空間變得愈加狹小,1840年中國沿海商業(yè)口岸紛紛開埠,“流氓”一詞得以被正式命名,上海、天津等率先開放的城市逐漸取代了蘇州、揚(yáng)州等內(nèi)陸商埠,成了流氓麋集的冒險(xiǎn)家樂園,上海的“白相人”(以嬉戲玩耍為業(yè))、天津的“混混兒”紛紛出現(xiàn),一種新物種開始粉墨登場。這些大都市流氓雖然花樣翻新、各極其巧,但其職業(yè)伎倆越來越卑賤下流,只是在各種社會(huì)勢力的邊緣空間里騰挪游走,就像電影《羅曼蒂克消亡史》中所展現(xiàn)的那樣,其力量和影響也越來越式微而漸趨消亡了。
反抗流動(dòng):周期性的社會(huì)癥候
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huì),階層流動(dòng)才會(huì)引發(fā)權(quán)力流動(dòng),關(guān)于流氓的歷史研究和社會(huì)學(xué)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首先,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huì)的權(quán)力譜系中,流氓群體扮演了一種鯰魚之類的角色,它激發(fā)并維持著社會(huì)權(quán)力的平衡、失衡和再平衡,從而展現(xiàn)出周期性社會(huì)發(fā)展的內(nèi)在歸因。他們既是維持社會(huì)權(quán)力微妙平衡的力量,又是撬動(dòng)和改變這種平衡的杠桿,其破壞性力量和社會(huì)影響力都不可小覷。另一方面,在傳統(tǒng)皇權(quán)社會(huì)制度下,流氓先天缺乏合法性的社會(huì)基礎(chǔ),其興也勃,其亡也忽,主流權(quán)力秩序始終反抗流動(dòng),促成權(quán)力流變的流氓屬于一種意外變量,兩種權(quán)力相互較量且此消彼長。
其次是歷史上流氓社會(huì)身份的變化值得關(guān)注。數(shù)千年流氓演變史,最明顯的一個(gè)趨勢就是,流氓的社會(huì)角色從公共空間向私人空間逐步倒退。從先秦的儒俠之末流,到明清時(shí)期的市井無賴,源于孔子而迄于郭解的中國武士道精神早已幻滅殆盡,名俠的理想主義也隨之墮落委頓,但關(guān)于游俠流氓的文化傳說,卻為社會(huì)底層建立了一個(gè)想象中的江湖世界,它和官府世界遙遙相對(duì),在武俠小說類型文本中,這個(gè)其實(shí)并不那么光鮮美好、遙不可及的江湖世界,寄托了歷代文人和讀者們對(duì)于桃源世界的理想。

《魯迅全集(2021年新校版)》
魯迅 /著
萬文社 | 花城出版社
2021年8月
最后,流氓文化和農(nóng)民意識(shí)之間的融合雜糅和相互濡染也值得研究。數(shù)千年以來,流氓思想對(duì)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政治等領(lǐng)域的滲透浸潤極深,魯迅的小說《阿Q正傳》曾對(duì)之有過極精彩的描述。按照魯迅的解讀,流氓階層起源于各種社會(huì)權(quán)力的縫隙,走的是刀鋒上舔血的危險(xiǎn)路線,像最初的俠客被夾在官府和強(qiáng)盜之間,生存空間極其有限,這才有了流氓的誕生。流氓的本性里混合著國民性里最狡黠油滑的因子,“和尚喝酒他來打,男女通奸他來捉,私娼私販他來凌辱,為的是維持風(fēng)化;鄉(xiāng)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來欺侮,為的是看不起無知;剪發(fā)女人他來嘲罵,社會(huì)改革者他來憎惡,為的是寶愛秩序。但后面是傳統(tǒng)的靠山,對(duì)手又都非浩蕩的強(qiáng)敵,他就在其間橫行過去。”
活躍在奴隸和主子之間,流氓分明是社會(huì)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中的微妙力量,可以上下逢源而游刃有余。這樣來看,《狂飆》里高啟強(qiáng)“卑微、跋扈、謙和”的三重面,分明只是阿Q自我革命式的又一個(gè)翻版,社會(huì)生活經(jīng)驗(yàn)豐富的“演技派”老生張頌文,最擅長把小人物演活了,這是演員之幸焉,還是編劇美化角色過了頭,抑或是觀眾的感情動(dòng)錯(cuò)了地兒,這又是另一個(gè)值得玩味的“社會(huì)癥候”了。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802028547號(h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