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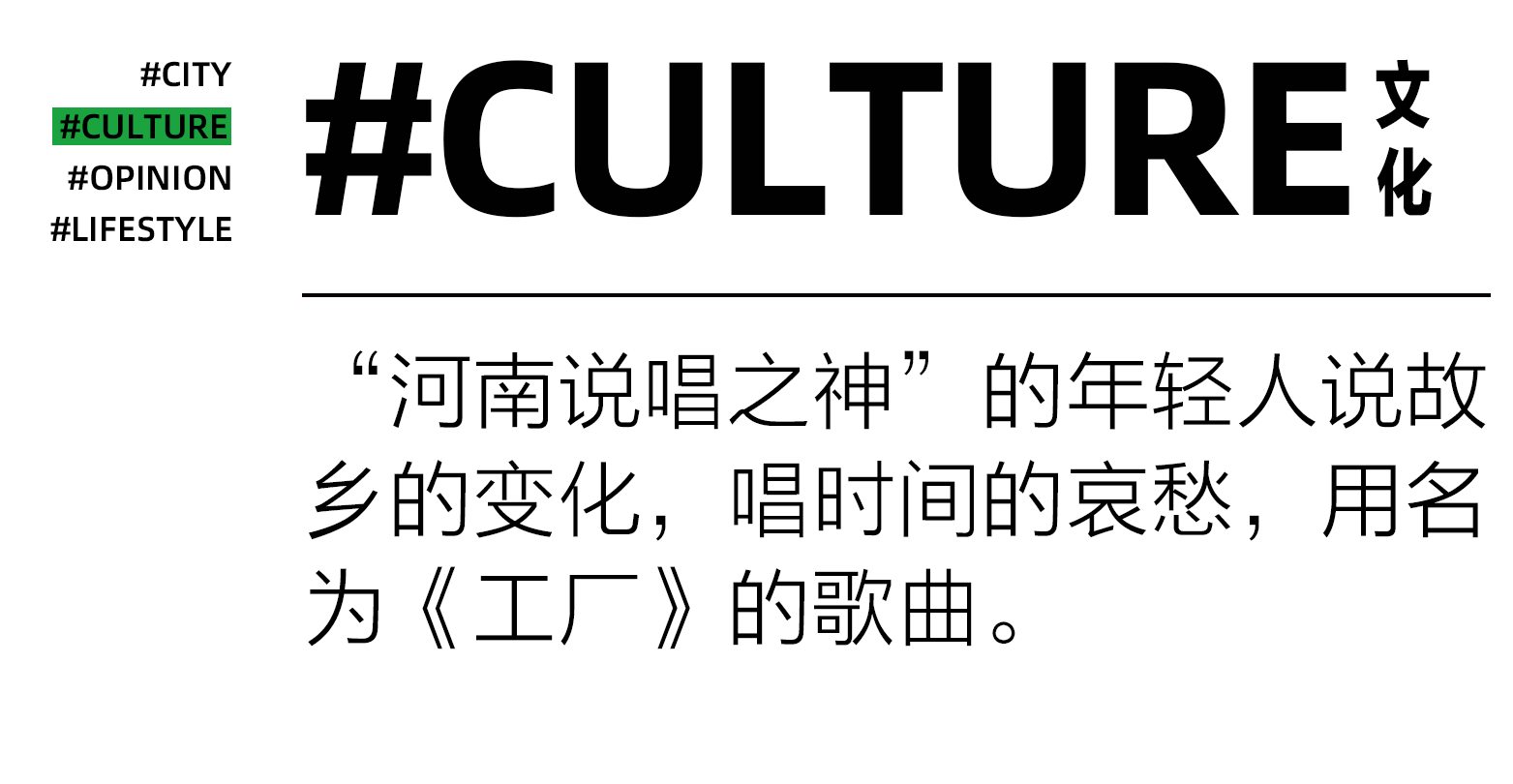
新生活方式研究院/文 《工廠》火了兩周,當暴漲的傳播曲線逐漸回落,它帶給人們的后勁,或許才剛剛開始。
歌曲的突然走紅,并不在作者張方釗的預期之內。他說,歌寫出來,當然想好好宣傳,但沒承想火成這樣。
張方釗在《中國新說唱》里的阿卡貝拉環(huán)節(jié)唱了這首歌,但當時沒有太多人察覺到它的價值。直到MV上線,全網轉發(fā),人們才反復確認著一件事:一般的作品,寫的是自己;動人的作品,寫了所有人。

張方釗用歌詞把河南故鄉(xiāng)堆疊為一個舞臺,來自各地的聽眾都在舞臺上尋找自己的位置。這種作者和聽眾的共同參與,是一個兼具詩意和反身性的總結,讓沉默敦厚的土地和更多的地方有了具體而相似的樣貌。
MV里,張方釗站在兩個煙囪之間,拆遷的廢墟之上,像王寶強演的樹先生,賈樟柯電影里彷徨的人,用他的慵懶吐字和emo說唱風格,開始講故鄉(xiāng)與他的故事:工廠舊址腳下?lián)P起了塵,孩子們舉著關刀玩具穿越樹林。一個孩子趴在白墻上,畫沒有被煙霧蓋住的星星。
歌里唱,“他沒有故事/也沒有人聽”,但驚人的播放數(shù)字證明,它不僅“有人聽”,而且被河南年輕人聽到了心里。無數(shù)人涌入評論區(qū),寫下自己有關河南的種種,也讓這首《工廠》,成為2024年人們注定將記住的旋律之一。


面對張方釗,我首先好奇,這首歌創(chuàng)作的機緣是什么?
他說,2023年7月收到《工廠》的伴奏,聽了一會覺得很棒,腦子里很快有了畫面:拉長的合成器聲音仿佛時光機,把他從記憶的鐵軌送回童年。吉他如車輪快速滾動,帶著孩子的笑鬧聲疾馳。
歌詞隨之而來。關于童年,故土,被時間改變的村莊,如釘子般留守的人們,像他一樣離開的年輕人。他的童年時代,裹滿快樂和塵土的過往,他所心疼的農民,始終支持他的媽媽,離開故鄉(xiāng)闖蕩的心酸,還有那么多矗立在現(xiàn)代化與工業(yè)化中的鄉(xiāng)親們。
可以這么說,張方釗為《工廠》足足積攢了27年的素材,每一個字可能都在過去念過,如今只是剛好把它們拼了起來。這些素材落向這片沉默的中原大地,留下一些神造訪過的痕跡。他并沒有覺得把素材變成歌詞是件難事,寫得很快,幾乎沒什么阻礙,“我寫的全是自己,都是些大白話,很自然就出來了。”

整首歌有一種由糾結而生的張力,尤其糾結的是那句打動許多人的“我沒有熱愛這里/我只是出生在這個地方”。
這句話特別有張方釗的味道,他的人跟他的說唱一樣,看似情緒很淺,實則思慮很重,有時發(fā)音含糊,但總有一條堅定的、憨直的軸立在話語的中間。他說認定的東西很難動搖。
他跟我說,當他看網友評論,看到有人能理解這句歌詞里的矛盾不安,有那么多的人對這句話產生共鳴,開始觀察自己和故鄉(xiāng)的關系,他會特別高興——他當然愛家鄉(xiāng)和人,也沒有抱怨過自己的出身。他要表達的是一種命定般的憂愁,他要為這個很多人保持沉默和板正的地方說句話。
也正因為此,他給自己起了“河南說唱之神”的名字——既然無法擺脫,那就不要擺脫,正視它,對抗它,與它對話,去和理解和不理解的對話。

實際上,他一直都沒有真正離開過家鄉(xiāng)。張方釗在成長過程中,去過東北、河北,再回到河南鄭州,從務農、念書到做音樂,掙了錢,得了名,但沒有停止過自我分析和懷疑。故鄉(xiāng)像身上褪不掉的烙痕,而“那些都是姊妹兄弟”。他沒忘了自己是誰,卻又總是困惑自己能代表誰。他幸運地逃離了鄉(xiāng)村,但他依然在原地。錢和聲望沒有讓他變成另外一個人,卻讓他無法停止關于未來的思考。
他把這些糾結的,看似普通但無比真實的情感表達出來,寫成了《工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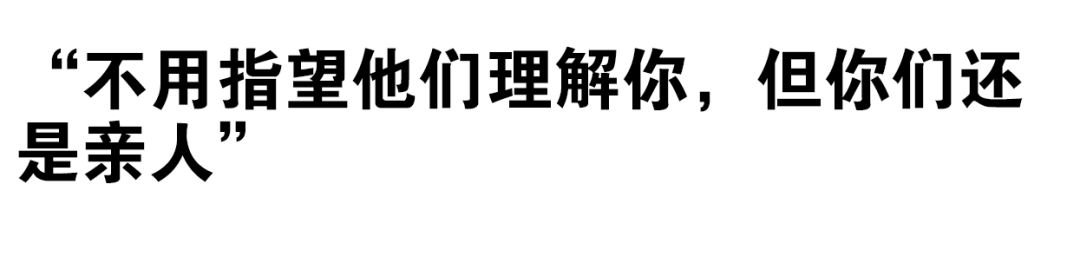
與張方釗這個棱角分明的名字相對照的,是出現(xiàn)在MV里的一些堅硬的元素:河南焦作的鄉(xiāng)村,不太清澈的河流,愈發(fā)退讓的田地,家附近廢棄的化工廠。這些是他無法舍棄的故土的一切。
這是他的來處,他的傷痕,他的精神歸屬,也是他想擺脫而不得的背影,這種情感樸素而復雜。
張方釗在采訪中一直保持低沉且有些含糊的語氣,但當提到有人質疑歌曲MV濾鏡灰暗、有過度展示土地破落的嫌疑時,他的聲音突然大了許多:
“我怎么會黑這里呢?這可是我家啊!”
MV里還出現(xiàn)了很多孩子,和張方釗當年一樣在村道上奔跑的孩子,一些喊他叔叔的小孩,一些輩分上是他叔叔的小孩。在MV中出鏡的還有他的母親,以及他的數(shù)量龐大的老家親戚。

拍MV之前,媽媽幫張方釗到處問親戚,求人幫忙,最終三姑六婆、叔叔侄子、村頭村尾,來了好多人。不像來拍一個MV,倒像春節(jié)聚會。張方釗說,親戚朋友們被喊過來幫忙,大家對拍MV這件事其實沒有概念,談不上表演,但每個人都充滿熱情。他和導演李煊大概定了個框架,隨后讓他們做自己,做平常做的事,玩,鬧,用自己的方式消磨時光。
這很像《工廠》的動人之處,不只是音樂,它還是生活本身,擁有輕松的、不知所措的、表演的和非表演的細節(jié),真實性就藏在這些看似日常的片段里。比如拍親戚們在院子里的一組鏡頭,導演只交待了基本站位和動作,抽煙的,看手機的,聊天的,自然落位。
張方釗說,他們自己開始研究起如何互動。有個大姨說,你抽煙,那我就來搶你的煙吧。大叔說,你看手機啊,那我就擱你邊上一塊兒看。
相比起一個被全國人民知道的歌曲和MV,張方釗覺得更幸福的是借這個回家的機會,與家里的人一塊。他喜歡被一群親戚們簇擁的那個畫面。他呆呆地望著天空,表情看似空洞,但心里有暖意。他說,這是一張多難得的大合照啊,平常大概沒有機會拍到人這么齊的。

他不跟老家的人解釋自己在做什么,說唱是什么。解釋不清。他看得很開:“你不用指望他們理解你,但你們還是親人。”

聊到“河南說唱之神”這個響亮且有些中二的名字,張方釗很坦然,他沒覺得這是一頂太大的帽子,而是一種給自己的故鄉(xiāng)正名,為自己的媽媽和兄弟姊妹說幾句的倔勁兒。他說自己特別對抗,越不讓干越干。之前一張專輯叫《哥們廢了》,是因為不想照著別人定好的道路走;沒人為河南說點什么,那他來說。
張方釗對說唱的興趣,源自于少年時看的一檔《帶著節(jié)奏說話》的新聞節(jié)目,整體風格則源于蛋堡。他是相對少見的emo說唱歌手,有憂郁悲傷的詩人氣質。他尤其喜歡蛋堡的《少年維持著煩惱》,欣賞蛋堡能用樸實真誠的詞寫身邊的事,于是后來的他和蛋堡唱的一樣:
“那少年維持著煩惱/專心在他的煩惱/微不足道的煩惱。”
張方釗的其中一個煩惱大概是,他既是普通人,但不大可能是一個純粹的普通人。他是在鄉(xiāng)村務農的少年,但現(xiàn)在他想為這些務農的人們表達些什么。
他的說唱原本就有許多人喜歡,在上了說唱節(jié)目、憑《工廠》獲得更廣泛的認可之后,他打響了“河南說唱之神”的名號,憑著聲名和技藝掙了錢,某種程度上他已經脫胎換骨,躍升到另一個階層。但當他回到村子里,在媽媽和親戚們的眼里,他還是騎著帶光條摩托車的普通鄉(xiāng)村青年,也是戴著奧特曼面具隨性舞動的小孩。無論走多遠,他還是張方釗。

《工廠》之所以反響熱烈,是它喚醒了許多人。張方釗用他的白描,把“家鄉(xiāng)”這個詞還原成了一個讓人心疼的模樣。歌曲的強大共鳴從中原輻射到全國各地。這不是張方釗一個人的見聞體悟,是每一個人。他是你和我,你我也是他。我們和張方釗一樣,面對故鄉(xiāng)、面對過去和未來,有著相似的糾結。時間加速流逝,能握住的也同樣不多。
這首歌讓很多人看到了自己,然后用類似的方式嘗試表達自己,或者表達某個人群的聲音。《工廠》MV在B站的播放量已經達到了515萬,各種共創(chuàng)層出不窮。比如把MV替換成《hello樹先生》等其他影視劇的畫面,或者重新填詞去描摹自己故鄉(xiāng)的現(xiàn)狀。
無數(shù)人在評論區(qū)說著自己的故事,他們來自河南,來自河北,來自江浙,來自山東:我離開了故鄉(xiāng),但我依然屬于那兒。
這層底色附著在身上,無論走到哪,都是在成長的痛苦中反復確認自我,糾結未來的去向。

張方釗寫的是無聲的土地,而這些體驗是可以遷移到每一個普通人身上的。我們的家鄉(xiāng)都在高速發(fā)展下劇變。童年或是被封存起來,或不復存在。老家有親戚,有記憶,街巷被熟悉的味道串聯(lián)起來,幾條怎么走都不會錯的路拼接成過往。我們還是毅然決然離開了,但類似《工廠》這樣的作品,會把我們帶回過去,在一種懷舊的情緒共情陌生人,也共情自己。
《工廠》最大的意義,是唱出了我們沒有必要因為窘迫和遲疑,而對身邊的真實視而不見。
過去,我們很少把河南與說唱關聯(lián)在一起,但張方釗用實踐證明了,說唱本來就源自街頭與鄉(xiāng)土,寫的是自己的本心。它天生區(qū)隔于主流敘事,帶著調侃、懷疑和批判的氣質。《工廠》是這種理念下的產物,而我們期待會出現(xiàn)更多。
我不夠真實 我太要面子
其實我需要很多的錢來
將我的自卑和不安給掩埋
但我了尊嚴我不想給賤賣
做好事不成功 那我就變壞
我沒忘我是哪個
我怎會忘記我姊妹兄弟
我又能代表哪個
經常性陷入了自我懷疑
當他帶著復雜的情感唱出河南人所難以言說的復雜心情,不同地方的人們心中,響起了廣泛的共鳴。
作者:騰??宇
排版:張心睿
運營:李靖越
監(jiān)制:羅??嶼?
編輯?:宋??爽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8547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854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