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y湛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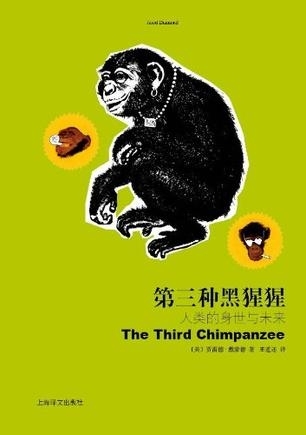
生活越來越像一部科幻片了,環(huán)境破壞、氣候變化、日新月異的科技產(chǎn)品,以及時(shí)不時(shí)發(fā)生在現(xiàn)實(shí)中或精神上的戰(zhàn)爭(zhēng)。我們?nèi)缃裼行乙灿心芰ΩQ見這一切,前無古人,繼往開來,以致于不需要把時(shí)間往后推,似乎一切困難與問題都是新生兒,每個(gè)人都毫無理由地去堅(jiān)信人類與環(huán)境曾經(jīng)有過和諧共處的“黃金時(shí)代”,是科技與文明進(jìn)化的雙刃劍把現(xiàn)實(shí)劈砍成如此美麗又如此丑陋。如果這時(shí)候有人站出來說:“你們都錯(cuò)了。”那他八成是個(gè)科學(xué)家,要知道,科學(xué)總是違反常識(shí)的。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就扮演了這樣一個(gè)角色,一如生物演化學(xué)的鼻祖達(dá)爾文多年前所做的那樣。
人異乎于禽獸,毋庸置疑,人是一種大型哺乳類動(dòng)物,亦毋庸置疑。但是哪些關(guān)鍵因素使人所以為人?除卻那些我們引以為傲的文明標(biāo)識(shí):語言、藝術(shù)、農(nóng)業(yè),很不幸,吸毒也要被涵蓋進(jìn)去。在科學(xué)面前,一切道德名詞都是乏味又無力的,寫就科學(xué),唯需根植于事實(shí)的推理。《第三種黑猩猩》是戴蒙德被授予麥克阿瑟基金后,決心將自己的思考傳播給大眾而寫就的第一本科普作品。雖然他并非人類演化學(xué)的科班出身,但正如《第三種黑猩猩》的譯者王道還所說,作者恰是因此,在精神意趣上成為了“今之古人”,以傳統(tǒng)“自然史”發(fā)展之路透顯人性的根源。
戴蒙德是一位生物地理學(xué)家,他的經(jīng)歷頗值玩味:童年時(shí)趕上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父親在他的臥室墻壁上掛了兩幅巨大的地圖,一幅是歐洲地圖,一幅是太平洋地區(qū)地圖。隨著戰(zhàn)況的變化,父親每天都會(huì)移送地圖上的別針,這激發(fā)了他早年對(duì)地理和歷史學(xué)的興趣。在成長(zhǎng)過程中,他愛上了對(duì)野鳥的觀察,并因此決定從事與生物學(xué)相關(guān)的職業(yè)。戴蒙德受過生理學(xué)博士的訓(xùn)練,以生理學(xué)研究的成績(jī)當(dāng)選美國(guó)國(guó)家科學(xué)院院士。他還繼承了母親的語言天賦,學(xué)會(huì)了12種以上的語言。所有這些都使他可以進(jìn)一步研究和解釋科學(xué),打破“兩種文化”(人文與科學(xué))的分庭抗禮。
一個(gè)帶有人文關(guān)懷的科學(xué)家的視角是別具一格的,戴蒙德在《第三種黑猩猩》中探討了許多使我們困惑卻被我們忽視已久的問題:作為人類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的農(nóng)業(yè)并非只為人類帶來好處,事實(shí)上,女性地位的變化,階級(jí)的形成,都是自農(nóng)業(yè)被“重新發(fā)明”之后的事;人類會(huì)明知有害,卻故意地去吸毒、酗酒、攝入煙草,持續(xù)這種行為原因或許是“上癮”,但愿意去嘗試則可以用動(dòng)物界的殘障原理去解釋——只有那些對(duì)個(gè)體有害的構(gòu)造和行為,才能有效地顯示發(fā)出訊號(hào)的個(gè)體是誠(chéng)實(shí)的,例如“我的身體足夠強(qiáng)壯”。而人與動(dòng)物在這點(diǎn)上的關(guān)鍵性差別,只是動(dòng)物看似“自毀”,實(shí)則利大于弊,人類卻是真正的代價(jià)遠(yuǎn)超收益。
雖然人類的很多特征都并不能使我們對(duì)未來更加樂觀,但在戴蒙德看來,真正有可能引領(lǐng)我們走上毀滅的則是我們仇殺外族的潛能以及對(duì)環(huán)境的破壞。人類在地球上無止境地?cái)U(kuò)張,伴隨著征服、驅(qū)趕和殺害其他的族群。“我們成為彼此的征服者,也是世界的征服者。”戴蒙德以科學(xué)的推理追問:為什么某一族群擁有征服其他族群的文化優(yōu)勢(shì)?沒有任何證據(jù)能夠表明一些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優(yōu)秀,事實(shí)上,一些父母還停留在石器生產(chǎn)的人,子女現(xiàn)在卻以開飛機(jī)為生。“有些社會(huì)的文化習(xí)俗成為世界主流模式,不是因?yàn)槟切┪幕?xí)俗可以令人幸福或者有利于人類的長(zhǎng)期生存,而是因?yàn)槟切┥鐣?huì)在經(jīng)濟(jì)和軍事上的成就。……各大洲的文明業(yè)績(jī)不同,是因?yàn)樗茉煳幕卣靼l(fā)展的力量,是地理,而不是人類遺傳學(xué)。”
本書的第四部分被命名為“世界征服者”,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給戴蒙德留下的經(jīng)驗(yàn)使他對(duì)戰(zhàn)爭(zhēng)有深刻的思考,這種思考是科學(xué)式的,而非哲理性的,戴蒙德將人類視為第三種黑猩猩,也以對(duì)黑猩猩觀察的實(shí)例指出:所有人類的行為特征中,最直接從動(dòng)物前驅(qū)中衍生出來的就是滅族屠殺。曾經(jīng)有人類學(xué)家提出,人類演化的過程受人類狩獵的需要驅(qū)動(dòng),戴蒙德覺得這也許是個(gè)事實(shí),“只不過,我們狩獵的對(duì)象也是人,我們是獵人也是獵物,因此我們被迫群居。”
責(zé)怪被害人這一心理變奏使得滅族屠殺有了合理性,對(duì)于那些“站在錯(cuò)誤一方的人”,怎么做都可以,包括滅族屠殺。人們例行公事般將受害者比作畜生,各族語言中都不乏其辭。最可悲的是,滅族這種悲劇性事件并不會(huì)給第三方造成什么影響,很多人或許不以為然,但實(shí)際上,細(xì)數(shù)人們對(duì)某些事件的關(guān)心,例如發(fā)生在中東地區(qū)的戰(zhàn)爭(zhēng),實(shí)則了了。由于我們甚至不曾記得,因此這類前例也就更加無法成為阻止新悲劇釀成的契機(jī)。人類目前殺戮外族的能力隨著武器的愈加精良已空前強(qiáng)大,而隨著社會(huì)間沖突的加劇,相互廝殺的欲望也逐漸升高,人類有能力毀了別人,也有能力毀了自己,這在今天越發(fā)不是杞人憂天。
所有這些現(xiàn)實(shí)無不使人悲觀,更早之前就有人發(fā)出過嘆息,探險(xiǎn)家維希曼預(yù)測(cè)人們會(huì)重復(fù)前人的錯(cuò)誤,因此在其所著的《新幾內(nèi)亞探險(xiǎn)史》中以一句“什么都沒學(xué)到,什么都忘掉”作為結(jié)尾。如今有無數(shù)的科幻片展示著人類最后的窮途末路,但戴蒙德卻說,如果相信毀滅的命運(yùn)早已注定,他便不會(huì)寫這本書了,人類的命運(yùn)遠(yuǎn)未可知,或許我們要比兩種黑猩猩幸運(yùn)多了,誰說的準(zhǔn)呢?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802028547號(h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