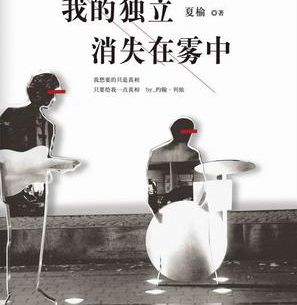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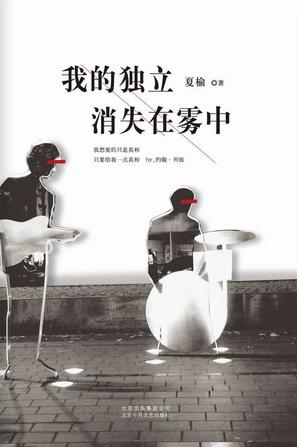
作者: 夏榆
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by王元濤
霧霾中的北京,夏榆的小說正應(yīng)景:一切美好與不美好都在,又都湮沒在霧中。
《我的獨立消失在霧中》據(jù)稱是部半自傳體小說,猜想哪些情節(jié)是夏榆的真實經(jīng)歷,哪些出自他的虛構(gòu),成了一份額外的福利。夏榆長期從事記者工作,記者寫小說,往往讀者意識太強。不自覺地取悅擬想中的讀者,就絕難做到以自我為中心。而小說需要以自我為中心,需要那種不管不顧的粗暴勁頭。怎么痛快怎么來。你痛快了,我痛快了,才算真正有緣分。這是小說與報道的本質(zhì)區(qū)別。夏榆的敘述手法還不夠圓熟,但態(tài)度接近神圣,仿佛新聞工作只是小說創(chuàng)作的一場實習。
小說的主要人物有三位,“我”是一種支點似的存在,里里外外補綴起唐卡與陸游的人生線索。唐卡是一個年輕姑娘,有錢,有時間,卻沒快樂,盡管她已獨自游遍世界。陸游是一位調(diào)查記者。他揭艾滋病黑幕,揭工廠污染黑幕,得罪了官方,被迫逃亡,后經(jīng)唐卡介紹,到“我”居住的城鄉(xiāng)結(jié)合部暫時棲身。這樣三個人,糾纏在北京的高樓之間和胡同深處,會有一段什么樣的故事?
小說中的“我”高度仿真。夏榆做過礦工,“我”也曾是礦工。我不免擔心夏榆借“我”之口來申明“礦工經(jīng)歷是我人生的財富”。還好他沒有那樣做。礦工經(jīng)歷于他不是財富,是實實在在的痛苦。而對這種痛苦的反思,可能是財富,也可能相反。
更重要的是,夏榆并沒有因為體驗過礦工的苦,就借勢控訴時代。這一點足以證明,夏榆已不再是記者,他有資格躋身小說家行列。作為礦工,早已不再有機會像時傳祥一樣去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握住一雙保養(yǎng)良好的手,但這個工種,終歸有人要干。有人做礦工,自認為是大不幸。有人為了做礦工,卻還在四處求爺爺告奶奶。這才是生活。從個人出發(fā),到個人結(jié)束,與時代,與政治正確,都毫無關(guān)涉。
一直期待夏榆能徹底地直面他的礦工經(jīng)歷。在這部書中,他又一次做出了勇敢的嘗試。但走到一大半還是退了回去。他寫到了礦井下的孤獨和封閉,寫到了父親的粗暴與冷漠,但涉及礦工群體對他身體的污辱與摧殘,就不肯鋪陳更豐富的細節(jié)。這種深及骨髓的痛,他可能還沒有做好分享的準備。
不知道有多少人會透過夏榆的筆愛上唐卡,但我想挑剔再一點,夏榆筆下的唐卡少年時曾受到過性侵,因此始終未能擺脫迷茫和自棄。其實若讓唐卡過的就是平常日子,只是因為缺乏愛,就不會愛,只是因為沒有體會過信任,就不懂信任,因此而迷茫,則更有平凡的悲劇意味,也更容易激活我們靈魂深處同樣固有的那片蒼茫。
夏榆讓唐卡背負著陳年的創(chuàng)痛,游走于世界的深處。西班牙曾是她的最愛,在那里,日常就是狂歡,漫步就是風情,她尋找一切機會讓自己迷醉。迷醉,就是最成功的逃亡。但馬德里恐怖爆炸案恰在她眼前發(fā)生,一下子把她拉回了現(xiàn)實。那一刻,她突然失去了行走能力,仿佛冥冥之中有神靈在告誡她:你注定無處可逃。
夏榆在處理陸游這個人物時,顯得有些猶豫。我因此確信陸游是虛構(gòu)的。在他身上,集中了這個時代記者的最大困境和焦慮,他們與律師群體相似,在扒糞的過程中,直接面對這個社會的病灶,無從閃避,無力改變,因而受害最深。在陸游這個人物身上,隱約有夏榆的影子,影子與他,恰如父兄。
但陸游的逃亡稍顯牽強。夏榆沒有交代,所謂的官府追殺是不是陸游的自我恐嚇。現(xiàn)實生活中,為了強調(diào)自我重要性,很真誠地以為自己正在受到迫害,這樣的記者不是一個兩個。夏榆似乎不耐煩這類形而下的情節(jié)交代,他更迷戀那種抽象的孤獨和苦痛。
唐卡在逃亡,陸游在逃亡。“我”則是一個旁觀者。或許,“我”已厭倦了那種憂傷;或許,是礦井生活,讓“我”的大半個身子依然扎在地下,動彈不得。而“我”精神層面的逃亡,則早已在無數(shù)個暗夜,令自己膽戰(zhàn)心驚。
夏榆小說營造的氣場,讓我聯(lián)想起捷克小說家赫拉巴爾以及他的《過于喧囂的孤獨》。赫拉巴爾日日守在垃圾場做苦工,他不以此為樂,也不以此為恥,更不認為“生活在別處”。身體與意念被生活漸漸磨損,這才是文學(xué)真正的營養(yǎng)。夏榆也是這樣,首先自我壓榨,然后謙卑地指點江山,因此,我愿意視他為這個時代殘存的意志圣徒。
同時,夏榆與赫拉巴爾面對的人群也極為相似。揭露真相,展示苦痛,這是高尚的行為,可你留意過嗎,你周圍的人們早已麻木。你說這里不對,說那樣不行,多少人不喜歡聽,他們的表現(xiàn)是,自動進入一種自我保護程序,然后奮起抵抗真相。馮小剛的《一九四二》為什么賣不過王寶強的傻笑?這就是答案。
說到底,夏榆的表達,永遠都將保留一種礦工氣質(zhì)。從地下最深處掘出來的東西,說不上寶貴和漂亮,但它們總歸會在某個不知道的地方暗暗燃燒,暗暗釋放能量。
一百三十頁,出現(xiàn)一個費虹。費虹是 “我”的外甥,開別人的車撞車后,無力賠償,遭遇訛詐,被迫逃亡。與唐卡和陸游相比,費虹的逃亡,最具真實感。貧困,平庸,對費虹而言,生活就是望不到盡頭的重復(fù),突然來了一個車禍,命運就此改變。
那么,“我”能為費虹做些什么?什么也做不了。面對這樣具體而微的災(zāi)禍與苦痛,我所有的精神堅守,都顯得那么蒼白無力。我對列儂的熱愛,我對庫爾特·馮內(nèi)古特的崇拜,可能給我慰藉,卻對警察與黑社會不起作用。往往就在這樣的時候,我們不得不承認,自己陷入了精神危機。
陸游的精神危機,可能與此相似。夏榆說,是真相毀了陸游,我倒覺得,陸游是在自毀。生存的殘酷,千百年來沒有什么根本性的改變,估計千百年后也將一樣糟糕。早年間是老虎吃人,然后是人吃人,今天則是污水與絕癥吃人。這才是更大的真相,陸游肯不肯像費虹一樣去面對?
夏榆不屬于才氣型作家,而是用功極深,一名合格的礦工是怎么做事的?勤奮永遠值得敬佩,但對于天才的靈光一現(xiàn),永遠都無原則膜拜。這是我們與夏榆共同的宿命,誰都不會浪費時間去抱怨的。
臺灣出版人安初民評論夏榆的小說:當現(xiàn)實與虛構(gòu)不斷交替變奏時,在救贖與完成之間,可能吶喊的是更為巨大的困惑。的確,夏榆的抽屜里和手掌里,都沒有答案,他最終還是困惑的,可是,在我們中間,又有誰不是困惑的呢?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80202854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