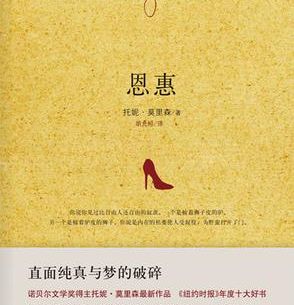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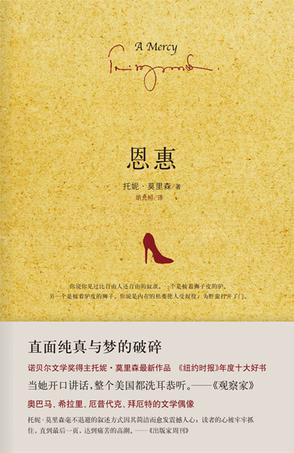
作者: (美)托妮·莫里森
譯者: 胡允桓
出版社: 南海出版公司
by黃夏
初讀《恩惠》,其脈絡(luò)不清、條理不明的敘述方式,碎片化、斷裂化的故事情節(jié),使人不由聯(lián)想起威廉·福克納的《我彌留之際》。事實(shí)上,兩書確有許多相似處,除多聲部有限視角、大量使用意識流等敘述技巧,《恩惠》也兼具《我彌留之際》的故事架構(gòu)和怪誕邪門的史詩風(fēng)格:《我彌留之際》講述丈夫率全家將妻子的遺體運(yùn)回家鄉(xiāng)安葬的苦難歷程,《恩惠》則講述女仆獨(dú)力承擔(dān)起全家的期望外出尋醫(yī)拯救垂死女主人的苦難歷程。兩書皆有一種酒神狄俄尼索斯那種狂歡、瘋癲、諧謔的韻味,它們唯一的區(qū)別在于曲調(diào)大相徑庭:《我彌留之際》是個由悲劇搭建起來的喜劇,而《恩惠》則像一顆糖衣炮彈,大團(tuán)圓的甜蜜之中醞釀著致命的苦澀。
故事由四個身份背景迥異的女人講述,在外人眼里,她們是白人女主人和三個膚色不一的女仆,而在家中,她們的關(guān)系則要微妙復(fù)雜得多。十七世紀(jì)九十年代的北美:三教九流匯聚一地,宗教信仰與傳說迷信難分難解,本土習(xí)俗與舶來思想你爭我奪,種族融合與沖突此起彼伏,時代巨變中 的“家”:因男主人早逝無嗣,這一干女人便形成一個“共同體”,有趨同的利益,也有嚴(yán)重的分歧,四個意亂情迷(黑人佛羅倫斯)、心如死灰(女主人麗貝卡)、心智未開(混血兒“悲哀”)、忠心聰敏(印第安土著莉娜)的女人,串起瑣碎、割裂、主觀因而也是極其情緒化的故事。讀她們的故事,似秉燭走入一個暗 室,燭光照到哪兒,哪兒便映出扭曲的光彩,而未見光的地方,則是一個個同樣扭曲的陰影。她們各自關(guān)于苦難的敘述往往直抵讀者肺腑,卻無法在彼此間形成共 鳴,這恰恰是反對話語霸權(quán)的莫里森在書中制造的最大悖謬,話語“自由”地傾瀉而出,卻又失落得幾近無語般沒有任何意義。共同的苦難不僅沒有使四個女人生發(fā) 出“同是天涯淪落人”的貼心感,反而使之愈行愈遠(yuǎn),為“共同體”的解體埋下了伏筆。
我們無法指望通過她們的視角來讀出這個“家”是因何崩潰的。固然,像莉娜這樣的智慧堅(jiān)強(qiáng)型女性以后將變身如《百年孤獨(dú)》之類的家族小說中向子孫們(讀者們)追溯家史的老祖母,但她們能講故事卻未必能講“前 因”。同話語權(quán)爭執(zhí)所造成的歧義一樣,她們的講述通常把故事神秘化、傳奇化了。故事的核心依然缺位于四個女人占了絕大多數(shù)篇幅的講述中。
所幸,我們從莫里森在書末安排的三個局外人的故事中獲得了一些啟示。特別是佛羅倫斯的媽媽,自述當(dāng)年將女兒賣(換)給主人的苦衷,她將之作為上帝賜予的、改變女兒命運(yùn)的“恩惠”。事實(shí)上,這也是一個代價極大的輪盤賭。平心而論,這一局賭得還不錯,但人生何嘗不是處處是賭局,誰能保證穩(wěn)賺不賠?而這與佛羅倫斯因失落了母愛而極度渴望關(guān)愛、幾近瘋魔的欲念,形成強(qiáng)烈的對應(yīng)。而書中其他人,如麗貝卡將從天堂跌落塵世的生活大逆轉(zhuǎn)歸咎于丈夫的溫柔慈善,“悲哀”恢復(fù) 理智卻成為一個冷酷自私的實(shí)用主義者,可以說都是在為“恩惠”付出靈魂的代價。整個故事仿佛一個循環(huán),人世的輪回只是為了重新回歸孽緣,所有的打拼到頭來換得的是一個壯麗的崩潰。《恩惠》并未直接控訴奴隸制的罪惡,而將批判內(nèi)化為對人性難言隱衷的探究,我們顯見人性如何在扭曲的制度下失色和枯萎,只是這一次,莫里森選擇從大寫的個體出發(fā),提出了為日后所有人刻骨銘心的深刻教訓(xùn):“接受支配他人的權(quán)力是一件難事;強(qiáng)行奪取支配他人的權(quán)力是一件錯事;把自我的支配權(quán)交給他人是一件邪惡的事。”這自然是莫里森穿越時空的箴言。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80202854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