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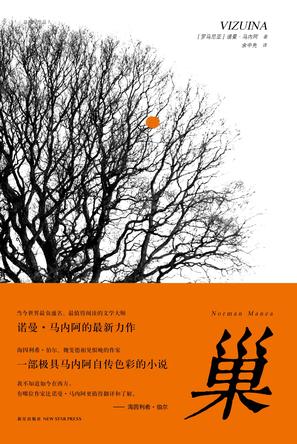
作者: 【羅馬尼亞】諾曼·馬內(nèi)阿
譯者: 余中先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by李靜睿
盡管諾曼·馬內(nèi)阿早就得過美國(guó)全國(guó)猶太圖書獎(jiǎng)和麥克阿瑟天才獎(jiǎng),并且被視為羅馬尼亞語寫作中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的作家,但他卻依然是一個(gè)“異國(guó)情調(diào)的啞角”。這個(gè)詞正是來自他這本書,“彼得·加什帕爾意識(shí)到,在自由的狂歡節(jié)中,自己是一個(gè)異國(guó)情調(diào)的啞角。”
2011年8月,馬內(nèi)阿在某個(gè)網(wǎng)站上發(fā)表了一篇文章,名為Against Simplification(反抗簡(jiǎn)單化),文章讀起來有點(diǎn)心酸,馬內(nèi)阿抱怨美國(guó)人是“簡(jiǎn)單化的天才”,但是現(xiàn)在這種簡(jiǎn)單化卻成為趨勢(shì),像藍(lán)色牛仔褲一樣攻占全球。他用意大利作家Claudio Magris的作品Blinding舉例,這本在歐洲獲得極高聲譽(yù)的小說很久后才被翻譯到美國(guó),而且從未收獲它應(yīng)得的關(guān)注,這也并不是孤例。馬內(nèi)阿引用了一個(gè)聯(lián)合國(guó)報(bào)告數(shù)據(jù)說,美國(guó)的翻譯文學(xué)數(shù)量等同于希臘,而后者只有美國(guó)面積的十分之一。
如果以是否簡(jiǎn)單化為文學(xué)劃分等級(jí),馬內(nèi)阿可以放心的是,《巢》即使放在歐洲語境下也可以打上四顆星。同樣是從納粹集中營(yíng)中幸存的猶太作家,他似乎比2002年諾獎(jiǎng)得主、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伊姆雷更難以脫離往日的陰影,也更致力于繁復(fù),雖然凱爾泰斯已經(jīng)被公認(rèn)為是托馬斯·曼式深刻的繼承人。《巢》有一個(gè)甚至算不上故事的故事線:三代羅馬尼亞的流亡知識(shí)分子,都從社會(huì)主義的“法定幸福”中來到美國(guó),第一代是大師迪瑪。第二代是迪瑪?shù)牡茏用缀諆?nèi)阿·帕拉德教授,后來被暗殺于廁所隔間,案件始終沒有偵破。第三代是小說的主人公彼得·加什帕爾。還有一個(gè)主角是介于第二代和第三代之間的戈拉教授,戈拉教授在妻子露的家族幫助下才能拿到護(hù)照,但是露卻并沒有跟他來到美國(guó),反而是幾年后跟著加什帕爾一起來,露是加什帕爾的表姐,后來成為了情人,而戈拉的前前妻愛娃則是加什帕爾的母親。總而言之,馬內(nèi)阿成功創(chuàng)造了他的復(fù)雜:一團(tuán)亂麻。
《巢》有濃厚的自傳性質(zhì),雖然馬內(nèi)阿到底把自己棲身于戈拉還是加什帕爾無法辨清,書中的大師迪瑪卻明顯以米爾恰·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為原型。伊利亞德是著名的羅馬尼亞籍學(xué)者、宗教史專家,1956年來到美國(guó),他著名的《宗教思想史》影響巨大。在伊利亞德去世后第五年,美國(guó)《新共和》雜志刊登了一篇揭露伊利亞德歷史的文章,作者正是馬內(nèi)阿,文中提到他曾經(jīng)在30年代支持過鐵衛(wèi)軍,這是極右的羅馬尼亞民族主義運(yùn)動(dòng)組織,其成員叫軍團(tuán)兵,鐵衛(wèi)軍雖然在1941年就被取締,但它被認(rèn)為是后來齊奧塞斯庫(kù)上臺(tái)掌權(quán)的前期功臣。《巢》中米赫內(nèi)阿·帕拉德教授的原型則是伊利亞德的弟子約·貝特魯·古利阿努教授,1991年5月21日古利阿努在芝加哥大學(xué)內(nèi)被槍殺,死于學(xué)院的教員洗手間內(nèi),子彈從相鄰的小隔間射進(jìn)了坐在馬桶上的古利阿努的腦袋,據(jù)說死因是古利阿努當(dāng)時(shí)正準(zhǔn)備審閱其導(dǎo)師伊利亞德早年的政治背景,而芝加哥有不少熱衷于鐵衛(wèi)軍的流亡羅馬尼亞人。
想要更好地理解《巢》,必須和馬內(nèi)阿的另外一部作品《流氓的歸來》互相映照,后者被認(rèn)為是非虛構(gòu)類的自傳作品,但事實(shí)上它和《巢》擁有一樣的內(nèi)核,兩本書的背景都在紐約和羅馬尼亞之間切換,《流氓的歸來》主要寫羅馬尼亞,《巢》主要寫紐約,可以把它視為《流氓的歸來》的續(xù)集,伊利亞德和古利阿努的故事在《流》中也有詳細(xì)敘述,《巢》里則不過改換了人名而已。
在《巢》的故事里,后半部的重要線索是加什帕爾為帕拉德的被殺寫了一篇文章,然后就接收到了匿名的明信片,上面引用了博爾赫斯小說《死亡與羅盤》中的一段話:“下回我會(huì)殺了你,我答應(yīng)給你一個(gè)由唯一一根看不見的、無盡頭的直線造成的迷宮。”這被認(rèn)為是一種死亡威脅,因而驚動(dòng)了學(xué)校校警和FBI。而在《流氓的歸來》里,古利阿努的謀殺案發(fā)生時(shí),馬內(nèi)阿正好在《新共和》上發(fā)表了上述和伊利亞德相關(guān)的文章,F(xiàn)BI找到了他,告誡他在與羅馬尼亞人及其他人接觸時(shí)要小心。
過多糾結(jié)于《巢》那雜亂無章的情節(jié)也許意義不大,馬內(nèi)阿留下了很多他自己也不見得能一一解答的疑團(tuán):加什帕爾為什么無故失蹤?那封死亡威脅信難道真的只是一個(gè)來自薩拉熱窩的女學(xué)生的行為藝術(shù)實(shí)驗(yàn)?小說里的“我”到底是另外一個(gè)羅馬尼亞流亡知識(shí)分子還是戈拉的身外化身,露最后為什么和“我”在一起?這是一本由各種閃光碎片支撐起來的小說,故事和人物都被他的語言逼到了墻角,顯得模糊不清、無路可走。
書里一個(gè)來自?shī)W德薩的出租車司機(jī)說了一段話:“我們?nèi)荚谧兂傻怯浱?hào)。不是烙在胳膊上的印,就像在奧斯威辛那樣,而是在一個(gè)信用卡上。Visa卡、萬事達(dá)卡、白金卡。社會(huì)保險(xiǎn)卡、醫(yī)療卡、地鐵卡。居留證。外來人居住證0298號(hào)。加什帕爾的號(hào)。”它大致可以概括馬內(nèi)阿或者說書里這些流亡知識(shí)分子的痛苦:流亡之前,他們被體制的牢籠所困;流亡之后,他們被自由的虛空所困。這種永遠(yuǎn)的邊緣感已經(jīng)說不清楚是承受懲罰還是自由選擇,所以《流氓的歸來》里引用羅馬尼亞流亡者齊奧朗的話:“遭排斥是我們唯一擁有的尊嚴(yán)。”齊奧朗還說:“你與祖國(guó)對(duì)峙,是出于對(duì)絕望的需要,出于對(duì)更加不幸的渴望。”在《巢》的故事里,“祖國(guó)”也可以替換為“美國(guó)”。
馬內(nèi)阿在不同的書里多次寫到自己的父親,在集中營(yíng)中父親驚恐地發(fā)現(xiàn)自己潔白的襯衫領(lǐng)子上有一只虱子,“這樣的生活不值得過下去”,但是母親向他保證,他會(huì)重新穿上漿得硬挺挺的白襯衫。然后到了1958年,他又坐上了共產(chǎn)黨的牢,穿上慘不忍睹的制服,原因是沒有當(dāng)場(chǎng)支付兩公斤肉錢,父親被判刑五年。當(dāng)然,他的父親沒有來到美國(guó),但是從馬內(nèi)阿的命運(yùn)也許可以想象這一幕如果發(fā)生,父親也不見得會(huì)覺得“這樣的生活值得活下去”,即使他能保證自己穿上漿得硬挺挺的白襯衫,但生活又不能僅僅是漿得硬挺挺的白襯衫。
諾曼·馬內(nèi)阿的書里總是混雜著想要忘記的尊嚴(yán)和不能忘記的痛苦,因?yàn)樗娜松褪侨绱恕K鋵?shí)很早就意識(shí)到羅馬尼亞社會(huì)主義新政權(quán)對(duì)自己的不友好,但在其他猶太人陸陸續(xù)續(xù)遞報(bào)告申請(qǐng)去以色列時(shí),馬內(nèi)阿拒絕以“受害者”自居的逃避行為,因?yàn)?ldquo;我對(duì)一切改變命運(yùn)的幼稚努力都表示懷疑,在我看來,對(duì)我們不夠完美的、短暫的現(xiàn)狀承擔(dān)起責(zé)任,并予以理解,更勝于僅僅作出地理方位的調(diào)整這種改變”。《巢》里也寫過,加什帕爾要求學(xué)校刪除關(guān)于他是一個(gè)大屠殺幸存者的介紹,因?yàn)樵诩彝ブ羞@是一個(gè)禁忌的詞語,這代表著侮辱,“我父親的一個(gè)朋友,從奧斯維辛回來,請(qǐng)一個(gè)醫(yī)生為他去除胳膊上的一塊皮膚,那上面文著他的囚徒號(hào)碼。這是他回來后做的第一件事!他從來就不提及那些年。”馬內(nèi)阿說,“我既不想要痕跡,也不想要回憶。”(這是《巢》的最后一段),但他顯然失敗了,他的書里永遠(yuǎn)如此:一個(gè)異國(guó)情調(diào)的啞角說出的話語,充滿痕跡,充滿回憶。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802028547號(h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