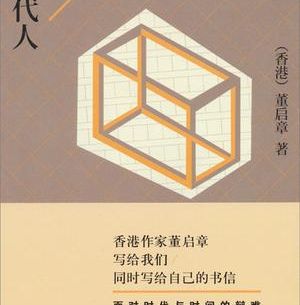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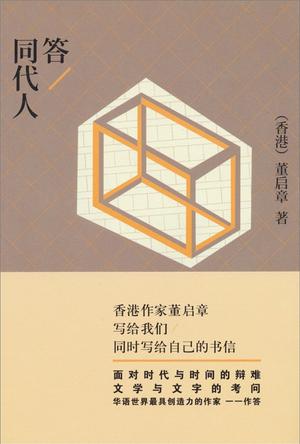
作者: 董啟章
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撰文:btr
從482頁的《天工開物·栩栩如真》、上下合計(jì)共886頁的《時(shí)間繁史·啞瓷之光》到710頁的《物種源史·貝貝重生之學(xué)習(xí)年代》,香港作家董啟章從2005年起潛心構(gòu)筑的巨著“自然史三部曲”眼看就要完成,但自2010年出版《學(xué)習(xí)年代(上)》迄今已近三年,完結(jié)篇卻遲遲不見 蹤影。
2013年3月,當(dāng)董啟章又一次拿起筆時(shí),這完結(jié)篇悄然起了變化:“自然史三部曲”并未虎頭蛇尾,而是——照小說里道人的說法,“蛇尾又生出虎頭來”。這一次,董啟章意在“虎蛇一體,首尾相應(yīng)”。發(fā)表于4月底出版的《天南》文學(xué)雙月刊的4萬字,便是其新作《<自然史>前言:美德》之前奏。
我們的采訪約在香港九龍?zhí)劣忠怀且婚g叫作“rice paper”的越南餐廳。餐廳旁有一個(gè)大型室內(nèi)溜冰場。董啟章的短 篇小說《溜冰場上的北野武》寫的就是這里。對于董啟章來說,小說世界就像這個(gè)溜冰場,是一個(gè)劇場般的存在;而作家的職責(zé),正如費(fèi)爾南多·佩索阿所言,是 “把自己的心化作舞臺”,搭建一座文學(xué)里的劇場。在這劇場里,懷疑將被懸置,人物將在一部部小說里重生,如同董啟章筆下的貝貝變成栩栩、變成恩恩、變成啞 瓷,在《美德》里又變成了維真尼亞。
|訪談|
問=btr
答=董啟章
問:《美德》與你此前的長篇在風(fēng)格和技法上會有哪些不同?
答: 有分別,但也有相似的地方。《美德》是非常濃縮的,因?yàn)橐押芏嗍虑椤⒑芏鄨雒妗⒑芏嗳宋餄饪s在一個(gè)幾萬字的空間里面,所以里面有差不多100個(gè)名字—— 100個(gè)名字對于一個(gè)長篇來說不算很多,但在4萬字里面密度就很高。所以我也擔(dān)心可讀性(笑),有一段就是名字、名字、名字,把名字排列出來似的,以前我 沒有這樣寫過,正因?yàn)橐獙戇@樣一個(gè)前奏,才用了這個(gè)方法,不是一個(gè)正宗的、寫小說的方法。但我也不是從來沒有試過——我寫過一個(gè)短篇《溜冰場上的北野 武》,寫的就是在一段短暫的時(shí)間內(nèi)在溜冰場邊觀察里面發(fā)生的事和孤獨(dú)的人們。在《美德》里,有一段是寫一個(gè)咖啡店,主角是在咖啡店里工作的經(jīng)理,他觀察咖 啡店里的人,而這些人都是在長篇里面會出現(xiàn)的。這是一個(gè)群像,有一大群人的面相在里面。
問:這群像應(yīng)該來自于你在日常生活中對于香港社會的觀察。你對香港有著怎樣的感情,在你的寫作中香港又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答: 很難簡單說。基本上,只能通過小說來表達(dá)。因?yàn)榧偃缥液唵蔚卣f一兩個(gè)詞語,說我對香港的感覺怎樣,都會是簡化的,所以你看我一直都是在寫香港,你也可以 說,除了這些人物,香港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gè)主角。我從小生活在這個(gè)地方,我的每一部分都跟香港是分不開的,所以很自然,寫作時(shí)我的意識、我的內(nèi)在和外在 都有這個(gè)成分。內(nèi)在就是:我是一個(gè)在香港長大的人;外在就是:我長大的時(shí)候,面對的就是這個(gè)叫“香港”的社會。所以,從內(nèi)到外都會不自覺地去反射這樣一種狀態(tài)。
問:對于一個(gè)生長于此的人,會不會看慣了周遭一切?為什么你能持續(xù)保持一種創(chuàng)作的沖動,而且創(chuàng)作了如此大量的作品?
答: 對,為什么沒有看慣呢?其實(shí)香港人,不單是我,對于自己作為香港人的自我意識是很強(qiáng)的,這可能是從我這一代人開始的。為什么一個(gè)習(xí)慣的地方,會常常在意識 里出現(xiàn)呢,我想這是因?yàn)橄愀圻@個(gè)地方很小,很容易相對于其它地方而存在。這種“相對感”是非常強(qiáng)烈的,相對于中國大陸,相對于西方,正是這種“相對感”讓 我們看到邊界。假設(shè)在內(nèi)地城市,在一個(gè)城市長大的人都有一種感情,像上海人對于上海,廣州人對于廣州;但與香港比,那種邊界感就沒有那么強(qiáng)烈。當(dāng)邊界劃得 很明顯時(shí),就會越來越自覺這樣的存在。
問:同樣寫香港,你為什么更多地選擇小說這一體裁?
答:雖然大家都在尋找、或者說以某種身份和立場說話,但背后這個(gè)身份也是慢慢建立起來的,不是一個(gè)非常簡單的、本質(zhì)的東西。歷史是什么,也是這樣一個(gè)建構(gòu)的東西。而這與小說是很相像的。所以小說里的所謂“虛構(gòu)”,在一般意義上與現(xiàn)實(shí)可以分得很開,說“虛構(gòu)”的就是假的,但小說里也可以建構(gòu)歷史,我一直覺得歷史和小說有相通的地方,用小說這種體裁也更能夠看清建構(gòu)的過程中發(fā)生的事。
問:但歷史的書寫有一種權(quán)威性?
答:從這個(gè)角度看,小說是相反的。小說沒有這種權(quán) 威性,小說都是從個(gè)人、從比較邊緣的角度寫出來的。相通之處是,兩者都有一種建構(gòu)。但歷史的建構(gòu)是非常強(qiáng)大的,作為一種權(quán)威;但小說的建構(gòu)是弱小的,通過 個(gè)別的寫作者,有相似、也有相對。事實(shí)上,每一個(gè)人都可以有自己角度的歷史。
問:那么從寫作風(fēng)格的角度看,你受到的影響主要來源于哪里?
答:長句子的話,普魯斯特的影響很大。從想象力方面來說,受卡爾維諾的影響多一點(diǎn)。香港作家方面,大的影響來自于西西、也斯。西西主要是把香港這個(gè)城市作為寫作對象這一點(diǎn),思維方法則受了一些也斯的影響。
問:粵語作為一種非常口語化的語言,與用作寫作的語言,在你的小說里通常會很舒服地融合在一起。你如何看待日常的口語與寫作的語言之間的關(guān)系?
答: 是比較難融合在一起的,因?yàn)椴顒e很大。我也是因?yàn)椴粩噙@樣去寫,才慢慢找到一種比較自然、也不太自覺的方式。在香港寫作有一點(diǎn)很奇怪,我們寫的與我們講的基本上是不一樣的兩回事,寫作從一開始就是一個(gè)很書面的、很不自然的事,是一個(gè)構(gòu)造出來的東西,所以不會去追求寫得非常自然,反而會覺得既然是一種構(gòu)筑, 那就盡量去用不同的方法建構(gòu)吧。
問:你的好多小說里、包括《美德》里面都有一個(gè)小說家,或者說,您的小說經(jīng)常是meta-fiction,指涉自身。您為什么會做這樣的安排?
答: 事實(shí)上,我并不是非常關(guān)心meta-fiction這個(gè)問題,我反而覺得很有需要去探討的是所謂“真”與“假”的關(guān)系。即,在寫作這個(gè)行為里面,什么是 真,什么是假。我寫得很真,讀者讀得時(shí)候覺得很真,這是怎么一回事。那你“寫得很假”又是怎么一回事。我本來是在虛構(gòu),但是我寫一個(gè)角色,他是一個(gè)作家, 讓人覺得與我有關(guān)系的時(shí)候,這樣的做法是真還是假?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探討“寫作”這個(gè)行為本身,或所有藝術(shù)創(chuàng)作行為的背后。這是個(gè)本質(zhì)的問 題,所有藝術(shù)都在問這個(gè)問題。
問:你認(rèn)為“真”與“假”的邊界在哪里?
答:邊界不在版權(quán)頁上。讀者讀一個(gè)小說,他知道這是假的,但他慢慢進(jìn)入這個(gè)世界,而且覺得里面的東西很真。并不是因?yàn)橛X得作者寫得很好,所以才很真;而是覺得它與真實(shí)生活中發(fā)生的某些事情真的有關(guān)系。這很難說,可能一說出來就不是我本來想說的東西。
問:類似于看電影的時(shí)候?qū)⒆约捍虢巧?/strong>
答: 嗯,但那是暫時(shí)的。我在剛寫的《體育時(shí)期》再版序言里談及這點(diǎn),最近香港有個(gè)劇團(tuán)將之改編成舞臺劇,再版時(shí)也加進(jìn)了一些關(guān)于演出及劇團(tuán)的文章。寫小說,既 不是要把你“騙倒”,也不是要讓你覺得“它是假的”,而是要在兩者之間——就是你明明知道它是假的,但是你也不能抗拒,會投入其中,暫時(shí)覺得它是真的。英國詩人柯勒律治(Coleridge)所說的“suspension of disbelief”就說得非常巧妙,所謂暫停我們的“不相信”,但前提就是 “我們是不相信的”,只是我們暫停這個(gè)懷疑,暫時(shí)去相信它。是先要有這個(gè)“不相信”,然后才有“信”。這是一個(gè)非常辯證的關(guān)系。我要寫的就是這樣一種東 西,我覺得“真”與“假”的邊緣狀態(tài)是非常奇妙的。有讀者告訴我,他從十幾歲中學(xué)時(shí)代就開始看我的小說,看得太沉迷了,他覺得變成了我的人物,那我就有點(diǎn) 擔(dān)心,可能對他會有不良影響。但就是會有這樣的事情,那真和假的邊界又在哪里呢,很難說。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80202854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