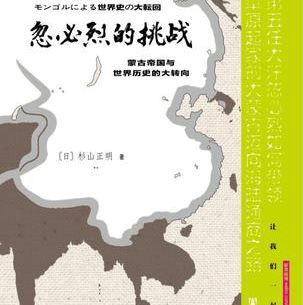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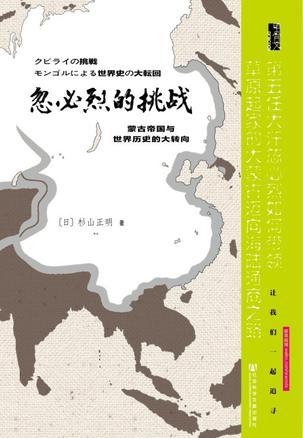
《忽必烈的挑戰(zhàn)》
(日)衫山正名
周俊宇 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林彌生/文
在《白銀資本》和《大分流》這樣極具顛覆性的著作產(chǎn)生之后,無論讀到何種強調(diào)東方世界作用的文字都不應(yīng)該覺得驚奇。這類作品告訴我們,我們曾擁有比歐洲世界更多的財富,也曾擁有足以和西歐相抗衡的經(jīng)濟實力,只是在1800年之后才逐漸和他們拉開差距。為此,我們曾將近代的磨難歸咎于乾隆的短視,也曾埋怨“西方的強盜行徑”,但越來越多的研究告訴我們,事實遠不是我們所以為的那樣簡單而富有悲劇意味。因此,黃仁宇會將近代問題歸因于中國傳統(tǒng)中“數(shù)目字管理”的缺乏,黃宗智則將關(guān)注點放在農(nóng)民的生計上。他們也許都未曾想過,假如現(xiàn)代歷史不是以我們所知的那樣出現(xiàn),一切又將怎樣?
在沃勒斯坦的《現(xiàn)代世界體系》那里,一個由大航海時代開啟閘門的、以西歐為中心的生產(chǎn)與流通體系的建立,是現(xiàn)代的基本特征,也是世界成為一體的基礎(chǔ)。日本學者杉山正明則針對此觀點,認為忽必烈建立的元帝國已經(jīng)率先建立了一個世界體系,將歐亞大陸為中心的廣大地域組織成了一個經(jīng)貿(mào)的整體。他在《忽必烈的挑戰(zhàn)》中就元帝國的產(chǎn)生及其對世界性通商的影響展開了論述。作為該書的核心論題,他從都城營建、征服南宋、海上稱雄、商路建設(shè)、商業(yè)管理、貨幣改革等方面試圖論證以元朝為中心的世界商貿(mào)體系的存在。當我們還在爭論元朝究竟是北族政權(quán)還是中原政權(quán)的時候,他的眼界已經(jīng)超越了“華夷之辨”這個層次,開始關(guān)注世界史領(lǐng)域中的蒙古歷史,這正是《忽必烈的挑戰(zhàn)》最大的價值所在。
這個蒙古世界體系為何能夠產(chǎn)生?杉山氏認為,直接的原因就是忽必烈鞏固汗位的需要。在他的解釋里,忽必烈在汗位之爭中完全是篡權(quán)者的形象,為了獲得各汗國的認可,他需要像以前的蒙古大汗一樣,不斷地為他們提供財富。最終,他建立了一個以“首都圈”為核心,橫跨游牧世界與農(nóng)耕世界的大帝國,將蒙古的軍事力量、中原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和穆斯林的商業(yè)文明結(jié)合起來,讓蒙古在世界歷史上從征服者轉(zhuǎn)型為統(tǒng)治者與經(jīng)營者。可以說,杉山所說的具體史實,我們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但我們運用這些事實去搭建的解釋系統(tǒng)則與他截然不同。僅就軍事、經(jīng)濟與商業(yè)的結(jié)合而言,有時被歸納為元朝迅速走向腐化的原因,有時被概括為“內(nèi)北國而外中國”,而忽必烈開創(chuàng)的“兩京制”,也被解讀為“草原本位”或“草原中心”。杉山則將這些事實與汗位爭奪戰(zhàn)聯(lián)系起來,為我們描繪出一個世界體系的雛形。
以往我們說到元明時代中國對“世界”的作用時,常掛在嘴邊的是馬可·波羅的游記和鄭和的航海旅程,但對二者的意義則很難做太多的闡發(fā),因為看上去它們和后來的世界并無太多關(guān)系。杉山氏則告訴我們,這兩個案例都只是忽必烈所搭建的世界體系中的產(chǎn)物,是這個體系下的細節(jié)。這樣一來,我們的世界形象一下子偉岸起來——盡管杉山同時也提到,元帝國并不是一個“中華王朝”。
有關(guān)元朝是否具有中國屬性這一問題,歷來就存在爭論。而在明初編纂的《元史》中,忽必烈的即位詔書完全是中原皇帝的做派,而且忽必烈本人對漢地文化與制度的興趣也是讀史者所習知的。以往由于文化本位觀的影響,常有將元朝摒棄于中國歷史之外的觀點出現(xiàn),但元帝國所具有的濃厚的中原氣息總是不可否認的。站在漢文化傳統(tǒng)的立場上,我們可以說元朝存在“漢化遲滯”的現(xiàn)象,而若從游牧文明與農(nóng)耕文明交融的角度去觀察,我們也可以說,日漸增強的中原色彩,讓元朝原本鮮明的征服王朝特征逐漸褪去。
王朝屬性問題,對世界體系的有無并不存在支持或否定作用,值得思考的問題在于,如果真的在忽必烈個人的政治需求下建立了一個以蒙古為主導、以元帝國為核心的世界體系,那么為什么忽必烈采用如此復雜的方式,而不是更為簡便的其他手段來供給各汗國財富,比如掠奪戰(zhàn)爭或高額征稅?杉山筆下的忽必烈,更像是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家筆下的理性經(jīng)濟個體,一個指揮全局的總設(shè)計師,而非一個馬背上的皇帝。他和他身邊的“策士”們居然能夠動用各種手段,比如杉山所強調(diào)的蒙古鐵騎、漢地物產(chǎn)與穆斯林商團,并大費周章地利用運河、開辟海航、改革幣制,以求在商路所及之處獲得財富,并維持元帝國在這個貿(mào)易體系中的地位,未免有點不可思議。即便是最精明的阿拉伯商人,也不可能提出這樣一整套的政策性與制度性方案,說得極端一些,即便是現(xiàn)代中國,通過一代人的努力建立一個如杉山所說的世界體系——哪怕只是第三世界范圍內(nèi)的——也不可能,何況是忽必烈?
另外的一個問題是,如果忽必烈因為個人原因建立了一個世界體系,那么在以后的元朝皇帝那里,令它能夠維持下去的動力又是什么?在前現(xiàn)代的王朝中,決定一種與政權(quán)關(guān)系密切的事物是否能夠存在的,更多時候是政策,以及政策制定者的態(tài)度,而非一個并不存在的、能夠自己運行的制度。元朝皇帝的更換頻率極快,除了忽必烈和末代皇帝元順帝,其他人在位時間少則一年、多則十幾年,且政爭不斷、政策變動頻繁,所謂的世界體系如果真的存在,其持續(xù)存在的政策性或曰政治性原因在哪里?杉山將蒙古世界體系的崩壞起始時間定在一三三零年代,認為蒙古帝國聯(lián)合體從這時開始瓦解,而對元朝內(nèi)部的皇位更替與政策變化所能產(chǎn)生的影響則未置一詞。
在另一個地方,杉山強調(diào)了元帝國死刑判決數(shù)量極少的情況,似乎將之作為可贊揚的事情,而這種政策性現(xiàn)象,正是學者們將元朝看做“罪犯天堂”的重要論據(jù):伴隨著低死刑率的,并不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而是高犯罪率。這種有些天真的誤解,不知是否和忽視元朝政治動態(tài)有關(guān)。
在對蒙古的世界體系進行評估時,杉山有將這一“世界體系”產(chǎn)生的影響放大的做法。他以“大明可汗”為論據(jù),認為這就是世界體系的殘留影響。不過,在邦交方面,沿用前朝舊稱稍加改作的形式,在新王朝建立之初時往往會出現(xiàn),而且即便這稱號被長期使用,比如唐代的“天可汗”,所體現(xiàn)的也只是中原皇帝在宗藩關(guān)系上的主導身份——周邊各邦共同擁戴的“可汗”,而非某個跨國體系的主導者。
另外一個將“世界體系”作用放大的例子是對明成祖朱棣的評價。杉山認為明成祖遷都北京、對北元進行征伐之舉就是想要“重現(xiàn)大元汗國”。明成祖遷都與北伐的目的,吳晗就曾做過研究,其他學者也有過相關(guān)論述,其目的應(yīng)該不是重現(xiàn)元帝國,而是盡可能地消滅元朝的殘余勢力。杉山又以明成祖的身世傳說為例,認為人們傳說他是元順帝之子并非沒有原因,正是因為他想要建立元朝那樣的大帝國才會如此。如果我們注意另一個有趣的傳說就會發(fā)現(xiàn),這個觀點實難成立。在傳說中,元順帝并非蒙古后裔,而是宋恭帝的私生子,這和秦始皇的身世傳說有些類似,目的都在于否定其繼位的合法性并貶低其出身。而明成祖的身世問題與此相類似,但一定程度上是與其偽造身世、令后人遐想有關(guān)。
既然所謂蒙古的世界體系是否存在非常令人生疑,其閱讀意義又在哪里?在我看來,這是東亞學者在歐美學術(shù)范式下對其自身歷史的審視和對現(xiàn)代起源的解釋。
現(xiàn)代世界究竟為何出現(xiàn),以怎樣的形式出現(xiàn),是很多西方學者探討的論題。卡爾·馬克思、馬克斯·韋伯、哈貝馬斯、沃勒斯坦等都從自己的角度提出了現(xiàn)代世界產(chǎn)生的原因。對這些理論,東亞學者也日漸在反思中進行回應(yīng),比如余英時就以《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來回應(yīng)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同樣,杉山氏也以《忽必烈的挑戰(zhàn)》來回應(yīng)沃勒斯坦的《現(xiàn)代世界體系》。余英時通過研究中國宗教與儒家觀念在中唐以后的世俗轉(zhuǎn)向,對所謂“商人倫理”進行了剖析,使用韋伯的基本理論對中國前現(xiàn)代社會晚期的歷史進行考察。杉山在研究取向上和余英時極為相近,使用沃勒斯坦對世界體系的基本界定,從東亞世界尋找與這一學說相契合的因素,再以此對沃勒斯坦的觀點進行反擊,正是所謂“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他們的研究都沒有方法論的創(chuàng)見,只有將東亞事例與西方理論結(jié)合的試驗。這種試驗本身并不成功,而且都有將案例抽象化和誤讀的表現(xiàn),但他們也通過這種試驗證明了一個問題:在明顯從歐洲經(jīng)驗出發(fā),對現(xiàn)代性進行解釋的理論下,試圖以東亞歷史去迎合這些理論的工作本身也是對歐洲經(jīng)驗的一種默認,且只能使對東亞歷史的解釋落入歐洲中心的陷阱。現(xiàn)代國家從歐洲出現(xiàn),是一種歷史現(xiàn)象,而且是一種偶發(fā)性現(xiàn)象。偶發(fā)性就意味著歐洲出現(xiàn)現(xiàn)代化進程時東亞世界并未出現(xiàn)類似的反應(yīng)。如果一定要在并未發(fā)生的歷史中尋求歐洲經(jīng)驗,無異于緣木求魚。
更重要的是,用東亞歷史去做歐洲經(jīng)驗的注腳,會抹殺東亞歷史本身存在的特征。就以《忽必烈的挑戰(zhàn)》為例,沃勒斯坦所提出的現(xiàn)代世界體系理論是以西歐經(jīng)濟發(fā)展為前提,以海外開拓為動力,以形成中心—邊緣結(jié)構(gòu)的世界體系與現(xiàn)代帝國為結(jié)果的,而在杉山的論述中,忽必烈之所以能夠建立一個蒙古的世界體系,則是以橫跨歐亞大陸的蒙古汗國為基礎(chǔ),以元帝國的各項措施為手段建立起來的,一個強大的前現(xiàn)代帝國的出現(xiàn)不是結(jié)果而是前提,政策性因素也成為非常重要的支撐,這和沃勒斯坦的理論模型本身就存在差異,而杉山本人對此似乎并未特別注意,而是將筆墨更多放在描述蒙古世界體系的輝煌這一點上。也許,重視元帝國本身的特性,重視元帝國、阿拉伯世界及歐亞其他地區(qū)在商貿(mào)交往上的復雜關(guān)系,會發(fā)現(xiàn)一個真正的前現(xiàn)代體系,如果它真的曾經(jīng)存在過。這樣,我們就可以給《白銀資本》和《大分流》寫一個“前傳”,探討大分流時代到來之前的東亞世界。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80202854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