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片來源:圖蟲創(chuàng)意)
姜昊騫/文
“一個(gè)大架仔”
作為一名譯者,“信達(dá)雅”的衡量標(biāo)準(zhǔn)自然是時(shí)常掛在心頭。嚴(yán)復(fù)原本講得很簡(jiǎn)略,“譯事三難:信、達(dá)、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dá),雖譯猶不譯也,則達(dá)尚焉。”按照通常的理解,信就是“準(zhǔn)確”,也就是譯文與原文的意義應(yīng)當(dāng)一致,不能有增減移謬。對(duì)于大部分文本來說,一種樸素的符合論意義觀就足夠翻譯之用了。美國(guó)數(shù)學(xué)家理查德·蒙塔古在上世紀(jì)70年代提出了一種“普遍語法”,用邏輯學(xué)家的形式語言來構(gòu)建自然語言的模型。對(duì)語言哲學(xué)家來說,蒙塔古語法往往用于解釋某一個(gè)具體的語言現(xiàn)象,因此必須要做精確地定義和推導(dǎo)。
對(duì)譯者來說,這套乍看起來過于簡(jiǎn)陋和刻意的模型恰恰是相當(dāng)優(yōu)雅地表達(dá)了我們的樸素直覺:世界由物體組成,詞語指代單個(gè)物體、多個(gè)物體或者物體之間的關(guān)系。于是,一句話翻譯得準(zhǔn)不準(zhǔn),或者說信不信,就看譯文里講到的物體和物體之間的關(guān)系是否與原文對(duì)應(yīng)。以這個(gè)易用且明確的模型為中介,源語言與對(duì)象語言之間可以建立起一座座名為映射的橋梁。我知道這不是現(xiàn)在走通的AI翻譯的模式,但對(duì)人工翻譯來說,蒙塔古語法所代表的意義觀依然是無可替代的底層邏輯。
不過,《龍與獅的對(duì)話:翻譯與馬戛爾尼訪華使團(tuán)》這本書里講述的內(nèi)容卻有一種振聾發(fā)聵的效果,在性質(zhì)上類似于康德從“獨(dú)斷的睡夢(mèng)”中驚醒:上一段描繪的優(yōu)雅模型在一些情況下完全不適用。這種來自歷史的厚重沖擊是哲學(xué)理論難以匹敵的。哲學(xué)理論往往要么針尖繡花,要么九重云霄,要么繞場(chǎng)三周半,總之一個(gè)缺乏慧根的譯者總可以用“這跟我有什么關(guān)系”來打發(f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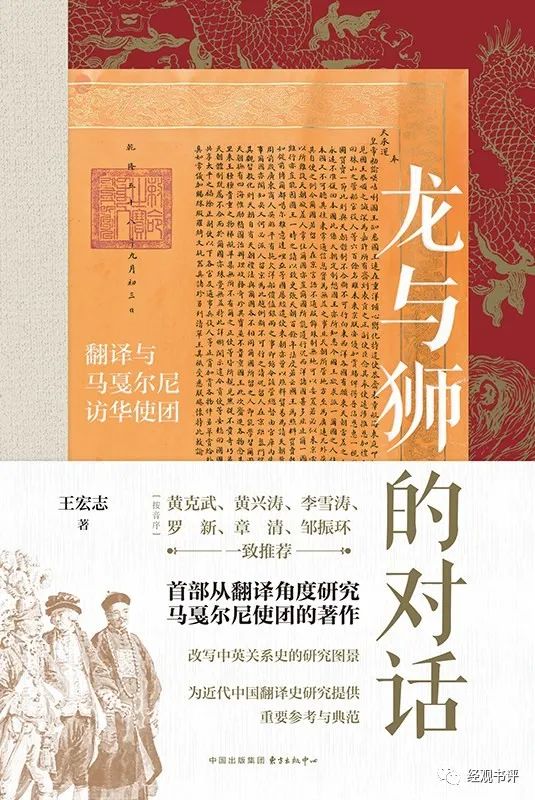
《龍與獅的對(duì)話:
翻譯與馬戛爾尼訪華使團(tuán)》
王宏志 /著
東方出版中心
2023年6月
但就算一個(gè)譯者再愚鈍,讀到這句話時(shí)恐怕也不會(huì)沒有觸動(dòng):“對(duì)于‘布蠟?zāi)岽罄檀蠹?rsquo;這樣的譯法,我們不應(yīng)對(duì)譯者過于苛責(zé)……但從效果上說,這件本來是英使最貴重且寄予厚望,以為一定可以打動(dòng)乾隆的禮品,卻因?yàn)榉g的問題而無法有效地傳達(dá)重要訊息,從馬戛爾尼的角度來看,這是很不理想的。”
我所受的觸動(dòng)主要不在于所謂外交無小事,畢竟我不是英國(guó)使團(tuán)或者滿清朝廷的人,而在于這種例子指出,翻譯中采用的意義模型有時(shí)必須加入新的參數(shù),而一旦加入這些參數(shù),“信”,尤其是“達(dá)”的標(biāo)準(zhǔn)就會(huì)一下子變得混沌起來。當(dāng)然,這并不意味著標(biāo)準(zhǔn)本身消失了,因?yàn)橥鹾曛窘淌诘姆治銮∏≈该髁怂枰a(bǔ)齊的短板——蒙塔古主義譯者從此多了一項(xiàng)需要掌握的判斷技能:何時(shí)用簡(jiǎn)單的符合論模型就夠了,何時(shí)必須切換到復(fù)雜得多的意義模型。接下來,我要結(jié)合馬戛爾尼禮單的例子來略作講述。
馬戛爾尼的目標(biāo)是在平等交往的前提下為中英貿(mào)易爭(zhēng)取便利,為此需要塑造英國(guó)強(qiáng)大,英王崇高的形象,這也正是使團(tuán)抵京前呈交禮單的用意。于是,單子上第一項(xiàng),也是最貴重的一項(xiàng)禮品是著名儀器工匠菲利普·馬特烏斯·哈恩耗費(fèi)30年建造的“哈氏天體儀”,拉丁文寫作Plantarum,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布蠟?zāi)岽罄?rdquo;。有一臺(tái)現(xiàn)藏于德國(guó)國(guó)家博物館,乍看上去只是一個(gè)大架子上擺著三個(gè)表盤,周圍有三個(gè)小的天文儀器,應(yīng)該是能看到日月星辰的運(yùn)行軌跡之類。事實(shí)上,乾隆派去查驗(yàn)禮品的官員大體上就是這么回報(bào)的,只是像木匠一樣把大架子高九尺八寸之類的信息記錄甚詳。若要理解天體儀的神奇之處,就必須明白它是當(dāng)時(shí)歐洲最新的天文觀測(cè)與理論的精確呈現(xiàn),包括顯示日食與月食、土星的光環(huán)和五顆衛(wèi)星、月球環(huán)繞地球的橢圓不規(guī)則軌跡等。
為了給乾隆一點(diǎn)科學(xué)的震撼,馬戛爾尼特地為天體儀補(bǔ)充了長(zhǎng)篇的專業(yè)解釋。可惜,不僅補(bǔ)充進(jìn)去的話漏譯了,禮單本身的譯文也極其簡(jiǎn)陋,稱得上將“簡(jiǎn)化”策略運(yùn)用到了極致:“一座大架仔,西音布蠟?zāi)岽罄蹋颂焐先赵滦浅郊暗佤肹球]之全圖,其上之地裘[球]照其分量是小小的……”且不說禮品名稱的不用心,后面籠統(tǒng)的描述自然很難讓乾隆看到其中蘊(yùn)含的奧妙,而只會(huì)讓人覺得它是中國(guó)早就有的渾天儀之類物件。難怪乾隆會(huì)認(rèn)定馬戛爾尼“張大其詞,以自炫其奇巧”。
譯者的問題不僅僅在于欠缺天文學(xué)知識(shí),更在于不了解馬戛爾尼的意圖和乾隆的知識(shí)面。簡(jiǎn)單來說,譯文應(yīng)當(dāng)用不容更改的科學(xué)真理營(yíng)造出不容置疑的權(quán)威光環(huán),重點(diǎn)是讓乾隆意識(shí)到,馬戛爾尼背后是一個(gè)昌明強(qiáng)國(guó),它擁有泱泱中國(guó)所無的知識(shí)和力量,但又愿意與大皇帝分享,以示交好之意。
“博學(xué)人里挑出來一個(gè)大博學(xué)人”
英國(guó)哲學(xué)家約翰·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給出了一個(gè)更適合分析此類現(xiàn)象的框架。1955年,他在哈佛大學(xué)開了一門12節(jié)的課程,講稿結(jié)集為《如何以言事》,其中第八講將言語行為分解成三個(gè)層面:話語行為、話語施事行為、話語施效行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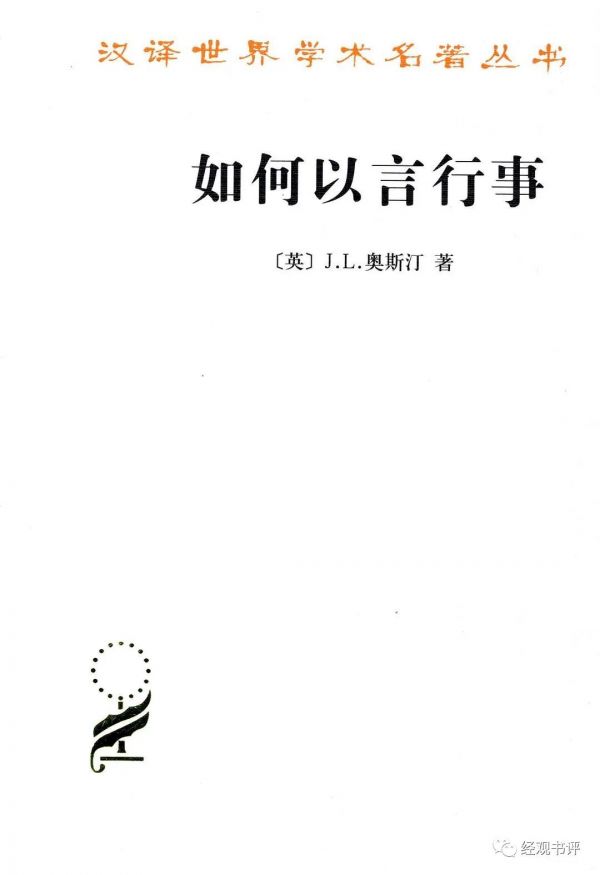 《如何以言事》
《如何以言事》
[英]J.L.奧斯汀/著
楊玉成 趙京超/譯
商務(wù)印書館
2013年3月
話語行為就是發(fā)出屬于一門語言的聲音,略微推廣的話,在紙面上寫字也可以算。嚴(yán)格來說,似乎只有一個(gè)人明確知道自己在寫什么的時(shí)候,他寫下的字才算得上是話語行為的結(jié)果。《龍與獅的對(duì)話》里有一個(gè)有趣的例子。馬戛爾尼使團(tuán)的副使名叫斯當(dāng)東,時(shí)年13歲的斯當(dāng)東的侄子也一同前往中國(guó)。小斯當(dāng)東頗有語言天賦,在倫敦學(xué)過一年中文。上一節(jié)里提到的禮單中文譯本就是他謄抄的,有人評(píng)價(jià)說,小斯當(dāng)東“寫中文比寫英文還要工整”。不過,他并不是一位合格的譯者,比如使團(tuán)離京后,他將一份英文感謝信翻譯成中文,用負(fù)責(zé)信件轉(zhuǎn)交的時(shí)任廣東巡撫朱珪的話說,“雖系中華字書,而文理桀錯(cuò),難以句讀”。無論是謄抄還是“翻譯”,小斯當(dāng)東的行為都難以算得上言語行為。相比之下,不管“長(zhǎng)生天氣力里,大福蔭護(hù)助里”看上去如何詰屈聱牙,但元朝的硬譯是符合言語行為的標(biāo)準(zhǔn),只是需要讀者略微習(xí)慣而已。
不過,真正給馬戛爾尼使團(tuán)帶來溝通困難的地方顯然不在于言語行為層面。畢竟,使團(tuán)呈交的譯文絕大部分都符合語法,所用也是正當(dāng)?shù)臐h語詞匯,中國(guó)官員和乾隆都能理解文書的字面含義。上一節(jié)中主要涉及的是奧斯汀三分法中的“話語施效行為”,也就是“[說話]后對(duì)聽者、說者或其他人的感情、思想或行為產(chǎn)生某種影響,并且在說這些話時(shí)可能原本就有計(jì)劃、有意圖、有目的地創(chuàng)造這些影響。”
傳統(tǒng)上,這主要是修辭學(xué)的研究范疇,有時(shí)哲學(xué)家會(huì)批判過分追求效率的做法是巧言令色,偏離真理,但對(duì)身懷外交使命的馬戛爾尼來說,這些都不是問題。他就是想用語言和文字的力量打動(dòng)清廷,只可惜被翻譯壞了事,完全沒能讓乾隆感到自己與英王是同氣連枝的大國(guó)君主,反而夯實(shí)了“紅毛”是海外小邦,喬治三世是“海主”的固有印象,盡管海主對(duì)應(yīng)的原文是LordofSeas,最起碼也是個(gè)“王下七武海”或者“四皇”的境界。當(dāng)然,從馬后炮的角度來看,假如馬戛爾尼果真讓乾隆產(chǎn)生了他想要造成的印象和情緒,那使團(tuán)大概就不只是徒勞無功,就連能不能平安離開中國(guó)都成問題了。這便涉及到了“話語施事行為”。
奧斯汀在講座中的界定比較簡(jiǎn)單,就是“我們以什么方式和在什么意義上‘使用’言語”。從分析哲學(xué)的標(biāo)準(zhǔn)來看,這壓根算不上一個(gè)定義,因?yàn)檎鐘W斯汀本人指出的那樣,短短一句話里用到了“意義”和“使用”這兩個(gè)臭名昭著的含混詞匯。不過,對(duì)應(yīng)到這次龍與獅磕磕絆絆的對(duì)話中,這個(gè)概念就具體化成了一個(gè)問題:馬戛爾尼交上去的文書是國(guó)書還是納貢表文?
從馬戛爾尼的立場(chǎng)來看,他自然是在遞交國(guó)書,《龍與獅的對(duì)話》中對(duì)原文和譯文做了精當(dāng)?shù)膶?duì)照分析。比如,原文羅列了馬戛爾尼的頭銜、使命和履歷,懂英文的讀者會(huì)感受到一種類似《權(quán)力的游戲》里龍媽頭銜的感覺:“喬治·馬戛爾尼子爵閣下,利森諾爾男爵,大不列顛王國(guó)樞密院成員,最榮耀的巴斯騎士團(tuán)騎士,最古老的皇家騎士團(tuán)白鷹騎士團(tuán)騎士……曾代表朕出使俄羅斯宮廷,曾治理朕在東方與西方的若干極大領(lǐng)地,曾任孟加拉總督……”縱使乾隆君臣不了解其中提到的部院、職位、地域都是什么意思,至少能夠直觀感受到對(duì)方在努力抬高自己的身價(jià)。
但在清廷看到的譯文中,馬戛爾尼卻仿佛是一個(gè)跑腿的小官:“從許多博學(xué)人里挑出來一個(gè)大博學(xué)的人(指馬戛爾尼入選倫敦皇家學(xué)會(huì)一事)。他從前辦過多少大事,又到俄羅斯國(guó)出過差,又管過多少地方辦事,又到過小西洋本噶蠟等處屬國(guó)地方料理過事情。”譯文的最大問題是完全扭曲了文書的性質(zhì)。這篇文書的譯者是廣州行商通事,他是按照常見的進(jìn)貢表文來翻譯的,因此通篇都將英國(guó)置于番邦小國(guó)的定位。鄙俗含混不僅僅是譯者水平有限,更受制于立場(chǎng),所以對(duì)皇帝要極盡恭維之能事,對(duì)英國(guó)則要力言其卑微渺小,與國(guó)書原文可謂南轅北轍。
當(dāng)然,在今天的絕大部分文本翻譯中,如此極端的扭曲相當(dāng)少見,更不會(huì)被提倡。但它以一種最激烈的形式傳達(dá)了一個(gè)涉及譯者主體性的普遍問題:我在做的是什么事?是勸告,是陳述,是講解,還是宣布?在一切知識(shí)背景和文體考量之前,這永遠(yuǎn)是先決性的總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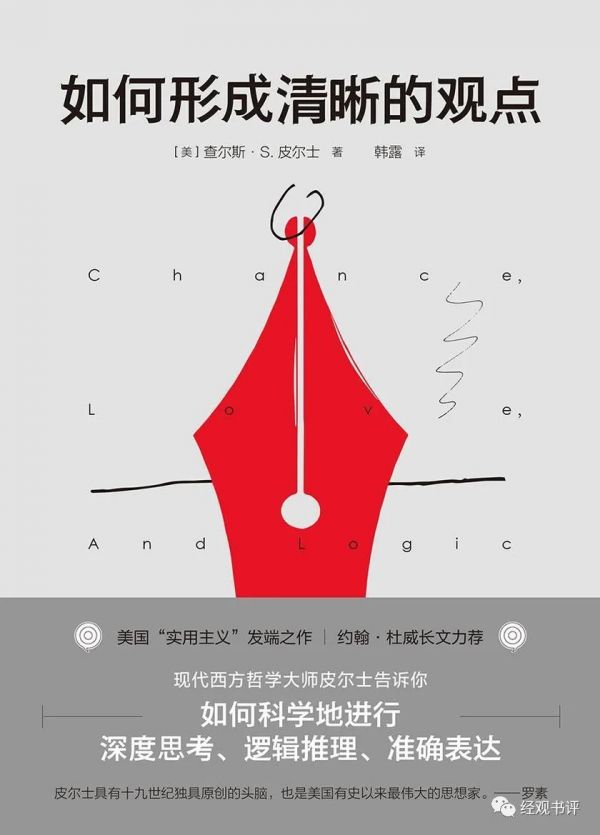
《如何形成清晰的觀點(diǎn)》
[美]查爾斯·S. 皮爾士/著
韓露 /譯
巴別塔文化|天地出版社
2019年11月
譯者的立場(chǎng)
既然提到了立場(chǎng),又是外交場(chǎng)合,那我們首先想到的是政治立場(chǎng),尤其是忠誠(chéng)問題。馬戛爾尼最倚重的譯員李自標(biāo)出生于甘肅省,來華前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一所神學(xué)院(今中華書院)學(xué)習(xí),已經(jīng)取得神職人員身份,恰逢馬戛爾尼尋訪譯員,便加入使團(tuán)。李自標(biāo)盡管不懂英語,文言文水平也比較一般,但用漢語與中國(guó)官員溝通不成問題,且熟練掌握拉丁文,能夠與出身貴族的馬戛爾尼等人交流,可以將拉丁語文書翻譯成堪用的書面中文。使團(tuán)大部分成員對(duì)他評(píng)價(jià)頗高,馬戛爾尼認(rèn)為他“是一個(gè)十分理智的人,意志堅(jiān)定,具有良好的個(gè)性”。
然而,李自標(biāo)來華的最主要?jiǎng)訖C(jī)其實(shí)是傳教,這與馬戛爾尼的通商目標(biāo)并不總是一致的。由此帶來的最大風(fēng)波是,李自標(biāo)曾瞞著馬戛爾尼,以口頭方式向朝廷請(qǐng)求改善中國(guó)天主教徒的待遇,結(jié)果立即引起乾隆的警惕,向使團(tuán)下發(fā)了措辭嚴(yán)厲的敕諭:“至于爾國(guó)所奉之天主教,原系西洋各國(guó)向奉之教……即在京當(dāng)差之西洋人等,居住在堂,亦不準(zhǔn)與中國(guó)人民交結(jié),妄行傳教,華夷之辨甚嚴(yán)。今爾國(guó)使臣之意欲任聽夷人傳教,尤屬不可。”馬戛爾尼自然一頭霧水,但最終也沒有懷疑到“誠(chéng)實(shí)且能干”的李自標(biāo)頭上。雖然從上帝視角出發(fā),我們知道馬戛爾尼追求的通商目標(biāo)也不可能獲得清廷應(yīng)允,但李自標(biāo)的自作主張仍然對(duì)使團(tuán)造成了不可逆的危害。
不過,“立場(chǎng)”一詞的理解可以適當(dāng)寬泛一些。立場(chǎng),就是希望某一個(gè)人或者一群人變得更好。李自標(biāo)濫用自己的語言能力和譯者身份,這無疑是自私的,充其量只是為了天主教徒這一個(gè)群體的利益,哪怕他真誠(chéng)地堅(jiān)信天主教是唯一的真理。這不是一名譯者應(yīng)當(dāng)采取的心態(tài)。相比之下,美國(guó)實(shí)用主義哲學(xué)家皮爾士在1878年《大眾科學(xué)月刊》上一篇題為“關(guān)于偶然的學(xué)說”的文章里的一句話頗得我心:“無限群體的利益、認(rèn)同這種利益至高無上的可能、對(duì)思想活動(dòng)無限延續(xù)的希望,這三個(gè)方面[是]邏輯不可或缺的要求。”
這本探討邏輯學(xué)、數(shù)學(xué)、物理學(xué)、進(jìn)化論等科學(xué)議題的小書里有一條貫穿的暗線,那就是理性思考不是單調(diào)僵死的觀察、歸納和演繹,而必須至少相信自己是為未來將會(huì)出現(xiàn)的無數(shù)人類工作。值得注意的是,這個(gè)信念本身是無理可循的,尤其是對(duì)我們這些早已在無數(shù)小說電影中見過人類毀滅或者瀕臨毀滅的21世紀(jì)網(wǎng)民來說。當(dāng)然,在大多數(shù)翻譯實(shí)踐中,這樣崇高的理想不會(huì)浮現(xiàn)在譯者的意識(shí)里,有時(shí)甚至可能與眼前的利益相悖。但在我看來,皮爾士的表述恰恰表述了一位譯者的理想立場(chǎng)。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802028547號(h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