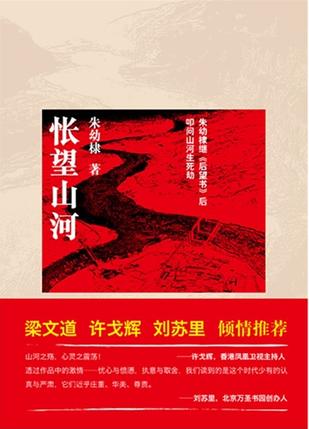馬國川:謝謝各位朋友,今天天氣不太好,而且因為今天搞馬拉松,很多地方交通管制。大家到這里來肯定不太容易,我有一個朋友是中經報記者。曾經做調查,北京一年的交通管制七千次,也就是說平均每天有二十次。我想起一個故事:有一個當過委員長的,在全國常委會里面。有一次他就說,你們老是說北京堵車,我覺得不堵啊,我每次到走長安街都很舒暢啊。你們以后應該實地調查,沒有調查沒有發(fā)言權。
我們來開始比較沉重的話題。《悵望山河》這本書我是周三上午拿到的,到晚上就讀完了。讀完了之后,非常感慨,文筆非常好,但有一個缺點,看了之后心情特別沉重。真的是特別沉重,就沒想到,今天的中國,我們在北京,有時候我做記者可能走的地方多一點,周圍朋友可能也走了很多地方,我們走很多地方沒有這么深入的去探討這個國家這么多年來山河如此巨大的一種變遷,而這種變遷,不是按照我們所想象的,向一個更美好的方向發(fā)展,而是向一個相反的方向發(fā)展。大江大河斷流,山川斷裂等等,這一切問題這本書里面都有反映。
我想是不是首先先請朱老師先談一談他到底為什么要寫這本書。他是怎么寫這本書的?
朱幼棣:因為我寫這本書,前后時間經歷了五年之久。五年以前,當時出了一個《后望書》,講到城市的文化遺產、城市風格和城市文化遺產的保護,也講到了一些江河水利的問題,是和江河以及跟工程建設有關的。但是當時寫的比較匆忙,有一些話還沒有說完,一些重要的工程重要的關鍵字也沒有說完。我記得當時跟王軍在書店做節(jié)目,就有人提出來,說我怎么對長江三峽這么重大的問題都沒說。我說我當時已經開始接觸了那部分,那時候還沒有進入后三峽時期,而且后三峽時期還沒有到。很多這東西看的不是很清楚。但《后望書》的最后一節(jié)已經講到了長江三峽問題,我就開始準備寫這本書。
這本書準備過程正好碰到了汶川地震,汶川地震應該說是一場我們的重大災難。汶川地震以前,我正好考察和調查世界文化遺址,也到過都江堰的一些地方。那個時候工程建設正在如火如荼的地步。當時提到了岷江水電,岷江河流都完全干涸了,那時我就想,是不是跟地震有關,當然是可能是一個大體構造的變化。就開始研究地震問題,地震雖然有多種原因造成,但是人為的工程因素也不能夠完全排除。
當時我就寫了一個關于汶川地震的地質方面的思考,到底我們的地震,也是一個山脊平衡被打破了。這個突發(fā)地震有多種原因,有自然的因素,有月亮的因素,還有可能有工程的因素,都不能夠排除。我有一個特殊情況,年輕的時候搞過地質。二十幾歲的時候在礦山做技術員,看了所有能夠找到的地質的書。后來我到新華社做記者,跟王軍同事,我也是是國家榮譽地質隊員,這方面也低調。然后就開始深入就講、寫地震的,比如地震我們應該注意什么,特別是工程建設重大工程建設怎么能夠保護我們山區(qū)的平衡,使我們江河和山體不受破壞。這就寫了一段時間,后來又寫了《大國醫(yī)改》,把中間斷了有一年多時間。
既然講江河問題,那主要的江河應該有。比較突出的問題是什么?我們究竟是水災,還是洪災還是旱災?我們江河面臨著什么?應該說,北方的江河面臨的主要的問題是斷流和枯竭;中部地區(qū)和南方河流主要是污染,而且地下水不能飲用。這樣我們就從一個宏觀層面,考慮到研究我們主要江河這個半個世紀以來發(fā)生的一些變化,這跟我們工程建設,我們治理的指導思想有關。為什么現(xiàn)在海河完全斷流?天津原來是一個河口、港口城市,現(xiàn)在天津沒有港,海河不能通航,都是近五十年來發(fā)生的變化,這個變化是非常大的。因為五十年就是兩倍人的時間,我們現(xiàn)在剛生下來就認為城市就是高樓大廈,城市就是現(xiàn)在我們的就這個情況,現(xiàn)在孩子覺得河流本來就沒有水。這個北京的永定河就是沒有水,北京就沒有河流。但實際上,歷史不是這樣的,是我們半個世紀以來,一步一步造成的一個江河、這個山川面貌的一種變化,我想探討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上,我畢竟不是專業(yè)人士,可能研究的有些膚淺,但我想宏觀把握好,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我想把這個問題提出來,更深入更具體的研究,以后需要一些有志于此的人,能夠在我們國家宏觀層面上來統(tǒng)籌考慮這個東西的變化。十八大里面提到一個是“美麗中國”,把生態(tài)文明列入到我們五大建設的總體規(guī)劃里面去。我多講兩句,這個“生態(tài)文明”提得非常正確。我記得前兩年有一次國家環(huán)保局的人叫生態(tài)文明,還有什么城市文明,社區(qū)文明、企業(yè)文明,都搞不清,究竟是怎么區(qū)分這些文明?我當時就提出,這個文明有兩個坐標系:一個是橫向的,包括社會、社區(qū)、職業(yè)、農業(yè)問題,道德文明,這個是橫向文明;另一個是縱向文明,游牧文明、農耕文明、手工業(yè)文明,還有工業(yè)文明,因為工業(yè)文明造成了環(huán)境和身邊的破壞。工業(yè)文明的后期就提了一個生態(tài)文明,這是一個縱向的事。
那么現(xiàn)在我們可能“十二五”,新一屆提到2020年翻兩翻,而且標志著我們國家已經進入到后城市化社會,有些破壞是不可逆轉的。但是我們必須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國內提的就是科學發(fā)展觀也好,我想一個人的科學覺醒是很重要的,這個就跟我們民族覺醒政治覺醒一樣,謝謝!
馬國川:謝謝朱老師!朱老師講的很好,我覺得剛才大家注意到,朱老師后來用了一些政治語言。他原來在山西省委辦公廳當過副主任,后來到國務院研究室當過司長。剛才我們在聊天的時候,他就講到08年溫家寶總理去哈佛大學那篇演講稿,就有朱老師,他當時參與了撰寫,是不是您寫的?
朱幼棣:我只是參與參與。
馬國川:那個演講稿我覺得講得非常好。剛剛朱老師講到,就是他的思考一開始是地震,后來是山河的變遷,我看這本書之后對我觸動比較大的也可能在座的朋友比較關心的,就是他第五章講的一個問題----北京的水危機,題目是《北京水危機背后》,我看了之后感到很震撼。書里面講到,其實在清朝的時候,昆明湖就是那個時代的一個水利工程,而它這個水利工程做得非常好,非常完美。不但解決了北京的水利、供水問題,也解決了災害----山上下來水的災害問題。可是后來我們搞了官廳水庫,現(xiàn)在水庫的問題出來了,水庫本身沒多少水,下游枯竭。我的問題是提給朱老師和王老師的,就北京的水危機,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自然原因還是人為的原因,有沒有解?朱老師你先來!
朱幼棣:這個是關于北京的,王軍老師更有依據,待會請他講一些更加深刻的。我講的就是從一些宏觀的角度來說的,北京城現(xiàn)在沒有一個完整的水系,這是北京最致命的問題。北京沒有地表的河流,地表的河流包括永定河,基本上都是斷流的。這個是我們解放后,對北京造成最大的一個50年最大深刻的變化,北京永定河和潮白河都是北京的母親河。解放后,我們第一個水庫就是官廳水庫。當時設計的庫容是40多億立方米,40多億立方米就是基本上把永定河的年平均水量的百分之七八十放到官廳水庫里,建一個水庫就能夠解決問題,結果下游一片,上游包括山西境內,包括河北境內,包括內蒙境內,修了很多很多。其中大同的叫做冊田水庫。控制了永定河流域的40%。你下游建了一個大的,上面又建了一個大的,這個永定河自建立以來一直沒有裝滿水。只有幾億方米。等于修的一個大棚,只有一個小管子里面有水,而且層層攔截。
興修水利是一個政治化的行動,而且沒有全流域統(tǒng)籌的考慮。不但造成了水力資源的大量浪費,人力資源的浪費,而且下游一點水都沒有,包括盧溝橋下面也沒有水了。現(xiàn)在據說北京要花一百多億打造景觀河,就永定河那么這個景觀河就不是河了,就是湖,而且沒有水,這使北京的地下水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北京應該是城區(qū)有湖、有水的,現(xiàn)在水面搬家,湖泊搬家,搬到長城以外居庸關以外的官廳和密云去了。那地方風光不錯,有草原,有湖有水,城里卻沒湖沒水,地下水也受到了嚴重的影響,現(xiàn)在北京70%還是用的地下水,不是用密云水庫的水,那么大的水面白白的在蒸發(fā)。北京也沒有搞一個完整的水系,一下了雨都進了下水管道,下水管道應該跟河流應該分開,地表水還可以再利用的,結果全部進入到地下管道里面去,跟污水混在一起,這樣我們的水系跟給排水系統(tǒng)是混在一起混亂了,這可能是北京市整個規(guī)劃設計上的一個問題,包括護城河什么的都沒有了。
我們現(xiàn)在僅有的幾個湖,就是元朝設計的,包括中南海、北海,都是郭守敬跟劉秉中設計的。解放后我們還沒有搞新的湖,除了亞運會鳥巢那個地方以外。所以要重新恢復北京市的水系,要保護最低的生態(tài)的水量和流量,從這個方面來考慮我們北京市的一些規(guī)劃,才能解決這個問題,包括調水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我想這個王軍會說的更好。下面請王軍老師!
王軍:這個先說幾句向朱老師致敬的話,因為朱老師是我在新華社非常敬重的前輩,也是對我進行最高啟蒙的前輩。那個時候朱老師還不認識我,我91年到新華社工作的。我看朱老師這本書,還說那會經常寫什么城市性的報道,就是長高了長大了,就不懂,一竊不通。那時候寫了很多錯誤的文字。其實我后來寫點書,也是自我的覺醒。我在這個過程當中朱老師給我很大的幫助,剛才還跟朱老師談說我看他寫的關于北京的這個很多大遺址保護的文章,那時候心里面一下子豁然開朗。然后就說元大都這個遺址還在,看了之后心里面咯噔一下,你看元大都那個時候你看馬可波羅,那么震撼,看他的記錄里,就知道元大都整個遺址的狀況是什么樣的。這個對我心里面是有很多的啟發(fā)。
那會,朱老師很多的文章我都看,然后后來就看他的《后望書》,看了之后也是很震撼。我回憶很深的就是官廳水庫,因為南水北調。這個跟北京水有關系,那個時候要繼續(xù)加高大壩,要翻天。實際上永樂皇帝干了兩個大事,一個是修紫禁城,一個是修武當山。那么這兩個大事,在解放之后,都遇到了大麻煩。比如說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制定了要改造故宮的計劃,在63年做出完全拆除的計劃,這是永樂皇帝的一個大工程。還有一個就是武當山,就是丹江口水庫,把下面一百多個那么重要的建筑,一點措施都沒有的,完全給淹掉了。所以我那個時候就去丹江口水庫,因為那個時候要南水北調,我知道那個故事我去采。后來我在看朱老師的書,就寫到這些老百姓被搬到青海,我看了之后真的是痛苦。
就這些人,都是一生只能過一次,這些人就是因為這么一個工程,他們的這一生就被毀掉了。而且別人一點都不覺得可惜,我看到老師的文字后內心里是非常痛。我在看這本書也是,我就覺得這本書說的一切一切的東西都是一個道德問題,就是我們這一代人就要把我們的大好河山為了我們所謂的利益,就要把后人的權利全給提前透支。
馬國川:有一個說法,說是犧牲歷代人的利益,為了后代,更好更好,還有這種說法。
王軍:因為我后來工作的分工,寫的城市的建設,這涉及到人文環(huán)境的問題,也造成很多的經濟自然環(huán)境的問題,實際上這兩個問題都是一樣的,就是都是我們這一代人對后代人的責任,一定要考慮這個問題。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看你這本書寫的冊田水庫,03年那個時候北京放水,那個時候北京已經干的不得了了。那個時候我正好是陪梁先生,他是剛剛生病的時候,那時候大家都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就覺得他是搞環(huán)境保護,他很抑郁。我記得我那時候《城記》寫完了后就送給他,他在我面前談的時候就落眼淚。他也說,我們搞了這么多年環(huán)保,呼吁那么多事情,環(huán)境保護是越來越差了,那還需要我們這些人干什么?這個是很痛苦,后來我記得有兩次聊天說,我就覺得他是搞環(huán)保的,就是老百姓一跑到北京來上訪了,都把他當政府部門來對待。
他老人家就成天接受這些事情,他只有一顆良心啊,還有別的什么嗎?包括里面寫的好多的移民,就找他,你說梁先生他能干什么呢,所以他也就是找找我們的記者。看我們這幫記者能不能寫點文章呼吁呼吁,幫幫那些老百姓。他很痛苦,梁先生我說了一句話,我印象很深。他說,我們這代人是趕不上了,你們怎么辦呀?我們很快就過世了,你說中國以后一定人口大爆炸,環(huán)境大爆炸,到那個時候,國在山河破,可能是國破山河也破,都不好說了。
后來我那個師傅說我陪你出去散心。他說我還沒有看過唐代的那個南唐史。比梁思成和林徽因,發(fā)現(xiàn)的那個唐代的還要早,早幾十年,那我就說我陪你去,去山西的五臺。那次就開著車陪他去看,他看了之后就心情非常好。緩解了他的心情,他那個時候有知道冊田水庫這個事,就一放水就往北京流。結果沒流到北京,這個就大地太干渴了就全部陷下去了。
朱幼棣:因為這個桑干河的上游。水利部門發(fā)明了一個詞叫做調水。你上游往下游放水怎么叫做調水呢?
王軍:這個就是面臨大自然的一個態(tài)度,這個就是一切都是人工化。你說好象是很計劃,其實根本沒計劃。比如說官廳水庫,我是這剛說回到北京一個話題,我是十多年前我和一個同事一塊去調查的官廳水庫。因為那個時候賈慶林在北京當市委書記,他也說希望把這個非常緊張的一個水流問題。因為當時北京是發(fā)了一次大洪水,結果是把密云水庫全給裝滿了。后來我記得是郭金農當書記。他高興壞了,他說本屆政府吃水的問題無憂了。這個吃到賈慶林當書記的時候就開始遭遇這個事了,就希望能把官廳水庫給用起來。然后我們又做一個調查,就發(fā)現(xiàn)那個里面全是污水,全部是張家口的工業(yè)廢水,生活污水。上面是幾百個水庫,這個書里面有詳細的數(shù)字,還是我記得有五百多個水庫。把張家口算上河北境內就有二百多個水庫,就全給截了,截到張家口那,往下流就沒有什么自然的徑流了。所以大家到康熙草原去玩,千萬別摸那個水啊,那個水是不能摸的。那個水臟的不得了。然后有時候像北京城西邊,像石景山、門頭溝那邊,有時候喝水困難,他們還偷偷的放點那個水。讓他沉到地下去。然后再通過這個凈化,然后在從地下水在抽出來,那個水都是很成問題的。
所以我就覺得,當然為什么會成為這個樣子,我就會想到那會毛主席。昨天在北大給同學講課讓同學們分享這個故事,就是他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肖像往那一看全部是煙囪。他說從天安門城樓往南邊一看全是煙囪,當時梁思成就不能理解,就說中國那么大,為什么要在城框框里面搞工業(yè)呢。其實毛主席說這個話他是有想法的。就那種蘇聯(lián)專家來北京搞規(guī)劃,制訂規(guī)劃的時候,他們說我們莫斯科我們是無產階級國家的首都,我們的工人階級,有百分之二十多,占城市人口的。你北京市就占3%、4%,你是無產階級國家的首都啊。說這一下子這是個問題。
所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還講了一句話,就是看到游行隊伍里面的工人階級比較少。毛主席就說劉淇是北京市第二副書記,就說難道首都要搬家嗎,要搬到上海去嗎?所以那會就很緊張,趕快就上重工業(yè),上首鋼,搞這些東西,上面還說還是方便中央領導熟悉工業(yè)生產,因為他們都是從農村來的干部。然后這樣北京在八十年代的時候,全國工業(yè)門類是130多個,北京就有120多個。這個為世界各大首都罕見。所以這一下就把北京的水資源耗的很厲害。你說像你剛才講的你這個我們那邊的萬泉河。它一萬個泉。北京市水是非常豐富的,以前完全就是一塊濕地。我當時到內蒙古那個鄂爾古拉,就是成吉思汗他們老家的那個地方,我就看到那一大片草原和濕地,我看到時候我就覺得忽必烈那會來到北京的時候,他看到這個西海這一片,肯定就是鄂爾古拉那種感覺,因為游牧民族是逐水草而居,他是這么一塊濕地。現(xiàn)在這濕地退的就幾個水庫還算是,那邊還在搞開發(fā)。大馬路修過去,然后我上個禮拜去看,荒郊野外空降一個巨大的shopping mall,那個完全是美國人的生活,就開著車大家跑那里去買東西,大家在那個地方都得開車。馬路修的那么寬,然后那么多這些產業(yè)全往那地方去。
我看朱老師這本書我真的是很憂郁。就是這個現(xiàn)在是咱們朱老師也寫了,咱們是靠南水北調打吊針了靠輸液了,打點滴了。這兩千萬人口的城市啊,是中國的首都啊,就靠打吊針活著。我就說這么多。朱老師接著說。
馬國川:剛才朱老師和王老師講,我理解啊,兩條,一個是上游修了太多的水庫,把水攔截在外面了。第二個王老師講的就是毛主席為了他們高興,搞了那么多工業(yè)建設,地下水用的太多。至少是兩條原因,兩條很根本的就是都是人為造成的。我看朱老師的書就剛才我說的感到很沉重。其實我看王軍老師的書也感到很沉重。他的《城記》包括他最近出的《拾年》,講北京城六十年來的變遷。一個非常好的非常美麗的在世界上都可以擺在前面的一個古老的城市,眼看到就一點點的拆沒了,拆成了現(xiàn)在的模樣。然后還有剛才王老師講的內容特別感慨,如果我們現(xiàn)在還回到60多年前,我想可能在北京去轉的話,可能就是王老師剛才的那個場景,當初都是水,都非常美的一個地方,就60年很短的一個時間就變成這樣,我就在想不管是山河的變遷,山河破碎,還是一個城市的樣子來說,變成這樣一個模樣他根本的原因是什么,為什么在兩代人,就是我們此前,就是中華民族在這土地上生活了幾千年都沒有如此改變過他,在這么短的時間里面為什么能夠把他改變成這樣,而且這種改變,我覺得我個人看并不是說向一個正確的方向改變,向我們希望的美好的中國方向轉變,而是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在他指導思想上很顯然,他絕對不是說方向正確,出現(xiàn)了小的偏差,而是完全錯了。他這樣的問題根源是什么,這是制度的原因,還是思想的原因,還是這樣一個哲學思想上有這樣的錯誤,我覺得這個問題我作為記者來說我感到很感興趣。想請王老師談一談。
朱幼棣:我先說。因為我想我們是一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這個行動的效率是非常堅決的,但是我想不是跟共產黨還是跟其他黨沒有什么太大關系,主要是指導思想的理念的一個缺點,然后比如因為國民黨他的行動能力比較差,就確定理念又做不好。但我們共產黨只要一確定以后馬上行動起來就是雷厲風行,我想包括對于河流、對于城市建設,對于我們建設的一些思路,理念首先是出了問題,比如說河流。那么應該說包括北京永定河,包括潮白河,包括海河,包括黃河長江,都是我們的母親河,我們怎么對母親河,如果這個關鍵出了問題,你一定認為母親河是個壞河是個廢河,一定要把海河根治了。這就是有問題。你怎么對待你的母親,這個母親可能有很多的缺點有很多的毛病,這個脾氣可能比較暴躁,有一點喜怒無常。但畢竟是母親,但母親是不能根治的。作為一個孩子來說,那么對于母親肯定是不能根治。我這里面寫到,北京中華世紀壇的第一付浮雕,一百萬年左右歷史的泥河灣人民遺址就是在永定河上游,那個桑干河的邊上,作為一百萬年我們中國古代的文明,就是沿著河流走來的,就是河流養(yǎng)育了我們的文明。
應該說我們祖先是最早認識河流的規(guī)律,包括河的漲水汛期和干旱,他就居住在河的邊上,包括新世紀時代和舊世紀時代,主要是沿河而居的。人類和河流始終是不離不棄的。到了這個世紀以后我們碰到了,場水災。比如說1963年,海河流域的水災。這個水災可能有自然原因,也有很多人為的因素,因為那個時候修的水庫比較差,都是土壩,就造死了很多人,就馬上說這個是害河,那么就要根治海河從根上給你拔掉。海河是根治了。花了十幾年每年都上百萬人在工地上,上面修水庫,中游怎么樣,整整干了十五年左右的時間。把海河給根治了,根治的沒有水了。然后就開始引灤濟津,天津沒有水了。天津是九河下游,就是首先沒有水,然后就從灤河引水到天津,天津九河怎么會沒有水呢,就沒有水了,然后引灤基濟津剛剛完,又開始引黃濟津,現(xiàn)在又從南水北調濟京。就一個工程接一個工程的干。這樣干下去我看了,有個領導在里面,他從三峽調水,他說可能漢江沒有水了,水不夠,因為漢江上游要先往西安調水,呢北京呢?這樣水不夠。準備從三峽那調水。這樣干下去我們還有一個休止嗎?
馬國川:這個是一連串的錯誤,看我們看宣傳報上,幾乎每一個都會成為領導人的政績,根治海河成功了,是政績,引灤濟津成功了,成為一個政績,現(xiàn)在南水北調又是政績。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xiàn)象。
朱幼棣:但這個沒有認真的反思我們究竟要怎么達成要根治,海河要不要保證最低限度的生態(tài)流量。這個華北平原是不是需要白洋淀,是不是需要湖泊,這個地下水怎么辦,怎么得到補充?沒有一個部門從宏觀方面綜合考慮到我們這個生態(tài)環(huán)境、生態(tài)系統(tǒng)、這個水圈巖石圈大氣圈的一個變化。不是說我們需要那個專家,我們國家不缺專家,需要一個大師級的人物,能夠宏觀的綜合的確實科學的對我們的工程重大的思路思想工程和后果進行一些反思,不能夠簡單的有利弊,什么利大于弊。你這看不清楚,作為這個利弊對于生態(tài)是很難計算的,而且沒有一個時間的距離,很難能夠考慮到真正利和弊,這個不能夠比較。
那就覺得這個環(huán)節(jié)很好,但是這個地方能夠值多少錢,你算不出來,有些東西不好比較,不是一個層次上,所以這個我們呼喚著一些科學的覺醒,還有一個科學的真正能夠有科學發(fā)展觀的一個領導。
王軍:我想這個問題也是我想找答案的問題。現(xiàn)在這個新書的前面就是探討一下,為什么對我們的老祖宗有這么一段時間的改變是這么的扭曲,這個剛才像朱老師說的對待母親河是這樣的一個態(tài)度覺得他有病。那么我們對待自己的文化,我就覺得我在查檔案的時候看到55年對梁思成的批判,其中有一位高層領導說了一句話就是搞民族形式的賣國主義。這句話啊考考大家的智力,怎么搞民族的反而成了賣國的,我要搞西方的反映了愛國是不是?恨不得恨自己的人種不配套。所以我就覺得他們認為就是民族的就是落后的。你搞落后了,就讓別人打我,那你不就是賣國嗎?他們是這樣一種邏輯。那么在鴉片戰(zhàn)爭之前中國的人認為自己是天朝上國,那么經歷了這個鴉片戰(zhàn)爭,特別是甲午、日俄,就像嚴復寫的這個《天演論》,他的書的原名是達爾文進化論與倫理學。那么赫胥黎寫的,他認為那個社會不適用于這種,就說人和人之間有互敬互愛,不是那些最能殺人的人他才能夠存活下去,他說個是不適用與達爾文這個東西的。那么嚴復是把這部分全部刪掉了,就把自然界的達爾文主義全部移植到社會里面來,把別人的作品徹底閹割顛覆掉。嚴復還在序里面寫說翻譯要做到信達雅,看了之后我就覺得很不是那么回事,你可以不寫那個序,把別人的東西完全搞混了,既不信也不達更不雅了,那個時候是不是把這樣一種達爾文主義植入到中國人心里面,就覺得看自己老祖宗的東西什么都別扭。
馬國川:就是變成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
王軍:對對。就是這種叢林法則。就是那種笑貧不笑娼這個樣子,現(xiàn)在就是登峰造極了。你說我寫的《拾年》那本書,我是按照順序把在新華社十年的文章我把他歸置在一起,我寫的最早的文章是拆曹雪芹故居,最晚的是拆梁思成故居。這簡直是什么概念,比方你去問一個法國人,你們是不是要拆雨果的故居?那英國人是不是要拆莎士比亞的故居?我們生活在那樣一個時代,就是這個東西在不斷的演繹,演繹到最后一種邏輯、一種思維方式、一種規(guī)則,用了一段時間他就產生了既得利益,他永遠是會拿到所謂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說愛國,等等事情來說事。
朱幼棣:然后就說這叫做危房。
王軍:對。實際上我覺得現(xiàn)在就是這一種壞現(xiàn)象,這是我的一種理解,就是在文化上就說我這個,他好象對我們的祖先實際上還沒有很好的整理,胡適先生說的這個叫做整理活物,再造文物。首先要整理活物。你的傳統(tǒng)的文化有哪些東西,這些東西包括像治水。我看到朱老師寫到都江堰,他那會在主持這個論證相關的工作。希望媒體來反映這個事情,你這個是一個大悲哀,你說在都江堰這么一個工程上來干這個事情,那真的是有系統(tǒng)的來否定我們的傳統(tǒng)。而且是完全失去了一種起碼的邏輯和理性,我覺得是這樣,對北京城這種連續(xù)的拆除,甚至在五六十年代還做出要拆除故宮的計劃。這個有系統(tǒng)來否定我們的過去。對我們的過去是什么缺乏一些最起碼的研究,你比如說北京。我就覺得這個城市我不愿意用情感,我可以把情感全部拋掉,我就說這個在五十年代的時候北京好多的規(guī)劃這個城市要住一千萬人口,那這一千萬人口是怎么來的,有沒有跟水的供應有關系呢,還有要搞重工業(yè)有關系,沒人去想給毛主席一句話,毛主席說就是一千萬人吧。
那么在檔案館里一查那些檔案。我就看到有些知識分子在五七年反右之后讓他寫檢查說他說的話。那么有一個就是對黃河有關系。我看了之后真的是可以說是哪個朝代能夠做到黃河請。那時候搞三門峽,就是說他把黃河的水全部攔住了,那往下流出去都是清水。
馬國川:當時我記得我看文章說。胡喬木還寫了一片文章。文章里面我有講說黃河清圣人出。就是說黃河清了以后圣人出了,這個圣人是誰,就是東方紅。
王軍:所以你看這個往下游流的都是清水了。上游的我們植樹造林。我看這次朱老師寫三峽也寫到朱镕基總理很著急啊。說現(xiàn)在長江也跟黃河差不多,都是泥沙問題,你說上面植樹造林,五十您夠不夠,六十年夠不夠,根本不夠。還有說上面實行植樹造林。慢慢的水土保持就是新水了,下游的這個流下去的也是清水。那是多么大的一個悲劇。 我今年國慶節(jié)的時候我去看永樂宮,那是我第二次去,我覺得在座的朋友你們有機會一定要去看看永樂宮。他是元代的建筑,他里面的壁畫不得了。壁畫是用無道子的那一派的壁畫,他畫那個神仙頭巾的飄帶飄到地下一筆畫下去是三米三,中間都沒有接口。就那個師傅帶著他的弟子在那里畫了二十多年,但是現(xiàn)在永樂宮就是因為三門峽給搬遷了,搬遷了之后費了很大的力氣把那些壁畫切割,都能看到那種痕跡,都很心痛。然后搬到那個地方去,從永和鎮(zhèn)搬到芮城。就搬過去之后,永樂鎮(zhèn)那地方根本就沒有淹。那個三門峽就失敗了,然后那個遺址還擺在那里。這個想起來這種愚蠢。
朱幼棣:《后望書》這個序言我就寫到了這個問題,就是永樂宮的這個。我們電視里面經常放,因為在周總理的關懷下面,把永樂宮給搬遷了,沒想想三門峽修水工程,淹了多少古城。六座古城,很多的古跡。這個房屋被拆了搶出了一件家具,現(xiàn)在電視上不停的播,這個永樂宮當時總理怎么關心這個,這個人員做了什么。當然這個大伙被水淹了拆除這個房子,搶出了一件家具是很難得的,也是很值得表揚的。但是這個房子怎么被拆了,應該被誰拆了,沒有人考慮過。
王軍:所以說我看了之后包括像朱老師寫的那個新安江的那個,淹了那么多古鎮(zhèn),那么多老百姓,結果最后產生的效益就相當于一個小煤窯。我就覺得這個書太重要了,太重要在哪里?披露了大量的事實,大量的被一些虛假宣傳所掩蓋的事實,我就覺得真的是朱老師做這個工作太重要了。其實這個我們干這行的就是要把大量的事實向社會公映。你早點公映就會改變。我就看到朱老師在后期里面寫的司馬遷,很巧合,我在我的《拾年》那本書里面也寫到司馬遷。我不知道朱老師是不是贊同,我就覺得司馬遷就是一個新聞工作者。他為了寫史記到大半個中國都實地的調查和采訪,為了寫孔子還跑到孔子的故里去采訪。你說他那時候多慘啊,他那時候為了把史記寫完,我看到有一篇文章就寫司馬遷,后來我看了之后我覺得司馬遷他生活那個時代也是文化墮落的不得了的時代。
為什么?那個時候焚書坑儒啊,那會紙張還沒有流行啊。就把那個沒有多少讀書人焚書坑儒了,你說司馬遷他讀一個《左傳》,《左傳》是一個簡書啊,要買一棟房子呢,他把一個房子的一個簡翻完才把這本書看完,所以那時候沒有多少書,被焚了。所以那到漢朝你看那個時候人跟人怎么稱呼,都不太會了。我就想到我小時候,文化大革命結束。要文明用語,請、你好、謝謝、對不起、再見。從那個時候開始學,我了解的漢朝那會也差不多這樣,他比我們還慘在哪里?連立法都搞不清楚。后來司馬遷他們又去修立法。后來他們就治這個史記,如果史記不搞出來真沒有中國,就大家沒有一個集體的記憶,所以我就覺得你看一個書寫歷史的人他能夠向社會供應歷史的人,他能夠對這個民族這個社會所做出的貢獻是這樣的一個貢獻。
馬國川:王老師有一個發(fā)現(xiàn)啊。就是司馬遷也是一個記者。剛剛這個話題我覺得挺沉重的,就是說回顧這一段歷史,面對現(xiàn)實,就覺得我們現(xiàn)在面臨的很多問題都是不可逆轉的一種災難性的痛苦,北京城,不可能在回到原來的狀態(tài)了,今天的那種山河也不可能回到原來的秀麗山川了。剛才朱老師他給出答案最后可能在思想上,希望將來出一個大師,英明領導人,大概是這個意思。然后王老師也是在思想文化上找原因。我覺得除了這些之外應該還有些制度上的原因,比如說,為什么一個人一句話為了他的高興,就可以把所有的工業(yè)集中到一個地方上來。我最近剛看了一個故事,我覺得很有意思,就是羅瑞卿女兒羅點點寫的一本書。羅瑞卿,當時他都是要出席常委會會議的。后來毛突然有一段不讓出席了?什么原因呢?因為這個毛岸青的老婆紹華要下面四青工作。羅瑞卿說你別去,你要照顧毛岸青,紹華一定要去,結果這個羅瑞卿當時擋不住他了,就讓他去了。毛聽說之后非常不高興,這么一來誰照顧我的兒子啊,不要參加常務會了,就一句話,就可以不參加常務會了。過了一段紹華回來了,毛又高興了,又讓他參加常務會了。這是最高層這種決策的這種隨意性質,我覺得恐怕不僅僅是從思想上來找原因,還有一個制度的原因。就我前不久采訪聯(lián)想的柳傳志,他講的一段話非常好,他說西方的制度他運行的很好,但是還不是最好,他大概能打個七十分、八十分,打不到九十分但是也不會到六十分,中國這套制度如果一個好的決策搞好了可以打到九十分,但是一個壞的制度就可以0分甚至還是負數(shù)。這就是制度的差異性。
剛才在想朱老師和王老師講的這樣的思想的原因,包括一些專家的問題,這本書里面也講到了地震。朱老師用四個篇幅講地震,08年地震的時候很大的一個處境。我記得當時我看完我特別關注,我作為媒體人特別關注,但是主流的原因專家講的地震是不可預測的,我當時就覺得特別的納悶。因為我小時候學過有那么一點點,現(xiàn)在完全不是了。我當時就在想你要地震專家干什么,我當時也想寫說批駁這個,但是呢覺得我不是專家,我說不出那些話。可是看到這本書我覺得找到了朱老師可以和這些人對話。
他揭穿了很多所謂的地震專家的謊言。我想請教朱老師說,我們來談一談這個比較有意思的話題,就是地震這個問題你到底怎么看?到底將來是不是可以預測的。這也是我們每個人的福祉。
朱幼棣:我想用李四光的話。他認為地震是可以預報的。當時刑臺地震以后國務院召開一個緊急會議,就是地震能不能預報的問題,當時也有專家提出是地震不能預報,國外都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當時大家爭論面紅耳赤。總理就問,他說,大家話講完沒有,講完請李四光說說。他跟總理說,地震是可以預報的。而且他說不要議論紛紛,兵已渡河。他說把地球比成一米大的打球的話。那么地震發(fā)生在地殼上就是薄薄的一層紙。他說地震是在地殼的淺層發(fā)生,五公里到十公里的這樣子,就是跟地球一米大球,他就是紙一樣的厚度,而且地震并不是分散在地殼上面的,平均分散很多點肯定是不好預層,如果像雞蛋一樣,如同雞蛋破了的殼,那么地震就發(fā)生在破了殼的上面,就是斷裂帶,那么你可以觀察那些斷裂帶是活動那些是不活動,而且長期進行檢測。那么必定能夠找到預報的途徑。
我覺得李四光是對的,他還講到了四川川西的問題這個斷裂帶怎么形成的,要怎么密切的關注。而且我們當時出了一些政策,包括群防群治,包括專家包括大學生,用全社會的力量,來監(jiān)測地震。確實這個地震有很多的很難,特別是他有兩個概念,中長期的一個預測,一個是臨震預報,這個臨震預報是特別難的,就是半個月一個月以后發(fā)生,這個預報是比較難度,這個預報是中長期野外調查和中長期基礎上搞的。可惜的很,現(xiàn)在我們進入了商品經濟的時代,這個地震行業(yè)要跑野外,他吸引不了我們優(yōu)秀的人才,也吸引不了優(yōu)秀的學生,可能待遇也比較差,這個從事地震工作或者地質工作很多人都不安心,而且況且你可能這一輩子研究了這個地震也不可能發(fā)生,蹉跎歲月。一般人看來這個東西是甘于寂寞的行業(yè),要很深入的研究地質的問題,要跑到野外,搞調查,現(xiàn)在地質系統(tǒng)大概是有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就是原來中科院的搞地質的,地礦部搞地質的。這是地震地質的研究,另一部分是原來的國家地震預報的東西,就是搞地震儀的臨震記錄的,地震儀可以測量哪個地方發(fā)生了幾級地震,是搞監(jiān)測的。從現(xiàn)在看搞檢測的比較有錢,他可以申報國家的課題。他搞計算機搞什么網絡,固定設備這樣,是地震行業(yè)里面活的比較好的一部分。而且這里面可能掌握了部分話語權的部分。因為他坐在室內做的能夠申報課題又能夠申報國家的投入,你跑野外你到處跑也弄不了幾個錢還很辛苦。
搞檢測肯定是馬后炮為主,因為發(fā)生地震以后才有記錄。這樣搞預報的搞臨震預報的人才特別短缺。現(xiàn)在這些為推卸責任也好,干脆說國際上都沒有解決我們解決不了,國際上當然是難,那日本上還有海底的那個,跟我們大陸是不一樣。海底你肯定是預報不了,他這個斷裂在海底,不在我們大陸上面。但我們中國的斷裂帶應該說幾條還是應該在大陸上,比其他國家要有利的多。我想周總理也說,跟大學生說,我們這代人可能解決不了,但是我希望你們這代人能夠解決地震預報問題。
對行業(yè),特別是對地震科這個志氣信仰很重要,世界上沒有干不成什么事。如果有這個信仰就一定能夠突破,如果老是無所作為,這個世界難題就解決不了,那么就一定通過不了。因為我已經有了很好的一個成功預報的海城地震。
王軍:我這個沒有什么發(fā)言權。劉巍在這里,他對海城預報包括汶川地震之前的地震預報工作的狀況,他是作了一個非常系統(tǒng)的調查。當然我是他那些報的編輯,我在看的時候也是一直有一個困惑,就是地震怎么預報的問題,因為有很多說法叫做地球不可侵入等等,我看了朱老師這本書有一個李四光這樣一個分析,是淺層的這個地殼的活動狀況,這個是有很多辦法是可以檢測的。那我就覺得像五李四光包括周恩來他們做這個決定他們確實是有一種歷史的使命感,我就覺得對這種事情負責任的政府的官員,他有沒有在這么樣一種狀態(tài)。我就覺得大家都是懷疑,后來這本書里面事實上他們是為開拖責任來反駁他們,我就覺得看這些的時候真的是讓人感受非常的動怒。
馬國川:我理解剛才朱老師還有王老師講的這些問題其實涉及了兩個問題,一個就是科學態(tài)度,科學態(tài)度其實以前走到了另外一個極端,就是認為人定勝天,人可以改變一切,包括改變山川面貌,更不要說改變一個小小的北京城了。現(xiàn)在我覺得是另外一個方向就是也打著科學的名義,但是實際上是利益的在背后驅動,部門的利益,個人利益,包括說什么這個不可預測,那個不能做,或者說這個可以拆那個不能拆,實際上背后并不是什么所謂的科學預測,但是一些人以專家的身份,以科學的名義在那里做,背后是利益驅動,是不是這個問題?
朱幼棣:關鍵是不是敢于擔當、面對的問題,作為一個科學工作者或者地質學家,地震學家敢不敢擔當,敢不敢面對,這個李四光有一句話比較好,就是云南地震他沒有預報出來,就是李四光國務院開會的時候說最近發(fā)生在云南一次地震,地震以前是有先兆的,可是我們沒有預報出來,我對不起人民,對不起毛主席。我們是有罪的人,我們要將功補過,把地震搞好,他說自己是有罪的人,對不起人民,對不起毛主席。有這分擔當,人民也會理解也會原諒的。現(xiàn)在馬上來了一個就是怕自己承擔責任,就開始躲了,就不能預報。這是地震前一點先兆也沒有,就是有先兆,四十分鐘以前就發(fā)生了一次地震了,也不行。有先兆不行,沒有先兆不行,總而言之先把他說不能預報。然后就無所作為了。我總覺得作為一個科學家也好,作為一個行政部門領導人也好。要有一份擔當。李四光說的非常好,如果地震永遠都不能預報的話就成立這個部門沒有必要了,我們這個工作就沒有意義了,那么你不需要成立這個部門了。
那么我想有人成功的先例,只要努力工作還是可以預報的。為什么這次把意大利的學家判了刑。我覺得判的非常好,因為以前發(fā)生了很多的小的地震,結果跟地質學家商量,問大家近期有沒有大地震,最后商議后說沒有。你為什么知道沒有,沒有也是預報,你預報了沒有,其實死了人了,死了一千多人,那對工作不信任。那么這就出了問題,雖然國際上很生氣,聯(lián)名說地震學家是判刑是不對的,但我覺得是有道理的,你要不預報不出來,還搞不清楚。
王軍:他特別有意思,之前就是說沒有預報,然后一下子有了,這個是不可預報的。不知道是什么邏輯在他們心里發(fā)生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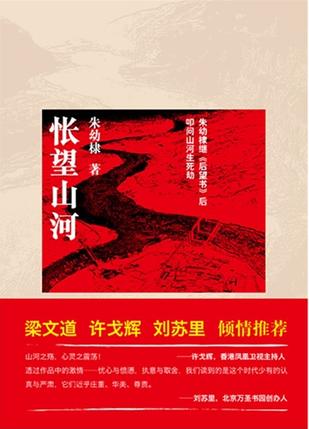
11月25日下午14點,由《財經》主筆馬國川主持,以”河山不能承受之重“為主題的對談,在字里行間書店(德勝門店)舉行。著名學者、作家朱幼棣攜新書《悵望江河》與新華社高級記者王軍,就六十多年來山河變化,以及生態(tài)環(huán)境破壞的原因,展開討論。因放不下對社會的責任,朱幼棣多年來鍥而不舍對這些問題展開追問,回望歷史,剖析當下,在對談間,他還提到了許多被隱瞞、被忽略的重要真實事件。以下為當天對談的現(xiàn)場速記,未經講者審核,如有疏漏,敬請諒解!
對談中精彩摘要:
需反思警惕周圍的話語,例如,"抗旱防汛"的提法就有問題,什么是"汛"?汛是江河在一定的季節(jié)漲落,汛期并不是水災。再如,二氧化碳只占大氣的萬分之三,人類能影響的不過萬分之一,然而目前人類社會已被碳所綁架,動不動就低碳社會,甚至要收碳稅。----朱幼棣
如果《史記》寫不出來,真沒有中國,大家就沒有一個集體記憶。所以我覺得,看一個書寫歷史的人,能夠向社會供應歷史的人,就看他是否能夠對這個民族、這個社會所做出的貢獻是這樣的。---王軍
當日現(xiàn)場記錄:
馬國川:謝謝各位朋友,今天天氣不太好,而且因為今天搞馬拉松,很多地方交通管制。大家到這里來肯定不太容易,我有一個朋友是中經報記者。曾經做調查,北京一年的交通管制七千次,也就是說平均每天有二十次。我想起一個故事:有一個當過委員長的,在全國常委會里面。有一次他就說,你們老是說北京堵車,我覺得不堵啊,我每次到走長安街都很舒暢啊。你們以后應該實地調查,沒有調查沒有發(fā)言權。
我們來開始比較沉重的話題。《悵望山河》這本書我是周三上午拿到的,到晚上就讀完了。讀完了之后,非常感慨,文筆非常好,但有一個缺點,看了之后心情特別沉重。真的是特別沉重,就沒想到,今天的中國,我們在北京,有時候我做記者可能走的地方多一點,周圍朋友可能也走了很多地方,我們走很多地方沒有這么深入的去探討這個國家這么多年來山河如此巨大的一種變遷,而這種變遷,不是按照我們所想象的,向一個更美好的方向發(fā)展,而是向一個相反的方向發(fā)展。大江大河斷流,山川斷裂等等,這一切問題這本書里面都有反映。
我想是不是首先先請朱老師先談一談他到底為什么要寫這本書。他是怎么寫這本書的?
朱幼棣:因為我寫這本書,前后時間經歷了五年之久。五年以前,當時出了一個《后望書》,講到城市的文化遺產、城市風格和城市文化遺產的保護,也講到了一些江河水利的問題,是和江河以及跟工程建設有關的。但是當時寫的比較匆忙,有一些話還沒有說完,一些重要的工程重要的關鍵字也沒有說完。我記得當時跟王軍在書店做節(jié)目,就有人提出來,說我怎么對長江三峽這么重大的問題都沒說。我說我當時已經開始接觸了那部分,那時候還沒有進入后三峽時期,而且后三峽時期還沒有到。很多這東西看的不是很清楚。但《后望書》的最后一節(jié)已經講到了長江三峽問題,我就開始準備寫這本書。這本書準備過程正好碰到了汶川地震,汶川地震應該說是一場我們的重大災難。汶川地震以前,我正好考察和調查世界文化遺址,也到過都江堰的一些地方。那個時候工程建設正在如火如荼的地步。當時提到了岷江水電,岷江河流都完全干涸了,那時我就想,是不是跟地震有關,當然是可能是一個大體構造的變化。就開始研究地震問題,地震雖然有多種原因造成,但是人為的工程因素也不能夠完全排除。
當時我就寫了一個關于汶川地震的地質方面的思考,到底我們的地震,也是一個山脊平衡被打破了。這個突發(fā)地震有多種原因,有自然的因素,有月亮的因素,還有可能有工程的因素,都不能夠排除。我有一個特殊情況,年輕的時候搞過地質。二十幾歲的時候在礦山做技術員,看了所有能夠找到的地質的書。后來我到新華社做記者,跟王軍同事,我也是是國家榮譽地質隊員,這方面也低調。然后就開始深入就講、寫地震的,比如地震我們應該注意什么,特別是工程建設重大工程建設怎么能夠保護我們山區(qū)的平衡,使我們江河和山體不受破壞。這就寫了一段時間,后來又寫了《大國醫(yī)改》,把中間斷了有一年多時間。既然講江河問題,那主要的江河應該有。比較突出的問題是什么?我們究竟是水災,還是洪災還是旱災?我們江河面臨著什么?應該說,北方的江河面臨的主要的問題是斷流和枯竭;中部地區(qū)和南方河流主要是污染,而且地下水不能飲用。這樣我們就從一個宏觀層面,考慮到研究我們主要江河這個半個世紀以來發(fā)生的一些變化,這跟我們工程建設,我們治理的指導思想有關。為什么現(xiàn)在海河完全斷流?天津原來是一個河口、港口城市,現(xiàn)在天津沒有港,海河不能通航,都是近五十年來發(fā)生的變化,這個變化是非常大的。因為五十年就是兩倍人的時間,我們現(xiàn)在剛生下來就認為城市就是高樓大廈,城市就是現(xiàn)在我們的就這個情況,現(xiàn)在孩子覺得河流本來就沒有水。這個北京的永定河就是沒有水,北京就沒有河流。但實際上,歷史不是這樣的,是我們半個世紀以來,一步一步造成的一個江河、這個山川面貌的一種變化,我想探討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