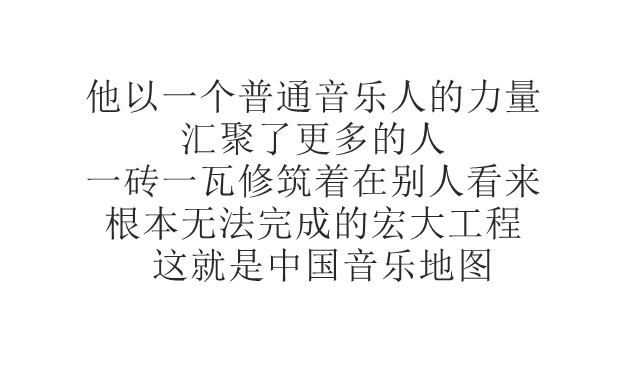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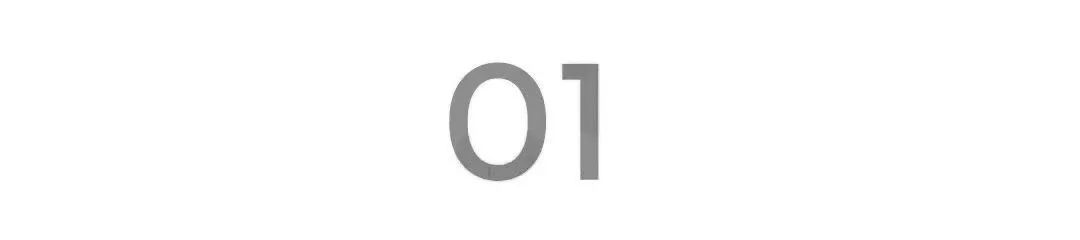
“告訴你一個小目標:我想讓瑞鳴這些音樂放在所有可能出現(xiàn)的地方,全世界聽見50億次,觸達200個國家和地區(qū)。”
一次聊天,葉云川這樣說。秋天已經開始,仿佛全世界都在落葉,我聽到某種飛蟲正在振動自己的翅膀。
葉云川,著名音樂制作人。2003 年在北京創(chuàng)立音樂品牌“瑞鳴音樂”。一個實驗者,一些人眼里的不靠譜的破壞者。其實我一直覺得他是那種有著很明顯的“僧侶性”的人——作為文化保存者,他會最大限度的與塵世拉開距離。他把傳統(tǒng)的盡可能錄入囊中,同時,他也努力做著更多有想象力的音樂。某種意義上說,他是當代音樂人中的一個孤本,一塊獨立于時代之外的飛地。
近 20 年來,他創(chuàng)作制作了二千五百首作品,作品獲得約一百八十個獎項及提名,包括美國獨立音樂大獎、全球音樂獎、中國金唱片獎、華語音樂傳媒大獎等等,這是一下子難以列盡的榮耀。
“我制作的音樂看似凌亂,招法百樣,卻離不開民族文化、世界音樂八個字句。野路子有野路子的內在邏輯、武功秘籍。”他笑道,“我自仗劍走天涯,那管你定的規(guī)矩,餓死方罷。”
聽很多人說過,他其實有一個很高的目標,那就是格萊美。他是為數不多的在格萊美注冊有投票權的中國會員,常常自費把作品郵寄到美國參加評選。2020 年,因為疫情原因,國際航線緊張,他給格萊美的評選會員們寄唱片的運費就花了兩萬多,“你都不知道費了多大力。”
自 2001 年譚盾的《臥虎藏龍》獲得格萊美最佳電影原創(chuàng)音樂專輯獎之后,中國音樂拉近了與格萊美的距離。但遺憾的是,這非常有限,特別在中國本土。作為致力用世界音樂語言來表達中國音樂的本土制作人,他一直希望這一局面可以改變,讓世界聽見更多來自中國的聲音,讓中國音樂有更多的國際話語權。
2020,這一次又失敗了。但他會“屢敗屢戰(zhàn)”。這次見面,我本想追問有關格萊美的事情,他卻把自己的另一個“小目標”說了出來。這個“小目標”,一下子讓我顯得特別功利起來。

“我要的比別人多。”他從不掩飾自己的野心,也不會隱藏自己的失落,“坦白地說,這么多年來沒有做出什么成績的,”“我的幸福感和失落永遠共存,只不過美好遠大過沮喪,總歸內心的滿足要更多一些。”
其實,多年來他在無邊世界旅行,“去大海里游泳”,刻意爭取國際上的影響力,這本身就是最大的成就。——看似為自己,其實更是在為中國音樂發(fā)聲。
有一次,他帶著 1000 張CD到德國參加世界音響音樂大展,英文不好,就在平板電腦寫著,“我是中國音樂人,請您聽我們的音樂”,兩天時間唱片全部送完。在美國做展覽,美國人聽了他制作的音樂,看到他的唱片,就覺得是日本品牌。在西方人的印象中,亞洲品質最好就是日本,最潮就是韓國,而中國的東西,便宜就好。這個東方的堂吉訶德幻想改變這種認知。
改變的前提,是要對這個世界有一點點新的貢獻。“而我,除了音樂,沒有別的可以奉獻。”
他的微信簽名是“一個人的旅行”。但他以一個普通音樂人的力量,匯聚了更多的人,一磚一瓦修筑著在別人看來根本無法完成的宏大工程——這就是“中國音樂地圖”。在一些人眼里,他就是一個哪吒,三頭六臂。目前,這個歷時三年,囊括近40個民族,213種傳統(tǒng)樂器,采錄超580位民間音樂人,1056首曲目,1000個音樂視頻,近30萬字采集文字資料的項目已經收官。
有一剎那,他全身仿佛輕了三十斤。但是隨即,另一個更大的心愿便籠罩了他:把這些東西存留下來,但還要努力傳播到更多人那里去,傳播到世界去。他說,“傳播就是保存的最好方式”。如果把音樂也像佛教那樣分為大乘與小乘,葉云川就是典型的“大乘音樂人”。這也是當代最為需要的音樂人。
他希望用一個完整的系統(tǒng)回答西方人常問的一個問題,什么是“中國音樂”。這些音樂世世代代相傳,如今傳到我們手里,卻正以沒有流量的名義遭到淘汰,“我們對這個世界、對自己的民族到底是貢獻還是犯下過錯?”

從成功學的角度看,他確如他自己所說,是一個“非常失敗的創(chuàng)業(yè)者”。他把自己的許多做法叫做“肉包子計劃”,所謂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2005 年做音樂缺錢的時候,他賣了位于北京三環(huán)邊的一套房子,然后租房住了 10 年,保證自己總有錢做音樂。“事實證明,財商極低智商不在線。”
“還是要跟木匠一樣不斷做東西。”在他心中,木匠這個角色,要比所謂“工匠”更有生命感。“我做的事情都是沒有用的東西,但是我想說,沒有用的東西遠比有用的更加珍貴和有力量。”
這么多年以來,他的“置裝費”平均一年也就一千元。常年牛仔褲帽衫,夏天就牛仔褲、白T恤,這是他永遠的標配。為人隨和,彈性很大,似乎把他放到任何一個狀態(tài),他都能比較容易去適應。但有朋友說,這只是“表象”。他實際上偏執(zhí)、苛刻、挑剔,不通人情世故。他也承認,“雙子座嘛,實際上很分裂很頑固的。”
他總結出一個最能體現(xiàn)自己特征的字:熬。像煎中草藥一樣,他用慢火“熬”著自己的 “小目標”。屢屢失敗的格萊美是一個。“中國音樂地圖”更是一個,“找出中國音樂與世界文化融合的道路”,這是他為自己的過去頒發(fā)的另一種格萊美。
而讓瑞鳴音樂——傳統(tǒng)中國音樂——被全世界聽見50億次,100億次,及至無數人次,則是他現(xiàn)在的目標。
“翻過一座山,見另一座山。”他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彼岸。”

葉云川 攝影:劉麗杰

“我們唯一能做的東西,就是去留存一些必然消失的東西”
搜神記:因為疫情,這兩年世界改變了很多。這期間你是怎么過的?
葉云川:我 2019 年和 2020 年是特別極端的兩年。2019 年一年我坐飛機差不多有幾十次,有將近 300 天不在北京,去了全國 14 個省,還去美國、日本錄音,跨度極大。因為我在做一個項目叫“中國音樂地圖”,瘋狂地、緊鑼密鼓地跑完了 2019 年。2020 年春節(jié)期間就去了越南西貢,然后回到北京,疫情就爆發(fā)了。等于 2020 年整個全年,全部埋頭做我 2019 年的這些音樂的后期。因為 2019 年我的體量很大,涉及 30 多個民族、580 個民間音樂人,樂器都用了 213 種。這就是中國音樂地圖,跨度很大,是一個別人叫做原生態(tài)我卻稱之為根源、母語的音樂項目。
搜神記:這個項目的初衷是什么?
葉云川:對于世界來講,我就回答西方人常問的一個問題,什么是中國音樂?這個對于我們來講有點像哲學性的問題,就像什么是中國豆腐一樣,沒有辦法去回答。因為我們有 500 種豆腐,怎么去講?日本豆腐很簡單,人說我們就是日本豆腐,中國人不服,我們有客家釀豆腐、麻婆豆腐等等幾百種,怎么講?所以我想用一個系統(tǒng)去告訴世界,什么是中國音樂。我用音樂地圖的概念來回答世界,這是中國音樂,你可以從省、民族、地區(qū)、風格當中去解構它。
但我更想表達一個東西,我總結了一句slogan,“用音樂找回民族的記憶,從母語中尋找生命的緣起”。我們的故鄉(xiāng)都被拆沒了,你等于是用今天所謂現(xiàn)代化鏟平所有人的記憶。不僅是我的家鄉(xiāng),是近乎所有人的,被鏟平了、鋪上水泥地以后,其實是所有東西都消失了,沉積千年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那什么東西是可以保留下來的?音樂一定是其中之一。因為音樂很難篡改。在所有的文化形態(tài)中,比如你這個圖片,你這種文字,都可以篡改,可以面目全非。所以說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是音樂很難,因為音樂是內心流動、流淌的東西,你只要敢改一個音符,它馬上就顯得特別不和諧、不自然,一看就是改過的。所以它最能真實地記錄一個時代的聲音。我錄的《西安鼓樂》,算是這次錄音有傳承記載距今時間最長的,最起碼是 1300 年,據說是安史之亂從宮廷逃出的樂師傳下來的,保存到現(xiàn)在幾乎是原貌的狀態(tài),且不說更多的東西。當然有時候有些音樂無法記載不好說,但是對于我們來講,當 1000 多年前的音樂響起的時候,那種端莊、雍容的氣質一出來,你一聽,哇,這應該就是那個時代的聲音!你知道那些演奏者是什么人?他們只是西安郊區(qū)的村民,但是他們的笙管笛、鼓一出來,一聽就是宮廷音樂,而且是大唐的那種華麗的雅樂。所以,“用音樂找回民族的記憶”,這是很好的一個路徑。
搜神記:Slogan的下半句“從母語中尋找生命的緣起”,聽上去也比較大而懸。給我們具體講講?
葉云川:比如我去梅州,這么小的孩子就不會講客家話了,為什么?因為你講客家話怎么上學?而且你講會被嘲笑,是你很土。我也錄客家音樂這些,你只要聽到這個音樂一響起,馬上就聽到了中原,那種敦厚的東西顯然在嶺南地方不可能出現(xiàn)的,它就是千百年從中原一路遷徙而來的。所以只要音樂保留下來、語言保留下來,歷史就能夠很好地去繼續(xù)下去。但是如果沒有這樣的東西,歷史就是勝利者去書寫,想怎么寫怎么寫,可能寫的是面目全非的。我很在意“用母語尋找生命的緣起”,就是因為語言一旦扁平化了、普通化了以后,獨特的多樣的文化一定就消失了。語言不只是工具,語言背后有著每個民族每個地區(qū)的遺傳密碼。
搜神記:要尋找那個中國,現(xiàn)在也只有到這些地方去了。你錄的很多都是各個少數民族的音樂,也是因為語言吧?
葉云川:是的。語言是保留下來的,有些也摻雜時代的語言,普通話,比如說你聽到藏族同胞用藏語講電腦,他也講電腦這樣的外來詞,但是絕大部分就是古老的語言。在這種語言當中,其實就能找到所謂生命的密碼,就能知道你是從哪里來的,然后你才知道要到哪里去。
春節(jié)前我們去北京的郊區(qū)村子里面做一些原生態(tài)的語言和音樂采集,前面這個村保存得很好,相傳幾百年。可我們去新的那個村,所有房子全部推平、全部建新的,然后號稱是有 400 年歷史的村落。你憑什么說 400 年?你甚至可以說 4 億年,因為這片土地存在了 4 億年,但是文化本身呢?歷史風貌呢?在你這里蕩然無存。這種情況在今天的中國比比皆是,我們也無能為力。我們唯一能做的東西,其實也是我做“中國音樂地圖”的重要動機,就是去留存一些必然消失的東西,肯定消失,語言消失、音樂消失,因為沒有人聽,你傳統(tǒng)的東西誰去聽呢?你在互聯(lián)網上沒流量,沒流量就給你刷一邊去了。但是我覺得我們把它記錄下來了,音樂、影像、文字、圖片,立體地把這種文化風貌基本地記錄下來,之后不管多少年,就算一千年依然可以聽到那個聲音,就好像我們聽西安鼓樂,一千多年前如果它沒有演奏的方式傳承記錄下來,我們如何知道唐朝是什么樣一種風貌?現(xiàn)在有很多山寨的那種都是想象的,但最起碼來講還有敦煌壁畫還有音樂看到聽到唐朝的這些東西。那其他的文化你看什么?可能什么都沒得看,這是很可怕的一個現(xiàn)狀,我們對歷史、對文化缺少最基本的尊重。
搜神記:后面會做什么項目呢?
葉云川:我自己喊的口號,是以一個普通的音樂人的力量,希望去聚合更多人,然后我們一起涌入海里。因為所謂的海洋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海洋。我就是這樣一個比較神叨叨的狀態(tài)。2020 年和 2019 年兩年的時間,基本是在做這個項目,2021 年我就是收尾。但是后面我會繼續(xù)做下去,把傳統(tǒng)的盡可能錄入囊中,同時做更多有想象力的音樂。我覺得還可以做 10 年,不過彈指一揮間,或者說一輩子,就一直做下去。
“因為 6 歲以前在鄉(xiāng)下,我沒有被束縛,就有無窮的創(chuàng)造力”
搜神記:你說你是客家人,為此經常去廣東“尋根”。這是怎樣一個來龍去脈,你能說清楚嗎?
葉云川:我本身是四川人,是四川客家人,母語就是客家話。小時候我們就叫土廣東,但是不知道為什么把我們叫土廣東,所有的風俗跟四川人完全不一樣,語言也完全不同。但那個時候因為沒有族譜,也沒有什么介紹,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我們跟周遭人是不同的。你知道為什么我發(fā)現(xiàn)了這個秘密嗎?是直到我后來去深圳。我少年時去深圳,闖深圳,一個人都不認識,我站在羅湖區(qū)蔡屋圍天橋上就哭了,那里是一個城中村,你想啊,一個人都不認識,舉目無親啊。然后我下橋,去找我姐姐的朋友給我介紹的一個人,發(fā)現(xiàn)城中村那些當地人說話我能聽懂!這很可怕,因為我沒有想到到了兩千公里以外,那個村子里面的人說的話我能聽懂。后來就開始琢磨為什么,由此就開始了自己對客家文化的一個興趣。
搜神記:當時為什么要去深圳呢?
葉云川:不想在四川待著了。那時就覺得深圳是一個可以闖的地方,我應該去,就坐了 50 多個小時的火車到深圳。50 多個小時的火車,結果是什么?下了火車睡在床上腳還是抖的,一直抖。深圳的幾年是最艱辛的,但也是建立良好職業(yè)習慣的幾年,學到了最寶貴的東西,比如契約精神,比如永不停歇的拓荒牛精神。之后一度回到成都,享受了幾年生活,但覺得那不是我想要的狀態(tài),后來看北京要開奧運會了,就來北京了。覺得奧運會那么重要,應該看看我有什么機會。
搜神記:我是2001年來的北京,你是哪一年?
葉云川:大約 2002 年。來北京的前兩年,跟著人起哄干了一些事,上很多當,特別的糟糕。帶著驕傲來,結果摔很大很大的跟頭。也想要放棄,后來一想,別放棄啊,放棄就根本沒戲了,在深圳不也熬過去了嘛。那做點什么呢?那就做音樂吧。
搜神記:為什么音樂可以做?
葉云川:因為之前的事情都是跟好多人一塊兒做的,就覺得好多騙子,欠我的、騙我的錢,最后搞得我特別的慘,我就想,我要做自己能掌控的事情。我請了著名制作人張春一老師來做了一個案例,然后開了張,從此以后就是我了,我就一直做音樂做到現(xiàn)在。
要感激這么多年經歷的東西,不管好的壞的,人生就是這樣成長。可以自豪地說,在我的這些作品當中,確實比一般的要深刻一點點,它不是一個娛樂的東西,是可以讓你聽完以后會有些思考的東西,顯然是我在這個過程當中的一些歷練,用音樂的方式給到了大家。
搜神記:一開始就是找人作曲、找人演奏嗎?這個制作人究竟是做什么的?
葉云川:雖然小時候自己學習彈琴唱歌寫歌,但彈不過別人唱不過別人寫不過別人錄音更不會。不過我覺得有一個人可以學習,《三國演義》的劉備,武功不如關張,計謀不如諸葛,卻可以憑借仁義勇氣成就自己,哈哈。所以學習,是我從開始做音樂到今天都沒有停止的成長方式。一個個作品不過是作業(yè),我就一直學一直交作業(yè),有時作業(yè)被人夸,有時作業(yè)被人棄我也無所謂,不過是作業(yè),學到了,內心的進步才最重要。
我的音樂角色是制作人,像你一樣,別人也總問我什么你到底做什么的,我說負責買盒飯,這是第一功能,你要讓你請的音樂家吃飯啊。第二個說法是珍珠項鏈里的繩子,雖然價格只是兩塊錢,但沒有這根繩子,這就不是珍珠項鏈。第三個,有些像漢字的“巫”字,上通天,下通地,中間聯(lián)接人,因為你聽得懂神的語言,也感受來自常人的心聲。
搜神記:你這樣解釋,估計很多人還是聽不明白。你是四川什么地方人?
葉云川:成都,其實我們家就在現(xiàn)在的三環(huán)路。我之前回去過,去到親戚家,拆遷早已抹去了我們所有的記憶,非常傷心。我特別感謝我小時候的那個生活狀態(tài)。因為 6 歲以前在鄉(xiāng)下,我沒有被束縛,就有無窮的創(chuàng)造力。所以到今天我都很驕傲的是,我從來不缺創(chuàng)造力。你給我一把泥巴,我想塑造什么就塑造什么,但是如果你給我一個玩具,你給我一個樂高,你告訴我它必須怎么拼,這個邏輯是怎么樣,那我最后可能就是一個升級版的機器,那沒有價值的。恰恰因為我小時候就是泥巴、泥塘、撈魚、嬉戲,那長大了以后就覺得,這個世界你隨便去想象,是無限的。所以我現(xiàn)在可以吹牛說我在中國有超過 40 個民族的朋友,也去到過 40 個不同的國家,可以無限延展。我覺得這一點對于所有人來講都是最重要的東西。但是這些在現(xiàn)代化當中全部被改變了,我們在從農業(yè)到工業(yè)化的過程當中丟掉了最樸素的、最本真的東西,生活細節(jié)消失,然后我們每個人都成為一顆流水線上的釘子。
“只有在海里游泳的人才會充滿敬畏”
搜神記:你是為數不多的在格萊美注冊的中國會員之一,聽說每年都自費把作品郵寄到美國參加評選。這是一件聽上去簡單、做起來比較復雜的事情。為什么這么做?
葉云川:2020 年又失敗了,我當時好沮喪,傷心了好一陣。給格萊美評選寄唱片,你都不知道費了多大力,光運費就兩萬多。不過失落又不是第一回了,想想也就無所謂。我很少跟別人講這個話題,因為我沒有實現(xiàn)的東西我不太講。
搜神記:但我覺得很有價值。
葉云川:它應該算是一種情結。一個人在游泳池游泳,一會兒 50 米就游過了,每天游十幾個來回,他就會覺得自己好厲害,但是只有在海里游泳的人才會充滿敬畏。為什么?因為無論多強大的人,在海洋面前、在自然面前都不值一提,都會產生敬畏。像我們因為看的東西多一點點,就會產生敬畏。但是反過來,你也會產生驚喜,產生很多強烈的愿望,為什么?因為海洋里面會有無數的珍寶。
搜神記:你是從哪一年開始接觸外面世界的?
葉云川:我最早一次去國外參展,大概是十六年以前去戛納,跟著別人,自費去的。從戛納去了巴黎,然后大家都去買名牌了,我就自己逛。巴黎有 18 條地鐵線,我只記住一個站名,就開始各種晃蕩,想去了解法國文化。從瑞鳴 2003 年一創(chuàng)立,我們的唱片上就中英文對照,而且中文用繁體字。因為簡體字很多華人不認識,我要讓國外的華人能夠看懂。所以十六年前就開始了。
但是慘敗的。參加過兩次戛納展覽,一點不夸張,老外都是繞著我們走。在很多西方人的眼里,中國似乎跟辮子時代差不多。如何去改變這些狹隘的認知,就面臨一個方法的問題。就是說,你是站在一個怎樣的高度去和別人交流,如果你只是說中國地大物博,那人家說再見、不送,人家很客氣。但是你如果拿出真正的作品來,人家看你的時候就顯然不同了。所以我的所有的作品都會把品質做得特別高,錄音、制作、印刷,所以才會有了目前幾十個國家都有一些聽眾的小小的氛圍。
搜神記:從一開始就有意識這么做。
葉云川:不是我特別有意識這么做,而是他們都認同我的作品,因為我把音樂品質定位為TOP級的,我們的音樂品質是和世界一直在一起進步,大家都在這個水平,只不過這個風格你喜歡不喜歡。包括 2019 年我們在美國做了六場展覽,還開了四場音樂會,就是盡可能去接觸世界,去介紹自己的文化,希望自己能夠站到那個頂端告訴別人,我們是優(yōu)秀的。因為沒有這個大家沒辦法對話。這之前,似乎亞洲最好就是日本,最潮就是韓國,而中國文化、中國音樂、中國幾乎所有的東西,便宜就好,就是這樣一個認知格局。我希望像我們可以獲得一些話語權,因為沒有話語權你說什么人家都不聽你的嘛。所以我其實是刻意地去爭取這些國際的影響力,雖然結果很失敗,但一直在努力。我比別人要的要多。坦白地說,這么多年來都是沒有做出什么成績的。2019 年還好一點,《荒城之月》在國際上獲了幾個獎,算是在國際上有些影響的作品。
搜神記:我個人覺得,你的作品是很適合作為禮物送給老外的。
葉云川:這是你考慮的,而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我們能否把這個作品做好。我的作品是比較干凈的,現(xiàn)在有太多作品不講究,因為沒市場,容易將就。但是我不行,我有精神潔癖,音樂里有一點臟的東西我就受不了,比如樂器與樂器之間產生的沖突性或者瑕疵。有一次混音中有一位錄音師把凳子都踢飛了,被我氣的,因為里面有我聽到的不想要的聲音我就要改,太苛刻招人煩。中國傳統(tǒng)樂器以前基本都是獨奏的,后來學習西方交響樂團要樂隊化,它很容易造成沖突,包括我們要把 7 個人弄到一塊吹拉彈唱的時候,你發(fā)現(xiàn)它全是沖突。所以要付出更多的心力調節(jié)融合。這種形式不是中國傳統(tǒng)的文化哲理,傳統(tǒng)文化里我們都是一個人,跟天地自然對話,所以我在長城的山谷中錄了一個作品叫《天人合一》,那個反映很好,包括德國的伙伴說他也要在黑森林照我的錄制。因為在山谷里彈琴,有很多自然的聲音,鳥叫蟲鳴,青蛙和魚都在跳,特別和諧。當時海航、國航、南航的一些全球航線都播,可能是他們覺得這個很適合飛機上安安靜靜去聽去幻想,但沒有一家公司給我一分錢。
搜神記:可以去找他們啊,這屬于商業(yè)。
葉云川:有時候也顧不了那么多,維權成本太高。反過來說,我最欣慰的還是自己做的一些東西大家覺得喜歡,影響了一些人,這不就挺好的?包括那天測一個網絡平臺的數據——真的不夸張,用我們的作品做背景音樂超級棒——我們其中有一首曲子被 31 萬個視頻使用,這帶來的肯定是億級的間接聽過我們的音樂,我們有 2200 首曲子,那我就很開心,雖然它沒有一塊錢,因為它是免費的背景音樂。我認同這樣的傳播方式,我們是有合約的。讓更多人聽到是最重要的,至于說多少人給你錢,它是第二位的事情對吧?難道人家不給我錢我就把它藏著掖著了嗎?那我做它干嘛?
搜神記:有很多機構跟你合作嗎?
葉云川:是的,大家在網上聽音樂的渠道我們都有合作,也還不錯,多少都有些錢,我收到的最少一筆錢是 1 美分,也有月付費 20 元的。有一次去一大姐家,她讓我喝了一包營養(yǎng)粉,價格是 40 元,我說這一口就喝了我兩個月的錢。當然也有很多的,都很高興。音樂對人的影響極大,如同鹽,鹽是賣的最便宜的,這或許是合理的,但會傷害從事音樂的人的心,大多數人會因此放棄,所以需要大家呵護。我們主要還是靠世界各地聽眾買我們的唱片、黑膠才維持這樣的創(chuàng)作。我個人覺得,對于商業(yè)本身來講,它一定是要有能力的人去做,假如沒有能力的人去做,比如我們去做,顯然就是猴子掰苞谷,你撿一個一定要丟一個。我為什么不愿意去撿那個,是因為我知道我撿那個我要丟這個,但是我這個是更重要的東西,我才不丟。那個有就有,沒有就算嘛,對不對?因為你必然要取舍。如果你兩個都給我,我也很開心,問題是不給兩個,上帝很公平,給一個拿走一個,怎么辦?那我肯定要我這個。你要做出好音樂,沒準 200 年以后它還在啊。
搜神記:你肯定也有缺錢的時候吧。
葉云川:做音樂不怎么缺錢,因為錢都花在這了。我這么多年保持著置裝費平均一年一千元(笑)。還有,最極端的是 2020 年疫情期間有半年中午就兩個饅頭,我一算,每餐 5 元就解決了。當然這是笑話,你把作品做好了,總是有無數的聽眾買單,支撐著你繼續(xù)做音樂。最初做音樂缺錢的時候,我賣了房子,兌換成了錄制音樂的費用。事實證明,財商極低智商不在線。那是 2005 年,三環(huán)邊,五六千元一平米的北京。于是我租房住了 10 年,可以保證我總有錢做音樂。

在美國,葉云川與當地音樂家合作錄制福音音樂
“我從小就信,我只要慢慢地爬慢慢地爬,爬到頂上葡萄就熟了嘛”
搜神記:前面你說過 6 歲以前在鄉(xiāng)下,正是因為沒有被束縛,才有無窮的創(chuàng)造力。想讓你再跟我們講講你小時候的事。
葉云川:小時候是這樣的,為什么我講客家話?客家話就是我的母語,我父母、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都是客家人,哥哥姐姐不會講了,我還找回來了一些。6 歲前在鄉(xiāng)下,沒上過幼兒園,傻玩。傻玩其實是沒有人跟我玩,因為我性格非常非常內向,你別看我現(xiàn)在侃侃而談,像個話癆,小時候那簡直了,見到女生臉紅的不行,有人到家里吃飯的時候,我是不上桌的,就躲一邊去。一個人傻玩,最主要的玩法是什么?盼下雨。下雨的時候鄉(xiāng)下的河溝里、田埂上都有魚,可以盡情撈,很有收獲。記憶最深的是,有一次魚塘被開放了,所有人都可以去撈,但是所有大人小孩都在一個地方撈,只有我在沒有人的另一個區(qū)域,一網,又一網,即使一無所獲,也寧愿一個人撈自己的魚。現(xiàn)在想起來,特別有畫面感。
搜神記:那時候我們都是一個放養(yǎng)的狀態(tài)。
葉云川:那個時候生態(tài)比較好,春天一打雷,那泥鰍就從泥里邊蹦出來了。這時候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是我的戰(zhàn)場,就拿個網去撈。有一次釣魚的時候差點被魚拖到水里淹死了,因為才幾歲嘛,釣好長一條大魚,魚拖著我往下走,是附近游泳的大哥在池塘里面把我撈起來了。我 6 歲前所有的時間都是和泥土的關系,而且絕大部分時候是一個人,就是人與自然的一個狀態(tài)。這狀態(tài)一直影響到我現(xiàn)在。
搜神記:音樂的啟蒙是什么時候?
葉云川:也差不多 6 歲左右。因為我姐是學幼師的,她彈鋼琴、唱歌什么都可以的。那個時候我就聽到了校園民謠,記憶最深的就是《捉泥鰍》,特別觸動我,那就是我的天性,因為我就天天捉泥鰍。還有第二首歌是《蝸牛與黃鸝鳥》,我到現(xiàn)在都記得,黃鸝鳥啊你不要嘲笑我,等我爬上它的時候,葡萄就成熟了。很多人不相信,懶得爬那么高,費事。我就信這個話,我從小就信,我只要慢慢地爬慢慢地爬,爬到樹頂上葡萄就熟了嘛,其實很小就建立了這樣的價值觀。
搜神記:后來呢?
葉云川:不好意思——其實也沒有什么不好意思,我初中以后就沒有受過官方教育,考不上高中,我連職高都考不上,因為成績太差了。差到什么程度?數理化這樣的課程我能考 2 分到 4 分,不是 5 分制,這是 100 分,那 2 分到 4 分全靠選擇題蒙。上所有的課我只看小說,語文課我也看小說,我不聽任何一個老師講,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老師氣的不行,后來就說,你隨意,只要不影響別的同學就好。
我不認識字的時候看連環(huán)畫,而且攢好多,零花錢都買連環(huán)畫書了。后來存放在鄉(xiāng)下,有一年鄉(xiāng)下親戚說你們家老房子被燒了,啊?燒了房子不重要,但那些連環(huán)畫全都燒沒了,這是很痛心的。然后看小說,中國的、外國的名著,沒的看了就看港版的舊書。所以我認繁體字,你給我繁體書我完全沒有問題,因為從小這么看。13、14 歲以前,就很幼稚地覺得把一輩子該看的書差不多都讀完了,包括武俠書什么都看完了。
那讀了很多書的好處是什么?就是很早就豐富了我的價值觀,而且這個價值觀是古代人的價值觀,不是現(xiàn)代人的。因為它給我的太滿了,所有的是是非非,全在書里面講得很明白,連《三言二拍》、《儒林外史》都看了,小時候就對所謂的官場完全沒有了興趣。我在北京其實也沒有刻意地交織,我也不會去迎合,我就做我的事,撈自己的小魚小蝦米,要不就看著天空幻想。
搜神記:其實到現(xiàn)在你還是處于一種野生狀態(tài)。
葉云川:是,我從小到大都是處于一種野生狀態(tài)的人。別人覺得很夢幻的東西,對我來講無非就是要像蝸牛一樣花更多的時間去爭取。最后基本全都能實現(xiàn)。我特別在意自己這樣兩個成長階段,6 歲、13 歲,可以說我 13 歲就停止成長了,后面的生活我認為都是在重復,就是不斷在重疊自己信念里的這些東西。后來去歐洲做一些東西,去美國、去日本做一些事情,就是帶著這種信念去做這樣一些幻想里的東西。坦白來說學費交了無數,真的不敢去算這些東西,也沒有必要去算。
“在一個快速的時代,沒有人愿意去做這種東西”
葉云川:我給你放一段音樂,正經地放,不是說作為聊天背景音樂的。這個是在 2017 年完成的一個作品《神話·山海經·上古傳說》,其實也是受小時候看連環(huán)畫和《山海經》的啟發(fā)。這個作品花了差不多有 7 年的時間,過程很曲折,好在扛下來了。你看過《山海經》對不對?我其實不想去講《山海經》里面的神神怪怪,九個尾巴十個腦袋,我覺得過度關注這些就根本沒有理解《山海經》背后的東西。我是想從中找到古代中國人的精神氣質。
搜神記:古代中國人的精神氣質?你找到了嗎?
葉云川:我認為這些上古神話里有很多代表著傳統(tǒng)中國的精神氣質,但今天都丟掉了。所以我要從這個自己的作品中去再現(xiàn)它。比如說第一首叫《盤古開天》,就是開拓的。也有永恒的主題,戰(zhàn)爭、愛情,當然還有我一直更看重的另外一個中國人的精神,曲子叫《夸父逐日》。每次講到這個,我都會起雞皮疙瘩,就是他明明知道無法實現(xiàn)的東西,但他也要去做,也要犧牲,當他最后精疲力盡、無法追逐到太陽的時候,他把手上的桃木杖往東邊扔去,他告訴別人說太陽是從東邊升起。你想一想這樣一種犧牲的精神多高貴啊!但今天的人不是這么講,覺得傻,我就想從這里去講中國人關于愛、關于奉獻的這些偉大的東西。
搜神記:聽了這曲子,確實汗毛倒豎的感覺。
葉云川:幾個月前我們《神話》專輯的作曲家張朝老師給我打電話,說云川你是個“偉人”,我說你這是調侃兄弟啊。我們很熟悉。他說疫情期間哪都去不了,就把西方古典音樂全部淌了一遍,回頭再來聽《神話》,特別的驕傲和感動。當時做這個作品,張朝老師住北京的郊區(qū),我從東五環(huán)往返一次大概 170 公里,我好像跑過八趟,三顧茅廬才跑三趟,我都跑八趟了。他說沒有我不會有這樣的音樂,我們是彼此成就。在商業(yè)社會,在一個快速的時代,沒有人愿意去做這種東西,而且錄音的時候往返錄了幾個月,內心的那種悲涼是什么?因為你知道,你做就是賠錢的。一首曲子幾十個人,而且都是找最好的演奏家來演奏,代價很大,大多數人未必喜歡,但是如果你不這么去做,就不可能產生你想要的東西。結果未必就是多么好,但是你希望它成為一個很好的作品,你就愿意這么去付出,對不對?
搜神記:你在錄制的過程中,是不是總會找那種很特別的樂手或者樂器?
葉云川:對,你隨便聽一下,這個樂曲,古琴是 900 多年的,最優(yōu)秀的古琴演奏家趙家珍老師演奏,那最后你聽的那個彈撥,不是豎琴,是箜篌。我自己錄制音樂使用過 400 種樂器,錄音師李大康老師、李小沛老師、張小安老師,都是中國最優(yōu)秀的錄音師,這樣可以保證作品的高品質。在不同音樂中會使用不同的樂器,不管樂器來自哪里,哪一個合適去用哪個。在不同的國家做音樂,我也都是選擇那些非常棒的錄音室。或許大多數人制作音樂不這么挑剔。但我覺得所有花的這些代價都是值得的,因為只有追求極致,好的東西才有機會留下來。

與印度音樂家在一起
搜神記:你所有音樂當中,都有一種很強烈的孤獨感。
葉云川:對,哪怕是我看上去很歡樂的音樂,但內心也是孤獨的。我的微信名叫“一個人的旅行”,因為我知道,就算咱們關系再好,也不可能一塊“旅行”的,你注定了做這件事情是一個人,那這些作品當中,其實從頭到尾都是帶著這樣一種狀態(tài)。
搜神記:就是微信開機頁面那個人,孤獨星球。
葉云川:但是這種孤獨也不是說因為什么事,是因為我從小就這么過來的嘛,就是從幾歲就這樣。
搜神記:孤獨是音樂的本質嘛。實際生活中你不覺得孤獨吧——因為我知道你有很多方方面面的朋友。
葉云川:還是覺得,還是有。到現(xiàn)在其實還是有蠻辛酸的東西,但是我有個好處,我會把它轉換成力量。當我覺得這里面承受了很多東西的時候,我會把它轉換成能量。我是一個很要強的人嘛,這種狀態(tài)會幫我,而不是說會影響到我什么。生活當中你看很多人都高高興興的,會享受,那我基本上沒有什么,我最大的享受就是在音樂當中,我每天在這就已經很享受了。問題是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所以我另一個更大的心愿,還是希望把它傳播到更多人那里去。很多人不是說不喜歡,而是因為不了解你,都不知道你有這些東西,因為現(xiàn)在充斥的都是那種屬于流量的東西,我們不占流量。
搜神記:那在你這樣一個人看來,實體唱片會消失嗎?就像我們的傳統(tǒng)媒體一樣……
葉云川:這個問題其實你已經有答案了對不對?不是會不會消失的問題,就是必然消失的嘛。我跟你講,你認識我很榮幸,我將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唱片的傳承人(笑)。這是沒有懸念的,但是我基本上會做到最后那一個。今天我們面臨的都是非常糟糕的一個狀態(tài),無論你付出多少艱辛,最后也無法體現(xiàn)你的價值,因為人們不會為這些價值去買單。比如我做“中國音樂地圖”,那么厚重的東西,如果把它全部數字化,它全是碎片,那怎么去體現(xiàn)我們對這個事情的態(tài)度?所以最后,還是要做成一個載體,像這幾年我弄的黑膠、CD等各種各樣的方式,因為這種東西有一定的儀式感,有美學上的認同感,很多東西可以濃縮到這個上頭去。你盡力去在你能夠承受的條件下做成一個拿得出手的東西,而且確實是對標世界的這樣一個東西。我這些作品拿到美國去,都說漂亮,book。美國現(xiàn)在做的東西很簡陋,為什么?因為美國的印刷很貴,簡陋的紙片、塑料就那么一弄,藝術家出門,拿個包就帶著走了,現(xiàn)場簽售破紙片。我每次去國外的時候,都是帶整箱的唱片,我有一個超級大的箱子帶著去,走到哪全部發(fā)完就高興了,因為我覺得這個品質代表著中國。
搜神記:做這種展覽,中國是不是只有你們一家呢?
葉云川:理論上應該就是這樣,因為它不劃算,不劃算的買賣只有傻子才干。我上次在中科院做演講,我說下面沒有一個傻子,所有人都笑了。我說沒有傻子的世界很可怕的,每一個人都那么聰明的話,那傻子都不夠用了。
本文圖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訪者本人提供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854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