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商/文 在托偽之作《奇情異想的堂吉訶德·德拉曼恰先生傳下卷》的前言,塞萬提斯的模仿者和崇拜者,阿維雅內(nèi)達(dá)聲稱,《堂吉訶德》幾乎是一部喜劇。后來全世界的讀者都了解了這一點(diǎn),《堂吉訶德》是一部喜劇。“諸位讀者應(yīng)該對(duì)他的《伽拉苔亞》和散文體喜劇感到滿意,這才是他小說最好的部分。”阿維雅內(nèi)達(dá)表示。奇怪的是,堂吉訶德本人很少臧否喜劇,他似乎只關(guān)心騎士文學(xué)。時(shí)至今日,我們?cè)缫褜ⅰ短眉X德》看作是喜劇,其最早的判斷或許可以追溯到偽作者阿維雅內(nèi)達(dá)。
《堂吉訶德》是否是喜劇?或許更為準(zhǔn)確的答案是,不完全是。
事實(shí)上,《堂吉訶德》早已經(jīng)被認(rèn)定為現(xiàn)代小說的起源文本,它又怎么可以屈尊,怎么可以僅僅滿足于成為喜劇呢?更何況,我們視其為喜劇,只是一個(gè)寬泛意義上的看法,我們從來也不認(rèn)為《堂吉訶德》只是體裁意義上的喜劇。另一方面,直觀意義上講,喜劇有其歷史的、體裁的不確定性。就這一點(diǎn)而言,《堂吉訶德》也有其不確定性,以騎士文學(xué)為中心,《堂吉訶德》劃定了一個(gè)非常廣闊的體裁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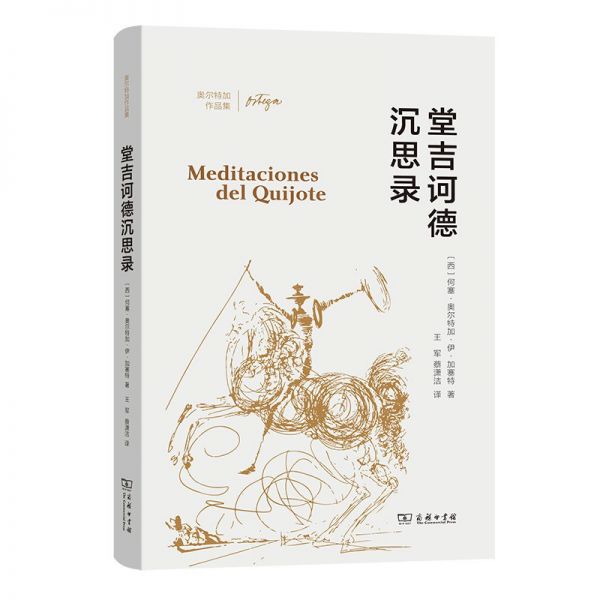
堂吉訶德沉思錄
作者: [西] 何塞·奧爾特加·伊·加塞特
出版社: 商務(wù)印書館
譯者: 王軍 / 蔡瀟潔
出版時(shí)間: 2021-4
一、
《堂吉訶德》是一個(gè)體裁的超級(jí)市場,其內(nèi)里有一部體裁史。換句話說,《堂吉訶德》將不同的體裁置于一系列或連續(xù)或不連續(xù)的位置上,其究竟是何體裁取決于我們的視角和立場。在《堂吉訶德沉思錄》中,何塞·奧爾特加·伊·加塞特正是采取了這種方式,他將《堂吉訶德》放置于諸多體裁的具體狀況和歷史脈絡(luò)中,以此衡量《堂吉訶德》所凝結(jié)的內(nèi)涵。
然而,在進(jìn)入奧爾特加的體裁論述之前,我們或許需要理解一些基礎(chǔ)知識(shí)。比如,體裁是什么?體裁何以如此重要?以現(xiàn)有的中國學(xué)術(shù)世界來看,我們對(duì)體裁有一些誤解,也有一些偏見,誤解在于我們將體裁看作是教科書式的定義,認(rèn)為體裁是學(xué)者考慮的事情。其實(shí)呢,體裁是歷史下傾后的結(jié)果,是歷史自我實(shí)踐遺留的副產(chǎn)品。換句話說,每一個(gè)體裁都依附于特定的歷史事實(shí),一旦脫離此域,它就會(huì)發(fā)蘗出不同的果實(shí)。
從這里出發(fā),我們就可以理解,體裁之重要正在于體裁攜帶著歷史的結(jié)晶。舉個(gè)例子,我們閱讀《一千零一夜》是通過它的體裁閱讀它的,作為一個(gè)異代人,我們是無法拋開體裁本身,直接閱讀《一千零一夜》的。拋開體裁,訴諸的是機(jī)械的閱讀方式,只有尋獲體裁,一種根屬于文學(xué)的有機(jī)閱讀方式才有可能產(chǎn)生。
奧爾特加的體裁觀,和我上述的闡述有所重合,不過奧爾特加更為篤定,更聚焦于體裁本身。對(duì)我來說,體裁是流動(dòng)的,體裁的具身并不單純屬于一時(shí)一地;對(duì)于奧爾特加來說,體裁有一個(gè)明確的中心事實(shí)。在奧爾特加看來,體裁是某些彼此無法妥協(xié)的極端主題,是真正的美學(xué)類型。按照奧爾特加的定義,史詩是一種在其形式中達(dá)到圓滿的內(nèi)容總稱。
不過,奧爾特加并未理解他筆下的“小說”。我不禁要問奧爾特加,你的小說是一種總括的體裁?還是一個(gè)特定的體裁?事實(shí)上,關(guān)于小說是總括的體裁,還是特定的體裁,目前仍存在一定的爭論。不過,就歐洲文學(xué)來說,小說大抵上最初是一個(gè)特定的體裁,而就世界文學(xué)來說,小說絕對(duì)不是一個(gè)特定的體裁。根據(jù)上下文,奧爾特加更傾向于認(rèn)為小說是一個(gè)特定的體裁。正如其所說,每個(gè)時(shí)代都有偏愛的特定體裁,奧爾特加的時(shí)代顯然偏愛小說。也就是說,奧爾特加將《堂吉訶德》視為小說。這是一個(gè)引人發(fā)思的看法。
為什么塞萬提斯和巴爾扎克、狄更斯、福樓拜、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相提并論?為什么十七世紀(jì)的文學(xué)和十九世紀(jì)文學(xué)相等同?就此而論,奧爾特加并不是一個(gè)嚴(yán)謹(jǐn)?shù)奈膶W(xué)史學(xué)者,但他的觀點(diǎn)卻包含了一個(gè)深刻的洞見。小說是一個(gè)跨時(shí)代的體裁。在歐洲,從十七世紀(jì)到十九世紀(jì),小說的內(nèi)容發(fā)生了如此劇烈的變化,但小說仍然是小說。只不過,如果說十七世紀(jì)還不是小說的世紀(jì),那么十九世紀(jì)就是小說的世紀(jì)。
這個(gè)洞見又包含了一個(gè)尚未充分展開的事實(shí):小說是一個(gè)全景的體裁。拿史詩和抒情詩來說,它們自然可以在一種語言和地域中維持長久的秩序,但卻很少跨越語言和地域,變成世界文學(xué)的基本體裁。但小說不同,小說自其誕生就是一個(gè)全景的體裁,而隨著工業(yè)化和殖民運(yùn)動(dòng),小說又蔓延至世界各地,成為世界文學(xué)的基本體裁。正是在這個(gè)意義上,奧爾特加在談?wù)撔≌f時(shí),談?wù)摿耸吩姟⒂我髟姟⑸裨挕ⅡT士小說、啞劇、悲劇、喜劇、悲喜劇、訓(xùn)誡小說等等體裁。奧爾特加尤其注意到,在塞萬提斯的筆下,小說是如何騰轉(zhuǎn)于多種古老的體裁,并最終使自己無所不包的。

唐吉訶德雕像,Don Quixote Statue
二、
在現(xiàn)代主義大爆炸的時(shí)期,奧爾特加重提體裁之用意在何為?其初心是告別98一代(Generación del 98),其內(nèi)涵或許是奧爾特加所想象的歐洲文化,其背景是歐洲的危機(jī),其發(fā)延是奧爾特加的透視主義。在具體闡釋之前,先廓清一些基本事實(shí)。為何體裁牽涉如此之廣,如此之深?其實(shí)答案或許很簡單,體裁史是思想史、但也不完全是思想史。正是在這個(gè)意義上,帕拉·費(fèi)雷拉斯才稱其是“一位沒有系統(tǒng)的系統(tǒng)思想家”。
在此,我們也可以給體裁一個(gè)新的定義,體裁史是沒有系統(tǒng)的系統(tǒng)思想史。此處更為重要的是“系統(tǒng)”一詞。如今,系統(tǒng)思想家頗罕見,但奧爾特加似乎在職業(yè)生涯之初就確立了此類志向,他在這本書的序言部分就表示,學(xué)者或許應(yīng)該在信息和博學(xué)之外尋找出路,其理由是:“在我們今天的時(shí)代重新追求博學(xué)相當(dāng)于一次倒退,就像化學(xué)退回?zé)捊鹦g(shù),或者醫(yī)學(xué)退回到巫術(shù)。”
請(qǐng)注意“巫術(shù)”一詞。這不就是西班牙98一代的典型印跡嗎?在《堂吉訶德沉思錄》出版前一年,98一代的話事人烏納穆諾出版了《生命的悲劇意識(shí)》。98一代成長于實(shí)證主義風(fēng)行的時(shí)代,隨著現(xiàn)代化危機(jī)的浮現(xiàn),部分98一代甚至反對(duì)歐洲主義,退回到西班牙的鄉(xiāng)土世界之中。接著這個(gè)契機(jī),烏納穆諾向西班牙年輕的一代發(fā)出呼吁,“現(xiàn)在,輪到你們了,年輕的一代,歐化的新生代……我希望你們:創(chuàng)造財(cái)富、創(chuàng)造民族性、創(chuàng)造藝術(shù)……”
奧爾特加合時(shí)宜地接過了這個(gè)使命,他抵抗住了西班牙靈魂上的悲傷,他召喚回了歐洲主義和自由氣息。在為《太陽報(bào)》撰寫的第一篇專欄文章中,奧爾特加寫道,“我們要向太陽學(xué)習(xí),將曙光變成熾熱的陽光。”不久之后,我們發(fā)現(xiàn),奧爾特加引領(lǐng)14一代(Novecentismo)徹底告別了98一代的歷史沉疴。奧爾特加為98一代和27一代之間的交替時(shí)期,定了一個(gè)新的調(diào)子:現(xiàn)代主義、世界主義、理性、純藝術(shù)、精英主義。
無論是烏納穆諾,還是奧爾特加,西班牙的危機(jī)和得救始終是潛臺(tái)詞。基于此,粗線條地勾勒一下,奧爾特加后來發(fā)展的“生命理性”哲學(xué),大抵上也是西班牙的命運(yùn)哲學(xué)。學(xué)者們又將其概括為“我是我和我的環(huán)境”(Yo soy yo y mi circunstancia)。我們也可以嘗試做一個(gè)替換,“體裁是體裁和體裁的文本。”某種意義上,體裁就代表著我和我的環(huán)境中間那部分。塞萬提斯在《堂吉訶德》中否定著騎士小說,他的否定累積成了一個(gè)新的體裁。在《堂吉訶德沉思錄》中,奧爾特加早已表明了這一點(diǎn),“我即是我與我所處的環(huán)境,如果我不能拯救我的環(huán)境,自己便也無法得救”。如果說,小說是塞萬提斯的得救之術(shù),那么,其間也自然布滿了多種體裁,多種協(xié)商,多種環(huán)境。
奧爾特加自西班牙向北方尋找解救之道,他先后尋找到了新康德主義、現(xiàn)象學(xué)、存在主義,并融合發(fā)展成一個(gè)自成一體的歐洲文化。在奧爾特加的眼里,嶄新的歐洲文化融合了地中海的感覺、表象,以及日耳曼的理性、深度。對(duì)于我們來說,首先需要將西班牙納入地中海的文明中,它勾連了亞歷山大港、卡爾佩、巴塞羅那、馬賽、奧斯蒂亞、西西里、克里特等地區(qū);其次將日耳曼文明,或者在此基礎(chǔ)上形成的拉丁文化,看作是地中海文明的一個(gè)補(bǔ)充。二十世紀(jì)西班牙的境況卻充滿危機(jī),如奧爾特加所說,“現(xiàn)實(shí)沖進(jìn)我們的感官,粗暴地?fù)湎蛭覀?hellip;…使我們迷失自我,讓我們的內(nèi)心空虛……”
西班牙與西班牙的歐洲是我們理解西班牙、塞萬提斯的重要視角,也是我們理解體裁的另一個(gè)重要視角。在《堂吉訶德沉思錄》中,奧爾特加呼吁,“更理智的做法還是繼續(xù)關(guān)注《堂吉訶德》中那個(gè)巨大的疑問:上帝啊,西班牙究竟是什么?混跡在廣漠的世界和無數(shù)的種族中,迷失在無限的昨日和未知的明天里……西班牙,這個(gè)歐洲的精神海角……究竟是什么?……請(qǐng)告訴我——那個(gè)清晰的詞……無法澄清自身歷史使命的民族是不幸的!”
奧爾特加的比喻將西班牙所面對(duì)的危機(jī)一股腦呈現(xiàn)了出來:什么才是西班牙?同樣地,這個(gè)比喻也給了答案,塞萬提斯的西班牙。塞萬提斯既是西班牙問題的提出者,又是最有效的回答者,塞萬提斯就在西班牙的內(nèi)心。奧爾特加所面對(duì)的境遇,不如用科尼爾·桑丘的說法,失敗的現(xiàn)代文化只有朝著孕育它的本質(zhì)性生命力量轉(zhuǎn)變,才是唯一的出路。奧爾特加的西班牙難道不是一種體裁意義上的西班牙嗎?對(duì)我來說,顯然如此。
三、
奧爾特加的堂吉訶德是一個(gè)抽象的堂吉訶德,或者說體裁意義上的堂吉訶德。在《堂吉訶德沉思錄》序言中,奧爾特加聲稱他無意觸及堂吉訶德這個(gè)角色,他要探究的是藏身在文本中的堂吉訶德幽靈。與此同時(shí),奧爾特加深深感受到,堂吉訶德包含著一種哲學(xué)、道德、科學(xué)、政治的思想。“有一天真有人向我們揭示塞萬提斯模式的輪廓,我們只需將這輪廓的線條延長至我們所面臨的其他共同問題,就可以在新的生命面前覺醒。”奧爾特加寫道。
更為重要的是,在體裁的基礎(chǔ)上,奧爾特加發(fā)展出了一種透視主義。而透視主義,是這位思想者和記者,在卡夫卡、索緒爾、愛因斯坦、斯賓格勒、葉芝、維特根斯坦、T.S.艾略特、華萊士·史蒂文斯、弗洛伊德、桑塔亞那、薛定諤、懷特海、雅斯貝斯、湯因比、凱恩斯、洛夫喬伊的時(shí)代所能做的最必要也最簡單的事。在上述視域中,體裁和透視主義是同義詞,但出于尊重奧爾特加的慣例,以下只采用透視主義。
關(guān)于透視主義,奧爾特加有一個(gè)非常貼切的比喻。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一般意義上,樹木自然是森林的片段和模糊,而森林才代表樹木的全部和必要。但如果我們考慮另一種情況,我們熟知每一顆樹,甚至到了不需要熟知森林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樹木或許較森林更優(yōu),因?yàn)樯挚雌饋硖峁┙o我們一個(gè)整體的圖景,但實(shí)際上只是整體圖景的輪廓而已,相反,無窮無盡的樹木不僅提供了圖景的輪廓,還提供了整體的圖景。在這個(gè)比喻中,無窮無盡的樹木就是透視主義。在《堂吉訶德沉思錄》中,奧爾特加用透視主義,為我們創(chuàng)造了并不連貫的圖景,但也創(chuàng)造了新的圖景的可能。
關(guān)于透視主義最常見的誤解是,透視主義僅僅是作者的透視主義。這種誤解根本上抹殺了透視主義存在的必要。從根本上講,透視主義必然是讀者的透視主義。換句話說,透視主義必然首先是閱讀的透視主義,而非寫作的透視主義。我想,有長期媒體經(jīng)驗(yàn)的奧爾特加更深諳此道。理解了這一點(diǎn),我們便能清楚,為什么奧爾特加的堂吉訶德闡釋幾乎全無堂吉訶德的蹤跡。為什么奧爾特加不斷聲稱自己所闡釋和創(chuàng)造的是堂吉訶德?但他卻很少涉及對(duì)堂吉訶德的直接審視和“把玩”呢?答案或許很簡單,奧爾特加采用了塞萬提斯對(duì)騎士小說所采用的方法,所謂否定之否定。這種情況,也可以從奧爾特加的文體方式來講,《堂吉訶德沉思錄》類似于散文詩,散文或許更有助于詩的呈現(xiàn)。
或許連奧爾特加也忽視的問題,是塞萬提斯的透視主義。在《堂吉訶德》中,我們可以從塞萬提斯對(duì)騎士小說的反映中感受到這一點(diǎn)。塞萬提斯對(duì)騎士小說的態(tài)度常常被認(rèn)定是反諷。但真實(shí)情況是這樣嗎?或者說,塞萬提斯有意以一種反諷的立場或者方法,創(chuàng)造一個(gè)令人啼笑皆非的堂吉訶德嗎?我想,答案可能是否定的。這并非因?yàn)椤短眉X德》并不適用于現(xiàn)代語境,恰恰相反,《堂吉訶德》公認(rèn)具有高度的現(xiàn)代性視野,實(shí)際上,這恐怕是因?yàn)椤短眉X德》從未真正有意使用反諷。而之所以反諷被誤解為塞萬提斯的招牌,恰恰是因?yàn)槲覀冞z漏了塞萬提斯的透視主義。某種意義上,塞萬提斯的透視主義正是奧爾特加的透視主義的源頭。
事實(shí)上,奧爾特加的透視主義并不像尼采一樣,后者進(jìn)入了神學(xué)的領(lǐng)域。奧爾特加的透視主義更像是一個(gè)媒體的產(chǎn)物,或許短期歷史的產(chǎn)物。他憎恨西班牙沒有脊梁,而他在西班牙的宿命終究還是噤聲,這與他所膜拜的堂吉訶德大相徑庭。事實(shí)上,在透視主義,抑或是體裁這個(gè)概念中,思想最終選擇不再流動(dòng),奧爾特加再也無法看到曙光從這白肚色的天空中升起。而就連我們這些愚人都知道,重要的不是天空,重要的是曙光;重要的不是透視主義抑或者體裁,重要的是新思想。
“我將自己思想的辯證肌理隱藏于文學(xué)的表皮之下,如同大自然用角質(zhì)層小心地覆蓋神經(jīng)、纖維和肌腱”奧爾特加曾自證道。這句話充分闡釋了奧爾特加的能量和局限,他或許不是天才,也不是思想家,而是一個(gè)如此真摯的見證人。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802028547號(hào)